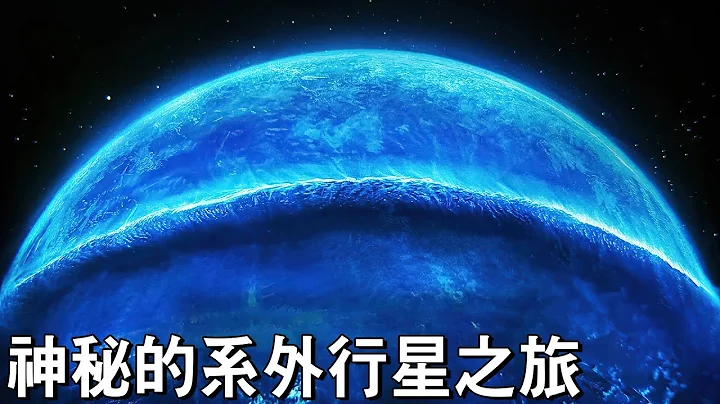在幾乎所有的月球和行星探測計劃中,對目標天體的重力場的測量和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
太陽系外行星因缺少觀測還難以開展對其重力場的深入研究。
太陽系內通常分為兩類:類木行星、類地行星及其衛星。它們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對於類木行星,主要由氣體組成,內部大氣對流變化很快,因此它們的重力場的時變性非常顯著。
對於木星和土星及其衛星的重力場解算主要來自於對 Pioneer、Voyager 系列計劃和 Cassini計劃的射電跟蹤資料。
如土星重力場目前較可靠的只能到10階次。
木星還有Ulysses 和Galileo計劃的跟蹤資料,可以有更高階的重力場結果。
木衛五已有6階次的重力場結果。或許後續的Juno計劃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關於木星重力場的結果。
而目前仍在超期服役的Cassini衛星在探測土星、環、磁場及其衛星等方面(含重力場)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對於地球,可以在地面及低空進行絕對或相對重力及重力梯度的測量、或者藉助衛星開展重力直接觀測。
在20 世紀90年代,將GPS安裝在繞地球飛行的衛星上,同時藉助於激光測距跟蹤,可精確地得到衛星的軌道,從而反演出地球重力場。
近年來,衛星-衛星跟蹤技術(SST)得到了廣泛應用,如CHAMP、GRACE 和GOCE計劃,前兩個都在超期服役。
GRACE衛星已給出360階(甚至2160 階,如 EGM2008模型)的重力場及其變化(35天甚至一星期間隔),從而可對地區性的質量變化特別是地面和淺地表的流體遷移開展研究"。
GOCE衛星由於搭載了特殊設計的重力梯度儀和阻力補償技術的應用,可以預期對全球冰川的變化得到有用的信息。但這種重力梯度儀器太重、太大而難以應用於對其他行星重力場的測量。
最近荷蘭在開展重力梯度儀小型化(約1公斤重)的研究工作。
如果成功,與SST技術的廣泛應用前景一樣,可以預期它將廣泛應用於以後對其他行星及其衛星的重力直接測量,並顯著提高(至少2個量級)對目標星體的重力場解算精度。
對於其他類地行星,通常都是將我們對地球重力場及其內部結構的觀測和研究方法推廣到對這些行星的研究。
下面以火星為例。目前發表的火星重力場模型有JPL的95階次的MGS95,GSFC的90階次的GGM1041C以及歐洲的MGGMO8A。
它們主要是從MGS、Mars Odyssey 和MEX的飛行器跟蹤資料解算所得,這些衛星的軌道都很類似,即傾角在90°左右。
使得高階帶諧項與同為偶數或同為奇數的低階帶諧項係數夾雜、糾纏在一起而難以分離,即所謂的「lumped」重力係數。
另外,從對火星各軌道器的軌道觀測反演得到的重力場出發,深入研究火星內部核的流變學狀態(固、液態?)、核的大小、礦物學特徵(如輕元素的組成及比例)等仍是火星內部物理學中重要和基礎性的未解問題。
對於地球,有大量的、各學科領域的測量,特別是地震層析成像和自由振蕩、電磁場、重力場、火山、地質學、地球自轉等以及實驗室資料,綜合起來共同反演。
但對於其他行星,則只有非常有限的觀測資料,因而對它們的內部物理反演結果的可靠性和精度也很有限。
例如,火星的總慣量矩Ⅰ和潮汐二階洛夫數K₂在現有的關於火星內部礦物學組成及其相變、溫度結構等研究中提供了非常關鍵(但很不夠)的全球性約束。
如有人認為火星核至少是部分液態的。但它究竟是完全液態還是存在固態內核,實際上還缺乏其他證據,仍然是一個很開放的問題。
在利用地面或衛星上直接測得的這些離散的重力或重力梯度資料、或由衛星軌道資料反演解算地球或行星及其衛星的重力場時,在理論上都會遇到一些共同的問題,例如:
(1)重力場反演結果是否唯一?
由於地球及其他行星的複雜性及各自特點,數學上,有很多甚至無窮多個質量分布可以產生離散觀測得到的這些觀測值(邊界條件)。
實際工作中,只能利用儘可能多的其他信息如初始重力場模型、行星地形模型等進行約束,並反覆迭代得到較優的反演結果。
如果缺乏這些先驗的重要信息(實際上我們對其他星球的知識正如此),就難以獲得較好的反演結果。
(2)重力場向下延拓是否穩定有效?
反演重力場,其本質是一個邊界值問題,即以衛星軌道面這個邊界上的重力、重力梯度或軌道數據作為邊界值,解算一定的觀測方程得到行星外部的重力場。
理論上,該結果只適用於該邊界的外部空間。要想得到行星表面與衛星界面之間的空間部分的重力場,就需要將衛星界面以外的解向下延拓。
但可能會發生不穩定性問題,因此還需要利用行星地表的有關數據,但事實上我們對大多數行星還缺乏這些足夠的信息。
(3)球函數表示法本身的問題:
目前所有的重力場模型都使用球函數進行空間解析。
但球函數截斷存在有效性問題及球函數級數在行星表面附近的空間不一定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