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介石

毛福梅(中)與兒子、兒媳的合影。
毛福梅,學名從青,奉化岩頭村人,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毛福梅的家是岩頭一帶的望族,蔣介石於 1901年(14歲)娶毛氏為原配夫人。毛福梅比蔣介石大5歲,女大於男在當時是很普遍的現象。毛福梅拜堂成親那天,小女婿鬧出一場大笑話。下午4時新娘花轎到達。這時按例鳴放喜爆(竹),一群隨轎看熱鬧的孩童和跟大人前來吃喜酒的小客人,都擁到天井去搶拾爆竹蒂頭。
年方14歲的蔣介石見此情景頓時忘乎所以也急忙奔出擠在其他孩童之中,搶拾爆竹蒂頭引得親友哄堂大笑。奉化向有「新郎拾蒂頭,夫妻難到頭」的俗話,人們都忌諱此事認為它預兆新婚夫婦可能不合。正坐在轎中的新娘毛福梅聽到此事,其痛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蔣母氣得跺腳大罵,王采玉流著淚數落兒子邊哭邊數,經兄嫂姐妹女眷們輪番勸慰,勉強收住淚。蔣母灑淚的時候也正是毛福梅傷心的時刻。她萬沒料到丈夫頑劣竟會這樣!新婚之夜毛福梅獨坐新房,面對龍鳳花燭流淚不止。蔣介石「賀郎」後便跑到娘的床上睡了。毛福梅聽著單調的更鼓聲,含著無限委屈的熱淚直坐到雄雞報曉。
按照奉化的風俗,男女成親之後開春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要到岳家拜歲。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一再叮嚀下,蔣介石和佃戶一大早就把禮物裝成一擔去岳家拜歲。這一天,毛鼎和夫婦忙得不亦樂乎,殺雞宰鴨、做湯圓、炒花生,備了一大堆吃的等待女婿上門。可是半天過去還不見生頭女婿的影子。從溪口到岩頭步行3小時即可到達,可一直等到太陽快落山還不見女婿身影。一家人不免心焦,親友陪客有的打算告辭,毛鼎和十分尷尬。
這時毛福梅的堂弟毛鴻芳氣喘吁吁地跑來報告:生頭女婿來了,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燈」哩!毛鼎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上了9年學的讀書人怎麼這麼不懂規矩呢?毛鼎和急對身旁的大兒子說:「武寶,快去看看果真有你妹夫,叫他回去今天不要上門了。」
毛武寶應聲而去,可已遲了一步。不一會兒門外鑼聲大作爆竹三響,花燈隊已走上文元閶門的石階。打頭的少年正是蔣介石,嶄新黑緞袍,襟上泥漬斑斑,西瓜皮帽下那條大辮子也快散架了。他走到大門前立住,從懷裡取出一枚7寸頭大爆竹呼一下吹旺火絨,把引線點著了。毛鼎和一看到生頭女婿蔣介石不禁火冒三丈勃然大怒。他把蔣介石攔在大門外用白銅嘴長煙管指點著這個年輕人的鼻子大聲斥罵起來:「你,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 還有臉上門來出醜?蔣毛兩家的門風都給你敗光了!」
蔣介石挨了毛鼎和一頓臭罵十分狼狽不好言語。他呼的一下轉過身子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毛福梅嫁給蔣介石是由兩家老人做主包辦的舊式封建婚姻,毛氏又是一個纏足的舊式家庭婦女因此結婚後夫妻兩人感情一般。自從串花燈負氣一場後,蔣介石對妻子的感情更加淡漠了。
毛福梅在新婚之夜鬧了個洞房空守,還是諒解了他。總以為他還年少又要讀書,心思不在房幃間說明肯讀書上進。所以心甘情願地做他的「大姐姐」,在生活上對他百般照顧,也時刻關心他的學業。
1903年8月蔣介石赴寧波趕考把名字改為蔣志清。毛福梅送丈夫赴考後也學婆婆的樣,天天在觀世音菩薩像前祈禱求菩薩保佑丈夫蟾宮折桂衣錦還鄉。可報喜的沒上門,蔣介石掛一臉霜回來了。他考場失意名落孫山。蔣母忙不迭地安慰,毛福梅更小心服侍,惟恐心高氣傲的丈夫想不開做出什麼怪事來。
其實蔣介石的失意並不是因考試落第,而是因當時寧波受新思潮影響,知識分子對科舉開始厭倦,社會上紛紛議論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蔣介石在這段時間共同生活中,覺得毛福梅對他的照顧是別人無法代替的。他聽說奉化縣城還辦了女子學堂「作新女校」,許多大家閨秀都在讀書,他的女人不該落在人後。
就這樣,1903年9月21歲的毛福梅開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毛福梅到奉化縣城後被編在新女校的班裡。啟蒙班專為隻字不識的女子啟蒙,學生大多是八九歲的女孩子,有錢人家的少女慕名就讀的也不少,但絕少有上了頭、開了臉的已婚女子。上學那天毛福梅走進教室拜了孔夫子像和師長,向教室最後一排座位移步走去時,數十雙驚奇的大眼睛盯著她。
毛福梅感到身為人婦,與年輕姑娘甚至還是流鼻涕的小丫頭為伍有點羞愧難言。但是毛福梅為人穩重富有同情心深受女孩子們信賴。在師長和女伴的關心下,毛福梅漸漸習慣了蒙童生涯。誰料蔣介石在鳳麓學堂又鬧出事來,使毛福梅不得不中途輟學。
原來鳳麓學堂雖是新辦的但課程設置還很古板,還是《春秋》、《周禮》之類為主課,英文、數學等不過點綴而已。這些古文蔣介石差不多已經嚼爛了,他是抱著「學真本領」、「求實用知識」的目的入這所學校的。再加上當時在鳳麓學堂的還有許多熱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陳泉卿、俞鎮臣等,他們對校務也很有意見。大家湊在一起擬了個提綱推蔣介石為代表去向校董談判。
蔣介石在教師面前從來不心怯氣虛,這次仍然大模大樣走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後挺起胸脯滔滔地演說起來。他列舉各地洋學堂如何重視新科學,再陳述本校的若干弊病然後提出改良的要求。由於蔣介石措詞激烈情態高昂氣得林校董無言以對,只喊「反了,反了!」第二天校董們謂蔣介石「煽惑學生,詆毀校務」,以開除其學籍相威脅。周日宣和一些同學們針鋒相對,集體向校方抗議,聲言如果要處理蔣介石將集體退出學校。
林某見這些學生都是佼佼者,而周日宣還是一個院考第一名入庠的大才子、名教員,只好不了了之。這場風潮很快過去,蔣介石卻不願再在鳳麓學堂待下了。學年還未結束,他就帶妻子回溪口老家豐鎬房。
小夫妻雙雙回家,蔣母非常高興。雖然只有半年多,兒子長高了,媳婦長胖了。對一個寡母來說,沒有比這更能得到安慰的了。轉眼年關將到,正忙得不亦樂乎,忽然來了一位舉止闊綽的客人。王氏一見喜出望外,急命兒子媳婦拜見孫家舅父。
這位孫家舅父乃是蔣父蔣肇聰第二個妻子孫氏的堂弟名孫琴風,家住奉化蕭王廟村。孫琴風比王采玉小兩歲也把王氏當親姐姐看。蔣介石小時常跑孫家拜歲,對這位舅父的感情不錯,忙不迭地把鳳麓學堂風潮及自己退學始末向他講述。
孫琴風走南闖北,對外甥的「越軌」行動不但不責怪還說:「阿元啊,我看你眉宇間有一股陽剛之氣,勿像吃文飯、吃生意飯的,還是繼續讀書的好。寧波箭金學堂有個主講我認識,姓顧名清廉,對周秦諸子,尤其對《孫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去學點性理學問和變通之法,對今後的仕進不會沒有好處。」
1904年春17歲的蔣介石帶著妻子毛福梅住進了寧波植物園內一所幽靜的住宅。這是蔣介石小夫妻第一次離開奉化家鄉,開始獨立的家庭生活。沒想到蔣介石大包大攬,理直氣壯地要盡起丈夫的責任,為她雇了一個梳頭娘姨。娘姨是個見過世面的女人,見女主人的髮式土氣,大膽地給她梳了個時興的髮式。
這個髮式使她原先的圓白臉變成了鵝蛋臉。蔣介石生怕妻子冷清不慣,特地邀請一位姓林的同學的妹妹來家與毛福梅做伴。他自己白天按時去學校晚上及時回家,一面複習功課一面教毛福梅識字。每逢節假日攜她去天童、育王、報國寺等處遊覽燒香,這段時間過得和美、甜蜜,是毛福梅最幸福的時期。寧波求學對蔣介石一生影響最大,在反清浪潮的衝擊下蔣介石也漸漸不安於現狀了。他向顧清廉吐露心曲,顧清廉鼓勵他:「當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學日本適其時也。」
這席話使蔣介石堅定了目標攜眷回家,開始做出洋留學的準備。如果說寧波伴讀是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那麼這少有的溫馨就這樣曇花一現般地結束了。
1905年4月蔣介石首次赴日本留學,首渡東瀛之後豐鎬房頓時籠上了一層蒼涼的色調。蔣家婆媳守著一尊觀音像黯然魂銷。對毛福梅來說這種凄清的感覺越加強烈。雖然成親已4年真正的夫妻和諧生活才開頭,一旦久別相思尤加。不過她是個傳統的守禮法的女人,上有婆婆下有小姑不能失態有傷婦道,因此強打精神把持家計。蔣介石憑一時憤激東渡日本原打算報考日本陸軍軍官學校,不料清政府與日本國有約在先:凡進軍校學生均需清政府陸軍部保薦。
蔣介石被拒在軍事學校大門之外,只得進入日本專為旅日學生實習日文的清華學校學習。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不如暫且回去設法取得合法身份再赴日本便有立足之地了。他聽說保定軍官學校明年招生,想到何不先去那個學校就讀?
1905年冬蔣介石結束了第一次留學生活,回到溪口與家人團聚。
蔣介石去杭州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杭州考點參加入學考試。等到發榜蔣介石大名竟掛上了杭州考區60名考生中挑選出來的14名錄取紅榜上。蔣母心滿意足了,她年年盼望的就是讓兒子為蔣氏門楣爭光。清陸軍部在保定軍官學校里考選留日陸軍學生,蔣介石尚無資格報考。但他打報告說已讀過一年日文要求報考。學校總辦趙理泰居然同意了,他喜出望外,經過考試又居然入選,破格保送日本振武學校。
蔣介石金榜題名,回到溪口向親娘報告喜訊。誰知王采玉不支持兒子再去東京讀什麼「士官預備學堂」。但這時的蔣介石翅膀硬了,兩個弱女子哪怕淚水淌成一條河也阻擋不住他。1907年春蔣介石到底離開溪口踏上二渡東瀛的路。
蔣家婆媳兩人在豐鎬房終日無事便專心於佛事上。法華庵內有個叫「王大人」的尼姑與毛福梅年紀相仿,吃飽喝足後便到毛福梅卧室里拉家常。這尼姑見房內陳設雅凈,嘖著嘴說:「大奶奶真是個福人。」 哪知這話觸到毛福梅的痛處,她凄然道:「只怕我與福無緣……」
尼姑是個乖巧人自詡會看手相,定要毛福梅伸出手來翻來覆去地看著,忽然笑了起來:「大奶奶,儂勿要急,從貴手相看來,命中注定有大富大貴的兒子呢。」善於迎人心意的尼姑信口雌黃,毛福梅聽來卻好似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一線希望:結婚多年雖曾經懷過孕,卻在一次夫妻爭吵中,被丈夫誤踢小腹以致流產。
此後不久,豐鎬房裡又來了一位看風水的方士,由這個尼姑陪著踏勘蔣氏宅基。他用羅盤東測測西望望上下左右轉了幾圈,便對蔣母王采玉說:「太太,貴府是藏龍卧虎之地啊!從氣運看你家早該添丁加口,百業興旺了。」王采玉聽了非常快樂,毛福梅也十分高興。
1909年王采玉接到兒子的信,說有時間回來過暑假。但信中又說因為在上海有要事,暑假裡只能住在上海。王采玉期待早抱孫子,便把毛福梅送到上海去與兒子團聚。這年夏天蔣介石從日本回到上海度假。一些革命志士常到他的臨時住處去訪談,在這種場合作為主婦的毛福梅理應出來應酬,可她哪經過這樣的世面。她出自山村孤陋寡聞,多年隨婆婆與青燈黃卷做伴,不說與上海的都市生活差了一大截,與留學歸來的新式青年的生活相去更遠。她無法在會客場合應酬,即便在別的男人面前站一站,也羞得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蔣介石認為這有礙他的顏面,老脾氣又使出來對妻子大發雷霆,甚至連房門都幾天不進。蔣母王采玉發覺此事痛責兒子不孝忘本。蔣介石過完暑假去日本時終於綠竹生春紅梅結子,毛福梅有孕了。
1910年農曆三月十八一個壯實的男嬰在豐鎬房呱呱墜地。這年蔣介石23歲,毛福梅28歲。喜報飛到日本,做了父親的蔣介石也大喜過望,蔣母通過族輩並徵得蔣介石同意,給孩子取了個寄託厚望的名字——建豐(即蔣經國)。
蔣介石覺得有了孩子天地也寬得多了,蔣氏有了後代老母有了慰藉妻子有了寄託,他的責任也輕了許多。建豐(經國)出世蔣氏豐鎬房春意盎然喜氣洋洋。最高興的當然還是毛福梅。結婚9年丈夫像一隻風箏若即若離飄忽不定。
第二年夏在蔣經國15個月遠在日本北海道的高田野炮兵第13團士官候補生蔣介石風塵僕僕趕回溪口探望新生兒子。天倫之樂舐犢之情使毛福梅激動得如醉如痴。只可惜好景不常,蔣介石在溪口只住上三宿便急急赴滬參加起義去了。
20個寒暑過去王采玉和毛福梅婆媳倆甘苦與共休戚相關,感情越發深厚了。王氏視媳婦如同親生女兒,毛福梅也把婆婆當做親娘一樣。1921 年6月14日蔣母溘然長逝,享年58歲。毛福梅的精神支柱倒了,她撫屍大慟一場,然後披麻戴孝守在靈前,陷入了沉痛的深淵。辦完喪事毛福梅還沒喘過氣來,一瓢冷水兜頭潑下把她打進冰窟窿。
蔣介石寫信給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要求與毛福梅仳離。這封「休妻書」說:十年來聞步聲見人影即成刺激。頓生怨痛亦勉強從事,尚未有何等決心必欲夫妻分離也。不幸時至今日家庭不成家庭,夫固不能認妻妻亦不得認夫,甚至吾與吾慈母水火難滅之至情,亦生牽累是則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認子何有人生樂趣也……吾今日所下離婚決心乃經10年之痛苦,受10年之刺激以成者非發自今日臨時之氣憤,亦非出自輕浮之武斷,須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極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言也。高明如兄,諒能為我代謀幸福,免我終身之苦痛。
毛福梅聽到 「離異」二字耳朵里嗡地一聲再也聽不到他要說的什麼。事情來得突然,毛福梅只有抱住兒子蔣經國,母子惟以淚眼相視。關於毛氏被「抓了頭髮」,「從樓上拖到樓下」毛氏又「跪下」「哀求留在家裡」(蔣經國1936年致母親信上語)的事,便發生在此前後。
蔣介石為什麼要寫這個「離異」的條示?其真實意圖是為了娶陳潔如做合法妻子。所以才想出一個高招,名義上宣布與毛福梅斷絕夫妻關係,彼此關係轉成兄弟姐妹關係。這一點明眼人是很清楚的。果然不久蔣介石與陳潔如在上海結婚了。
1922年對毛福梅的又一個打擊是蔣經國離開她到上海讀書,進上海萬竹小學讀四年級。毛福梅為了改變一下豐鎬房的悲涼氣氛,把義妹陳志堅請來。陳志堅這時已從湖州保嬰師範畢業賦閑在家,毛氏請她來當家庭教師教蔣緯國念書。
蔣經國對生母感情深厚。1925年10月19日蔣經國赴蘇留學,乘輪船從廣州抵上海因需候船得與生母做久別前的短暫團聚。毛福梅流了許多眼淚千叮嚀萬囑咐無非是盼他早去早回。蔣經國對母親百般安慰也流了許多眼淚。從此母子一別12年,除開頭那兩年外,往後竟連郵電都不通音信杳然。
1927年4月12日風雲突變。蔣介石「清黨」反共,大權在握的蔣介石一時成了眾矢之的。連他親生兒子蔣經國也在莫斯科的報紙上發出聲討其父的《嚴正聲明》。
蔣經國給母親寫了封簡訊,說母親多年來內心的苦悶處境的惡劣他非常清楚。他對家庭有難以想像的煩惱和憤恨,決定不再通信了,待以後回國就第一個先來同親娘見面。毛福梅雖不知道兒子登在報紙上的聲明,但接到兒子寄來的信使她無異天塌地陷五雷轟頂。她怎麼也想像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哭著請陳志堅代筆寫信給蔣經國,可去信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她把一腔悲憤全都轉移到蔣介石身上。
1927年8月蔣介石被迫下野「出國休養」。由於護照等手續沒辦好,他帶著小兒子緯國離開南京,先到杭州小游,後乘汽車回到溪口等待出國。毛氏聽說蔣介石要回來,但想起兒子她肚裡的怨氣直往上冒。
不一會蔣介石進來,毛氏不知打哪裡生出來的勇霍地立起,邁動小腳跑下樓梯,在天井與蔣介石碰個正著。她邊哭邊嚷道:「你把我的兒子弄到哪裡去了? 你要還我兒子!」蔣介石穩住了毛氏,不久便離開住地雪竇寺四渡東瀛,這次蔣介石是向旅居日本溫泉的宋家求婚。經幾次磋商最後達成協議:蔣必須與原配毛氏公開離婚才可與宋美齡結婚。
1927年12月蔣介石返回溪口親自操辦這件棘手的事,向妻妾們宣布公開離婚。毛福梅的兩位哥哥毛怡卿、毛懋卿兄弟遵照父親的意旨據「禮」向蔣介石宣稱:「福梅已是嫁出的囡潑出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活著是蔣家的人死了是蔣家的鬼。」蔣介石聽到這話坐不住了,怕這事若鬧出人命來不好交代。
這天夜裡蔣介石走出樂亭,不帶衛士沿溪徘徊一陣後,悄悄地走進豐鎬房。毛福梅正跪在佛像前嚶嚶哭禱。3天不見蔣介石几乎認不出妻子,她目光獃滯蓬頭垢面。蔣介石不禁動了惻隱之心,他和毛福梅達成一個秘而不宣的協議,終於在「離婚協議書」 上籤了字。毛福梅仍住在豐鎬房做她的主婦,蔣介石身邊的人尊她為「大師母」。蔣介石如願以償,為掩人耳目12月1日在《申報》登了離婚啟事:「毛氏髮妻早經仳離,姚、陳二氏本無契約。」
1936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是蔣介石 50虛歲生日。不久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南京城內的電台、報紙,日夜報道著西安方面的消息。小道消息也變得煞有介事,有的標題更觸目驚心:委座取義成仁……消息不脛而走,很快便傳到溪口。
毛福梅做夢也沒想到:蔣介石經受的這場變故,竟成了她和兒子骨肉團聚的契機。不久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毛福梅見到兒子的最大願望也實現了。
1937年蔣經國帶著妻子芬娜、兒子愛倫(蔣孝文),經海參崴乘輪船到了上海。蔣介石派人專程到上海迎接。蔣經國才知父親已另娶宋美齡,母親被迫離婚。他能想像母親心中有多少哀怨積壓著恨不得立即去溪口拜見生母。可身不由己他被父親布置的圈子團團圍住。他決定先去向10年來他一直看做「敵人」、「軍閥」的父親負荊請罪。
1937年4月28日下午藏山大橋出現一輛小汽車,蔣經國迫不及待地跳下汽車,依次向在門外迎接他的親朋行禮。然後又把妻子芬娜和兒子愛倫介紹給大家。當毛福梅一眼看到門外出現那個方面大耳、壯碩身材、令她朝思暮想的親骨肉時,眼睛不由自主地被泉涌般的淚水所迷住。蔣經國跑上前來跪倒在毛福梅膝前,叫了一聲「娘」就放聲大哭。她一把摟緊兒子的頭,淚水濡濕了兒子粗黑的頭髮。她把孫子抱在膝上問:「囡囡,儂叫啥名字?」
蔣經國趕緊答:「叫愛倫。阿爹說到了祖國要按中國式取名,替他取的學名叫孝文。」
毛福梅又問媳婦名字,蔣經國答:「她在蘇聯的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芳娘,蔣芳娘。」
「芳娘,這個名字不好。」毛福梅對大家說:「她是小輩,娘啊娘的,做姑姑姨媽的都得這樣叫她,多少罪過!還是改為方良吧,方下賢良,你們說好不好?」眾人都說這娘字是該改,而且改得好。從此蔣方良這個名字便一直沿用下來。
毛福梅心滿意足了,她變著法子給兒子兒媳做好吃的家鄉點心菜肴:裹粽子、炸麻團、蒸大糕、烘千層餅、氽湯糰,還有烤芋艿、鯗烤肉等。天倫之樂其樂融融。可是樂極生悲,等著毛福梅的是又一個悲劇。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開始,國共兩度合作共赴國難,祖國經受著血與火的洗禮。武嶺雖好終非桃源。蔣經國畢竟是個熱血男兒,他在武嶺學校向師生們宣傳抗戰曾激昂地說:「我們的敵人是誰?第一是日本帝國主義,第二是日本帝國主義,第三還是日本帝國主義!」他向父親寫了份報告:「我有很前進的思想,需要有機會去求證。而且我希望在最壞的條件下去試試。」
母子再度分離是痛苦的。蔣經國再三勸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來,立即接姆媽同去住所。毛福梅則表示除了短期隨去小住幾天之外不願終生離開豐鎬房,她堅信她的虔誠祈禱會給兒子帶來好運。當時溪口雖然尚無戰火但災難已波及到,糧食匱乏米價暴漲,溪口民眾叫苦連天。將近一年過去毛福梅沒有出過溪口一步。但是戰火蔓延著,溪口隨時有淪陷的危險。蔣經國不放心連連發電,毛福梅也感覺到了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
一天下午2 時,從寧波方向飛來6架飛機。溪口人哪知是敵機?正當人們好奇地抬頭張望,沒想到飛機卻丟下一連串炸彈,頓時地動山搖。在外面的人拚命往家裡逃,在家裡的人又拚命往外面跑。溪口鎮亂作一團,文昌閣樂亭夷為平地,豐鎬房周圍的民房在燃燒,豐鎬房內男女佣人各一人當場死亡;賬房宋漲生頭部重傷,未來得及送到醫院就斷了氣,另一女傭炸斷了一條腿。
當時人們找不到毛福梅,發現後牆倒塌處微微隆起便雇民工把瓦礫挖開,發現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彈洞腸子外流想是被磚瓦壓破的。毛氏遇難那天正是「西安事變」三周年。
噩耗傳到贛南,蔣經國心如刀絞。立即帶了妻兒坐汽車連夜兼程,趕了兩天兩夜方到溪口。蔣經國一跳下汽車,連氣都沒喘一口就奔進靈堂撲到靈床前撫屍慟哭,直到昏厥過去。人們急用茶水把他救醒他仍跪在地上悲號。爾後蔣經國拿起筆,噙淚寫下「以血洗血」四個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在生母罹難處。
蔣經國考慮再三,決定把生母靈柩暫厝在摩訶殿內,待時局稍定再辦喪葬事宜。他把這一計劃報告蔣介石。不幾天蔣介石來電批諭:「鑒於時局動蕩,總以入土為安。」這12個字,代表了蔣介石對髮妻的一紙祭文。
葬母大事一直懸在蔣經國的心頭。1940年他在贛州舉行盛大的「蔣母毛太夫人追悼大會」,還在贛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橋」以志悼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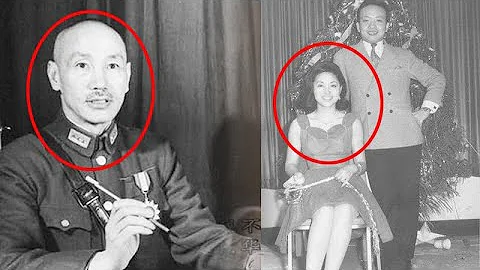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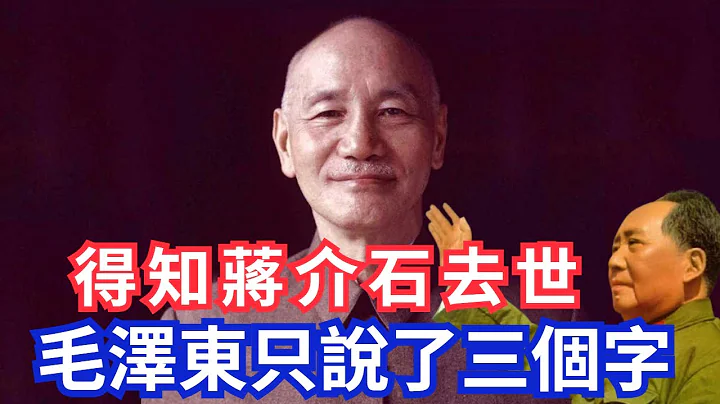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