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過夏,富人過冬」,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說法,而且在宋朝之前相當實用。為什麼?因為棉花種植出現於宋朝,在此之前古人連蓋棉被的自由都沒有。

這種說法是有一定依據的,棉花的廣泛使用是在我國的19世紀,也就是工業革命時期,而在此之前,棉花更多地出現於美洲。
這也就是說,元朝之前是有棉花的,但在我國內非常少,而且極其珍貴,是作為奢侈品傳入內地的,也只有勛貴之家才得以一見,且只能將它用於寢具使用。
宋朝之前的古人,根本就不知道棉被、棉襖是什麼存在,衣物的主流材質就是絲綢、皮草,甚至是麻。

實際上,哪怕宋朝時期開始了棉花的普及,但那也不是現在普遍的高原棉花,它準確的稱謂應該是木棉(來自東南亞),出產自桐棉、木棉、草棉樹。
大詩人杜甫當年做下千古名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其中有一句就非常真實地反映了窮苦百姓遮寒用品的材質:「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里裂」。
「布衾」就是那個時候人們的普遍寢具,說白了就是布做的被子,而不是棉花做成的被子。那種布自然也是粗麻材質,堅硬、厚重,但並不保暖。
由此可以得見,古代的窮人想要取暖,恐怕完全憑身體硬扛。「冷似鐵」的麻布被透風又不保暖,根本沒辦法起到良好的禦寒效果。

最出名的歷史典故中,有閔子騫被繼母虐待,以「皆藁枲為絮」做成棉衣,看上去厚是厚的,軟也是軟的,但就是沒辦法抗寒。
而繼母為親生兒子做的棉衣則是綿纊為里,其禦寒效果相對絲絮要好太多。雖然此故事為編纂而出,可卻清楚地說明了古時窮人的生活現狀。
窮人過不起冬,那沒有棉花的富人又是如何過冬的呢?說來又讓人倍感奢侈了。看電視劇《琅琊榜》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那些王子公主們在大雪紛飛的天氣,身上所穿皆為皮草。

冬天穿皮草,這是直到今天也流行,只是貧窮限制我們想像力的行為。更何況,在古代打獵本就是合法的,用動物皮毛來做衣服完全行得通。
只不過,這種事情也只適用於富人,窮人想要穿皮草並不容易。關於此,並不難理解,所謂賣炭的沒炭燒,賣油的沒油吃就是這個道理。
生活艱苦,窮人在好不容易得到最珍貴的東西時,往往是拿來變現補充生活的。賣炭翁冒著生命危險去砍柴燒炭,他為的是一日三餐,而非物質上的享受。

想想唐朝的李白大詩人,他也算是富家子弟出身,曾經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千金裘」這種奢侈的東西隨便就被他拿出來換酒喝。
再看名句「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那也是錦重重,滿地奢華的富家氣概。可這些東西,都只能是富人才有的生活水準,窮人只是「硬如鐵」的布衾而已。
「貧人夏披葛帶索,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灶口」——《淮南子·齊俗訓》
窮與富的差距是從古至今就有的,富人過冬靠貂,窮人過冬就只能是羊皮襖、粗毛短衣,上不遮體,下不禦寒。實在冷得受不了的時候,便只能靠在灶口。

其實,在古代窮人燒柴也不是那麼自由的。雖然那時大環境沒有今天如此惡劣,可隨便砍伐樹木用來燒火也是違法的,因為那些樹木大部分都有主人。
古代大凡近郊,或者說是被圈內的土地皆屬於富人,裡面再如何樹木旺盛,草長鶯飛,也絕對不允許窮人染指。你想要隨便砍了回家燒火,恐怕是要吃官司的。
「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四十尺為一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這是宋朝的法律,誰敢隨便砍樹那可是要被流放的。
當然,窮人可以到遠一些的深山老林去砍柴,但一天走了很遠的路,人都凍麻木了,這樣好不容易得來的柴,窮人只想著賣點碎銀子用以果腹,哪裡還有隨便燒掉的道理?

可見,窮人過冬穿衣不自由,燒柴不自由,更不用說棉襖了,那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好在,農家人還有一點辦法,那就是流行於當下的羽絨材質。
「冬被鵝毛,衣棉以為裘,夏緝蕉、竹、麻、芋以為衣」,這是出現在王安石筆下的邕州生活寫實。
也就是說,窮人在冬天便以鵝毛為被。只不過,那個時期的鵝毛是沒辦法與今天的羽絨相提並論的,那是真正的羽毛,蓬鬆但也扎人。
想起清朝有過雞毛房,那是為了避免窮人晚上被凍死,於是政府提供的一種經濟旅店,店內被鋪了厚厚一層雞毛,沒有被子也沒有褥子,滾到雞毛里就是最好的取暖。

「乞兒終日向寒啼,羽翼徒憐養未齊。三個青蚨(銅錢)眠一夜,雞毛房裡似雞棲」。
哪怕是這樣惡劣的地方,也要一晚交上三個銅錢,如果沒有,那就只能在外面凍一夜。通常,北方在外面凍一夜的話,基本也扛不住住了。
但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鵝毛、雞毛也是窮人賴以生存的取暖材料。雖然比不了富人的雪貂、棉服,但好歹可以過冬的。
不過,在古代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取暖神器,那就是爐子。雖然前面講買不起碳,也不能隨便砍樹,但窮人吃飯還是要吃的,而用來燒飯的灶則直接連著睡覺的土炕。

這應該是北方最典型的取暖工具,土炕本身保暖性極佳,而且溫度也適宜。富人用以取暖相對講究,比如漢朝時將花椒塗以牆面,據說可以起到保溫的效果。
「香壁本泥椒」,「以椒為泥塗室」,都是古代富人常做的事。只不過必須要家有萬貫的那種富,普通的小康承受不起這麼個造法,很容易敗家。
而窮人呢?那就不講究了,有點木頭可以燒炕已經不錯,若能有點碳來燒個泥爐,那就更美了。手腳放爐邊一烤也就整個人都暖了,不至於凍死,也不至於在寒冷中硬抗。
以最普遍的明清富家小姐取暖之法來講,手爐又是必備取暖神器。這種東西早在唐朝之前就有了,只要將木炭放進去,蓋個小罩子,那就是最好的「燙婆子」,走到哪暖到哪。

更甚至,在《開元天寶遺事》中,還有提到專門放在室內的大火爐,當時被稱為暖爐:「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余,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這就是窮人與富人的不同,窮人的暖爐里只能放點沒燃盡的余灰,而富人則是一條燒十日的瑞炭。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這麼冷又這麼難熬的歲月,古人還是熬了過來,從而有了我們今天棉襖、棉被自由的時代,著實不容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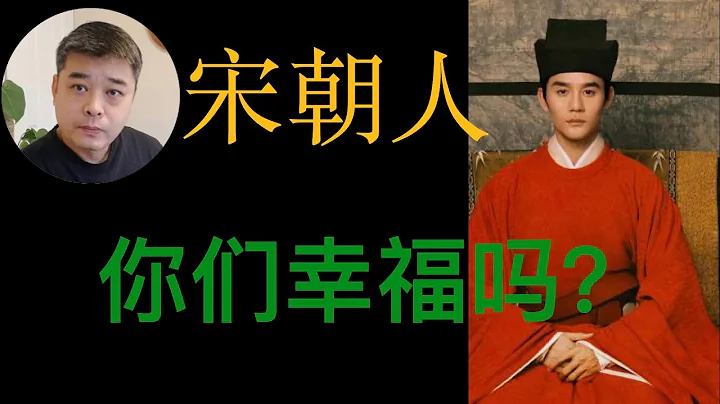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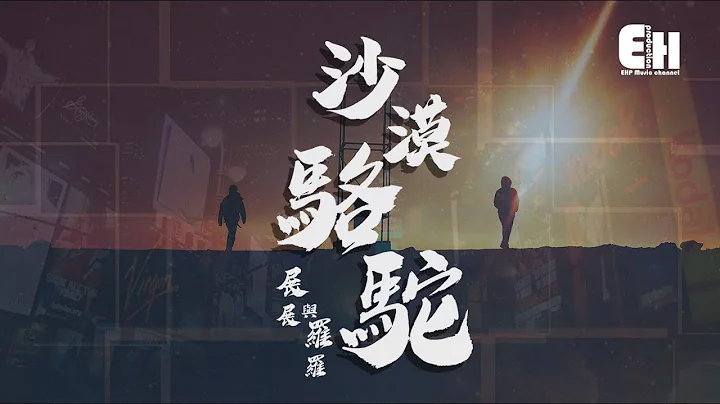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