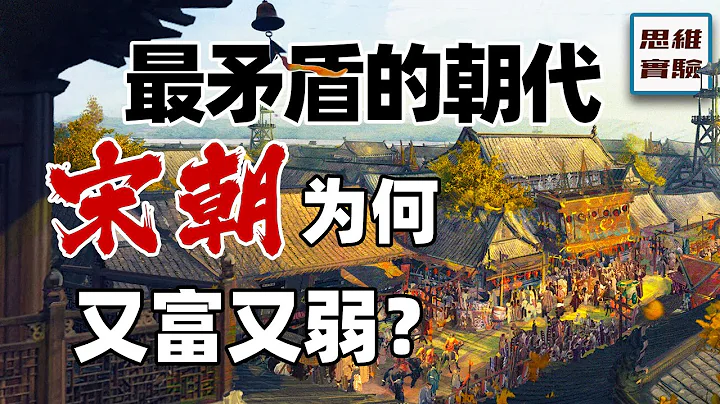公元1004年,遼聖宗和蕭太后率領20萬大軍入侵宋朝,其大軍銳不可當、所向披靡,連破宋朝數道防線,一直打到宋朝開封的門戶澶州城。
——可惜,澶州防禦十分嚴密,遼國拼盡全力也無法徹底拿下。但就在僵持之際,遼國大將蕭撻凜意外被宋軍射殺,遼國遭遇重大挫折。
與此同時,遼國入侵的告急文書傳遍中央,大宋滿朝大臣無不恐慌,很多人都主張遷都以避禍,宋真宗也被嚇破了膽,只想著逃離......
一、澶淵之盟
就在此時,著名的宰相寇準站了出來,力勸宋真宗御駕親征。
宋真宗雖然膽小,但好在是個聽勸的人,他最終還是鼓起勇氣,來到澶州,並且登上了北門城樓。
而這邊的宋軍看到皇帝都御駕親征,所有的人也是鬥志昂揚。史書記載:「將士無不歡呼,聲聞數十里,軍威大振。」
宋軍士氣高漲,而遼國卻因為失去統兵大將,蕭太后輟朝五日,士氣日漸消沉。再加上此時越來越多的軍隊來到澶州,蕭太后甚至有被包圍的危險。
最終,遼國不得不向宋朝提出談判。

當時宋真宗心裡也沒譜,所以一聽到對方要和談,立刻表示同意,於是著名的「澶淵之盟」便在此被簽訂。
關於澶淵之盟的結契,也算是經過了一系列周折。
因為寇準反對向遼國和談,所以他對和談的使者嚴厲警告,如果敢於喪失過多的國家利益就砍了去談判的使者,以至於一向懦弱的宋朝,居然能在談判中獲得較為平等的條件。
根據澶淵之盟的規定:宋遼為兄弟之國,宋每年向遼捐10萬兩白銀和20萬匹絹,從此之後兩國互不侵犯,雙方在邊境開展貿易。
在往後的歲月里,宋遼之間果然沒有再開戰,宋朝也以較小的代價換得了巨大發展空間,一直到金國崛起後,這個局勢才被打破。
而澶州與澶淵之盟也因此成為了歷史的見證點,因其意義非凡,而被後人所銘記。

二、澶州為何是戰略要地?
看到這裡,很多人不由得好奇,遼國不是勢如破竹,打得宋朝皇帝都要逃跑了嗎?為何會停在澶州,而且最終導致大將被殺,全局被翻盤。
——在這裡,不得不重點強調一下籤訂澶淵之盟的地點澶州。
根據史料記載:澶州「居中國要樞,不獨衛之重地,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在歷史上便是兵家必爭之地。
在歷史上,這裡曾經爆發過的大型戰役並不在少數。
著名的晉、楚城濮之戰,孫臏、龐涓的馬陵之戰,鄭、晉之間的鐵丘之戰,曹操和呂布的濮陽之戰,以及五代十國時期的後梁與後唐的20餘次交戰,都在這打......

毫不客氣的說,澶州是一個軍事戰略要地,往往決定了一場大型戰役的勝負。
而在北宋時期,宋朝一直沒收回幽雲十六州,導致整個都城陷入到「一馬平川」的尷尬境地,一旦北方游牧民族騎兵南下,隨時會有滅頂之災。
而唯一能扭轉乾坤的就是「澶州」,這座城池剛好是位於開封以北,毋庸置疑是京師的「北大門」。只要澶州沒有被拿下,那麼南下的大遼騎兵就絕不敢貿然進攻京師。
也正因為如此,宋真宗才會在這裡御駕親征,最終傾全國之力,外加上一些運氣,擋住了遼國的大軍,簽訂了和約。

三、澶州的命運轉折點在何時?
當然也許有人會提問,既然此處如此重要,為何在宋以前該地不怎麼出名呢?
相比較於大家耳熟能詳的荊州、益州,澶州好像是憑空冒出來的一般,這個戰略要地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關於澶州的歷史,還得追溯到春秋時期的衛國城邑「澶淵」。
正如 《水經·河水注》所載:「澶淵即繁淵也。 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此衛地又近戚田。 」
其中頓丘即今河南省清豐縣。由此可見,澶州的歷史是十分悠久的。
後來由於戰爭頻發、政權更迭、河水泛濫等因素影響,歷史上的澶州數次經過變遷,先後被稱為德勝城、澶州、開州等。

客觀的說,澶州在五代以前的確不怎麼出名,雖然它也經歷了一些歷史大事,可終究沒有被史官們所重視。
不過到了五代十國時期,澶州迎來了命運的轉折點。
公元919年,李存勖為控制河津一帶,派大將李存審在黃河德勝渡口夾河築柵,並於兩岸修築南北二城,稱為南北德勝城,中間由浮橋連結。
出於控制黃河渡口的戰略考慮與需要, 澶州城被設計成了由兩個半圓中間夾一條黃河的獨特格局。
——當時城牆周長24里,有4個城門,城垣南直北拱,狀似卧虎,俗稱「卧虎城」。
李存勖將此處當成進軍開封的橋頭堡,在這裡大規模囤積糧食和軍隊,對該處不斷進行興建和擴張,德勝城開始初具規模。

公元923年,後唐憑藉德勝城作為橋頭堡果然滅掉後梁政權,只是德勝城在戰後又被拋棄。
10餘年後,後唐政權被後晉政權取代,開封再一次成為首都,德勝城作為開封的門戶也又得到重視,迎來了新的擴建。
只是後晉政權先天底氣不足,居然當的是「兒皇帝」,而且還割讓了幽雲十六州,如此一來,北方再無任何防禦體系。
可偏偏在這時候,後晉皇帝又對契丹人宣戰,於是遭遇契丹南下危機。
沒辦法,後晉政權只能將希望寄託於澶州,於是又將澶州升級為防禦州,還將澶州的治所遷移到了德勝城。由此,使得德勝城變成了澶州城。
可惜,這一切依舊沒有擋住契丹人,後晉政權滅亡後,又經歷了後周與宋朝的變遷。

開封繼續作為首都地位,澶州也因此水漲船高,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到宋真宗時期已經成為了應對北方入侵的最後防線。
於是就有了開頭的歷史,以及由此展開的澶淵之盟。
四、澶州的後續與如今
不過隨著歷史的變遷,不單當年的澶淵之盟成為過去,就連大宋王朝也不復存在,那麼這座數次改變歷史的古城,歷經千年變遷又化身成了哪座城市呢?
——答案就是濮陽縣。
在歷史上,澶州和宋朝一樣命運多舛,在公元1077年,德勝城的南城被黃河淹沒,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北城。

到了金政權登場時,該地又被改名為開州,此後一直被沿用,直到民國初年改為開縣。但後來因為四川、貴州都有重名的縣,所以該地區又改回了戰國時的舊名,變成如今的濮陽。
經過上千年的變化,濮陽縣城已經不復澶州的軍事模樣,有很多的遺迹都已經消失了,最終只保留了四牌樓,八都坊,以及天主教堂和耶穌教堂等。
而在這些古遺迹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十字街」。
十字街,老百姓喜歡稱其為「四牌樓」,因為四牌樓為十字街的核心古建築。
它坐落在十字街中心,由4根方柱架起,綠色琉璃瓦頂蓋,其上四角翼然,其下四面敞開,整體像個亭子,而如果從四面分別看,都是一個牌樓,所以稱為「四牌樓」。

以這座牌樓為中心,濮陽老城的東西南北4條大街,分別留存有 200~400 米不等的長度,基本是「前店後坊」的格局,臨街都是店鋪,多為單層硬山頂,青磚灰瓦,飛檐翹角。
若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這座古建築始建於明代嘉靖元年,其四周掛著牌匾,東西兩面為「顓頊遺都」 「澶淵舊郡」,向眾人展示此地歷史之悠久。
南北兩面為「河朔保障」「北門鎖鑰」,著重強調其地理位置之重要。看過這些牌匾的遊人無不感慨,這些匾額濃縮濮陽千年歷史,可以說是解讀其深厚內涵的「密碼」。
結合前文歷史,我們對澶淵舊郡和北門鎖鑰的真實含義應該頗有理解,畢竟當年此處作為開封最後的北部防線,果真擋住了遼國大軍的進攻,而且此處也的確簽訂了澶淵之盟。
若當真面對這些牌匾,我們還真會有一種跨越歷史的錯覺。

接著從四牌樓往西400米穿過西大街,我們又會看到一處紅牆灰瓦的院落,這個院落的門口有一個大匾,上書迴鑾碑。
事實上,這個院子里有一口古碑以及一口古井,二者的歷史都十分悠久,乃是千年前宋真宗的真跡。
根據古老相傳,這口古井是為宋真宗飲水而鑿,而這個古碑也是宋真宗所創,其碑文乃是他親自寫的《契丹出境詩》,所以該古碑也被稱之為契丹出境碑。
當然,宋真宗和澶淵之盟都已經過去千年,這些古老的遺迹也不能完全保存。
若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迴鑾碑只剩下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有著明顯的模仿痕迹,這是後來的複製品。

不過,雖然出現了殘缺,但考古學家發現的這半塊碑文中,其上的文字還是清晰可見,字大如掌,蒼勁挺拔,秀麗流暢,即使隔著千年,也讓人為作者之書法而稱讚。
這就是千年後的濮陽城,其主城區還是保留著歷史的痕迹,能夠讓我們依稀感受到千年前的歷史碎片。
雖說真正的宋真宗時期的遺迹,只剩下那半塊石碑。
但它和四牌樓如同一個「退休老大爺」一樣,他們好像每天都躺在搖椅上休憩,但卻又似乎依舊在時不時的給我們講述這座城市的千年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