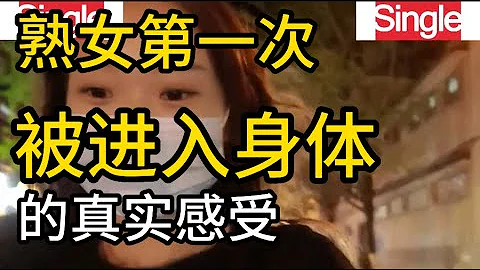葡萄和梅子,這兩種被最多應用於酒飲製作的水果,是西方與東方各樹標杆的代表。
如果說每種酒都有自己的性格,那麼香檳的性格,應該是高貴、精緻、明艷動人、不可方物。它見證了西洋深厚的葡萄釀酒歷史,和獨特的飲品表達方式。香檳的浪漫氣質,就是西方世界的浪漫氣質。
那麼,有沒有一種酒,能代表中國人的浪漫?
風雅梅見,是毫無疑問的答案。
它酸甜適口、含蓄內秀,生動詮釋了中國哲學的儒釋道、中國氣質的風雅頌、中國餐桌的家春秋。

中國是青梅的原產地,世界上大部分梅果樹都是從中國移種出去。梅子沒有葡萄那樣豐富的糖分和天然的菌群,能輕易被應用於釀酒;豐富的有機酸,讓它成為最酸的水果之一,酸與澀常常壓過甜,直接食用價值也不高。
但很早以前,中國人就發現了梅子的用處:《尚書》里,出現過「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這樣的句子。在食醋釀造技術尚未成熟之前,鹽與梅,是人們最重要的調味料。
梅子複雜的酸味,和曼妙的微甜,為它贏得了中國人廣泛的應用:以梅汁漬魚蝦,有效祛腥增香;以梅子泡蔬菜,可以彌補乳酸菌單調的酸味,帶來滋味層次更豐富的泡菜;以梅肉梅核熏烤肉類,油膩減輕,讓肉食更輕盈適口。

中國人很早就懂得「干制生香」的道理,比如腌制脫水的火腿、經過日晒焙乾的海米、經過煙熏的臘腸、經過風吹的干鮑,它們水分流失、風味物質濃縮、分子結構被打碎,香味陡生。晒乾的梅子則被稱為「烏梅」,它除了濃縮大量果糖和果酸外,還在曬制過程中,因美拉德反應產生了代表鮮爽與香濃的棕化物質。
這也是為什麼桃子、李子、杏子、楊梅等水果,隨著時代推進,被人們馴化得越來越甘甜美味,只有梅子依然保持著上古時代酸澀風味的原因所在。
這是一種被中國人賦予更高價值更多靈性的果種,更是一種被世界低估的果種。
作為梅子的原產地,中國保存了近200種原生梅種。梅見歷時5年甄選了100多種不同產區、不同品種、不同酸度的梅子,測試其陳化後的口感表現,最終在廣東普寧、福建詔安、四川大邑和雲南建立了四大基地,醞釀產出品類豐富多彩,呈現中國各地不同水土、風物、氣候、地理之下的多元飲品。

在構建梅酒酒體結構、塑造清晰悠長的酒味中,梅子的滋味,起到了調和的作用。恰如孔子倡導的「中和之美」,專屬東方的審美態度。
但無論梅子如何曼妙,真正締造梅酒風雅國飲地位的,是中國酒。
與西方的葡萄酒不同,中國酒的主角是糧食。
相比水果,糧食中可供發酵的固形物更多、栽種成本更低。唯一的問題是糧食中的糖分,主要以澱粉的形式存在。單純的酵母菌無法分解使用澱粉,只有依賴糖化酶,把澱粉分解成單糖之後,才能進行進一步的發酵。
東方人獨闢蹊徑,發明了一種高效釀造糧食酒的媒介:酒麴。
簡單來說,就是把發芽的穀物搗爛,重新放回到未發芽喚醒的穀物里。一方面,讓發芽穀物里的黴菌和糖化酶分解穀物里的澱粉,製造出有甜味的酒釀;另一方面,促使酵母菌吸收糖分,生產酒精。
兩種化學反應同時進行,這就是中國酒文化引領世界千年的雙邊釀酒法。

這種釀酒方法的優點,除了有效提高發酵能力、降低原料的損耗之外,還可以人為地通過釀酒結果的好壞,選取優質曲料,在今後的釀酒中繼續接種到新曲里,進一步優勝劣汰。
最晚到了東漢,中國人已經培養出了穩定的酒麴。更先進的塊曲替代了散曲,複雜的黴菌和酵母菌以孢子的形式被保存在水分稀少、溫度恆定的團塊里,保證了菌落的穩定性。「曲為酒之骨」的理論由此出現。
它描述了酒麴品種對糧食酒香氣和風味的框架性影響,更見證了中國人在「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哲學下,所培養出來的聰慧、堅忍和善於變通的民族性格。

經過反覆實驗,中國人還選擇了高粱作為中國酒的要義:這種紅皮穀物含有釀酒所需的大量澱粉,適量蛋白質、礦物質,以及單寧。單寧能對發酵過程中的有害微生物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並提高出酒率。而單寧發酵產生的丁香酸和丁香醛等香味物質又賦予了中國酒特有的芬芳。
這種獨特的複雜性和包容性,與青梅的風味產生了目成心許的默契,也成為梅見匠心所在。在星霜荏苒的醞釀、浸泡、老熟過程中,果肉里的風味被慢慢析出,並與中國糧食酒獨特的風味結合,形成梅見酸甜平衡、圓融適口、回香悠長的特點。
這是屬於風雅梅見的傳奇,也是中國式的,曲折通幽、大道至簡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