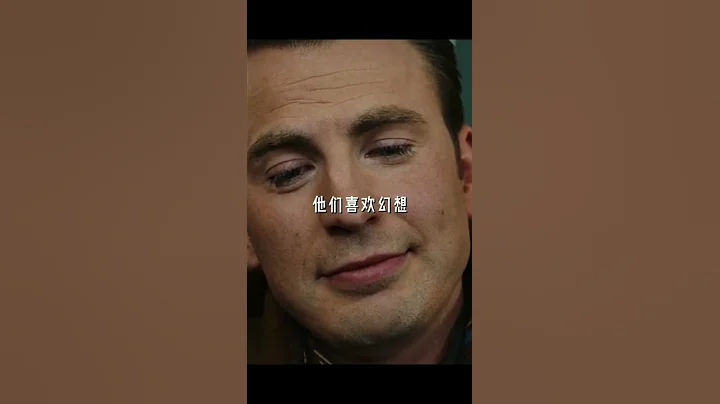撰文|張繼偉
2022年12月5日晚,知名抑鬱症互助平台「渡過」官方公眾號發布訃告,「渡過」創始人張進辭世,享年56歲。
1966年5月,張進生於江蘇南京,長於灌南。1982年16歲從淮陰考上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至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攻讀碩士。1988年,張進加入《工人日報》,先後擔任國際部編輯、副主任,再任記者部主任並升任編委。曾走遍《工人日報》30個全國記者站,主持采寫大量重要報道。2000年,張進加入《財經》雜誌,後擔任副主編。2009年又參與創辦財新傳媒,任常務副主編,後改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改革雜誌執行總編輯)。
2012年張進罹患抑鬱症,半年後病癒返崗。他直面切身病痛,邊治病、邊學習,成為朋友們眼中「最懂抑鬱症的新聞人和文章寫得最好的抑鬱症專家」。2015年,開設微信公眾號「渡過」。公號文章結集後出版為《渡過》系列叢書四輯。
2017年3月,他選擇離開在財新的全職工作,畢其力於抑鬱症救助事業,4月,啟動了抑鬱症患者尋訪計劃。2018年3月5日,他在「渡過」公號提出「陪伴者計劃」,後在杭州富陽建立「渡過」基地,為心理困境青少年回歸社會提供更長程的全方位專業支持。2022年4月,張進被確診肺癌。5月23日,接受了手術。

有些人是帶著使命來到人間的,我相信張進就是這樣。
張進1966年生於江蘇,父親是南京金陵大學高材生,但1957年即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蘇北農村教書,從此一生襟抱未曾打開。上一代不公的命運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張進的人生規劃,從南大中文系本科到人大新聞研究生,在專業選擇上老父親並不認可且頗有執念。或許出於對政治運動的恐懼,父親一直希望他讀理工科甚至語言學。直到1990年代張進在《工人日報》工作不久後即獲評副高職稱,父親才吃驚地發現,張進成長的速度已超出他的理解。
我曾不止一次聽張進講過這個故事。 他們父子情深,足為楷模,但也有些舊式教育「君子遠其子」的距離感。不過從旁觀者的角度,張進深受父輩和舊學傳統影響,對自我實現的追求,對政治生活的警覺,對社會責任和公共議題的關懷糾纏在一起,這種隱含的張力是相伴一生的。
在他30多年的職業生涯里,無論就職於媒體還是創辦公益組織,張進多次跌倒、多次爬起,但一直為他深愛的事業和弱勢群體不斷奔跑,直到成為一個傳奇。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在同事的眼中,張進從來不是一個鋒芒畢露的人,但才華是無法遮掩的。
1988年從人大畢業後,張進進入了《工人日報》,30歲就執掌了《工人日報》遍布全國的記者站,後迅速升至編委,這在當時的新聞界是不多見的。張進對於仕途沒有興趣,多年以後,他對我們回憶最多的是在京郊煤礦的實習經歷,以及當時壯遊全國的新奇感。
1990年,他和幾個同事被下放到門頭溝一個叫王家坪的煤礦,待了一年之久。作為當時還很稀缺的研究生,他和工人一起下礦,到不能直立行走的「掌子面」工作。他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的工種是岩石段的做柱工。所謂做柱,是指把巷道掘開後,用木柱把巷壁撐住,以防倒塌。要做柱,先得運木頭。礦工們運木頭的方法是我不曾想到的。如果是短粗木頭,他就把胯儘力向右扭,右手挾著木頭,木頭的另一端斜擱在胯骨上,左手撐著地面向前爬;如果是細長一些的木頭,他就把粗的一端擱在肩膀上,細的一端擱在前面,兩手撐地,全身匍匐;肩膀一聳,腿一蹬,一步步把木頭頂上去。」
這種原始的工作方式,令張進深感震撼:這是北京嗎?這是礦工嗎?
更為印象深刻的是礦難。「第二天一早,人終於被挖了出來。突然,礦門大開,四個膀大腰圓的救護隊員,臉色鐵青,抬著一個擔架出來。一塊白布把擔架遮得嚴嚴實實。一瞬間,守在井口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片哀嚎,哭聲震天。身處其間,我不能不動容,陪著流下淚水。我由此明白了什麼叫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張進有一種天賦,就是總能用精確的、不動聲色的方式講故事。不知道是不是和他學過素描有關,有時他聊天也會不知不覺進入一個勾勒細節、烘托氛圍的狀態,寥寥數語,就如銀鉤鐵劃般刻出一個元宇宙。
這段礦工經歷對別人可能是不堪回首的,但對張進而言無疑轉化為了一筆人生財富。他在那裡觸摸到了生命的質感,並把這些苦難的家庭當作了自身的一部分。這種「民胞物與」的情懷是如何形成的不得而知,但「訪貧問苦」成為他最為關心的報道話題,應該是在那時候奠定的。
在後來的《財經》、財新傳媒工作期間,他最早關注過「盲井」式的案件,組織過多次礦難、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的報道,更編輯指導過像「邵氏棄兒」、非法器官移植這樣的經典報道。是什麼讓他如此執著地關注這些話題呢?他平時愛稱引魯迅的話「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王家坪礦井應該一直留在他的心底吧。
在《工人日報》執掌記者部,一個「福利」是能到全國巡遊。張進不喜歡東南沿海的繁華,而是嚮往深山大川的空曠。他喜歡馬原筆下的西藏,並多次前往。1995年的玉樹雪災,給了他深刻記憶:「我下車,彷彿站到了月球上,荒涼、蒼茫。此地海拔5000多米,缺氧,每走一步都很費勁。緩行到一座小山坡上,我看到一輪昏黃的月亮,像一個圓臉盆,懶洋洋地懸在前面的矮坡頂上,好像一伸手就能撈到。我用很大的意志才剋制住飛奔而去的慾望。夜空透明,星光璀璨,這裡是真正的萬籟俱寂。」
張進喜歡這種空靈、自然的境界,似乎對於塵世的起起伏伏永遠有一種抽離感。對於周遭的人與物,他既用情投入,又時刻把自己置於一個觀察者的角色。今年春天他患肺癌之後,就提到了這種視角——把自己的想法(認知)、感受(情緒)和真實的自我分開來,好比抽身而出,居高臨下,觀察和體驗另一個自己。「回顧一生時,我就用了這個『抽離法』,就像在劇場旁觀銀幕上的自己,看到了周邊的各種環境、關係,過去和現在,以及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然後,再回歸當下,身心合一。」這是從「自我沉浸」視角轉化為「第三方視角」——「第三隻眼睛看自身」。
看透是睿智,不說破是慈悲
2000年張進加盟財經,在朝陽門外的泛利大廈10層,我也得以有機會和張進並肩戰鬥多年,從他那裡耳濡目染各種業務和非業務的智慧。
初見張進,很難不產生親近感。他身材不高,語出必中,總是認真傾聽認真作答的樣子,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大概就是如此吧。
熟悉了之後,經常海闊天空地閑聊。我們還有2003年加盟《財經》的張翔,都喜歡《儒林外史》,酒酣耳熱之際,經常相互徵引其中的段落對時事人物戲謔點評。與我讀書不求甚解不同,張進對於鍾愛的作品總能準確地複述出來。他最喜歡書中王冕媽媽的遺言——「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為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著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還有就是最末一回的市井四奇人,尤其欣賞那種矯然不群、橫而不流的民間雅士。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張進總是不太修邊幅的樣子,常年穿一件夾克,步履匆匆,頭髮略顯零亂。他對物質沒有什麼追求,除了愛吃櫻桃和生魚片,很少見他有什麼大的開銷。對於妝容精緻、滿身名牌的人物,他則總是有一種近乎天真爛漫的旁觀者心態,類似《圍城》里對曹元朗的促狹。
張進對於世情百態非常通透,對於人性沒有很高的期望值。同事王和岩說「看透是他的睿智,不說破是他的慈悲」。他喜歡引用《水滸傳》里李逵聽到自己喝的是毒酒,馬上就覺得「身子沉重」,說這是人的自然反應,事到臨頭誰都逞不來英雄。對於七情六慾,亦是如此,求不得是為苦,得到之後更會失望。他喜歡余華的《活著》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對生活的荒謬本質一針見血。他視《道德經》為超越人間的智慧,「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一切都應順其自然。因此2012年最初獲悉他得了抑鬱症,我由於缺乏對這一病症的基本知識,一度覺得難以置信。
2000年時是張進事業的一個低谷期。剛從體制內出來,面向不同的讀者,又是自己從未涉足的財經領域,應該處處都是挑戰吧。不過張進很快就找到了擅長的角度。在舒立(編者註:胡舒立,原《財經》主編,財新傳媒社長)的安排下,他聚焦於民生、三農領域,對公共政策做深入研究,還主持過「邊緣」欄目,一如既往地關注弱勢群體和社會法治話題,很快他管理的部門和領域就不斷擴充,特別是在2003年SARS報道之後,《財經》在社會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張進也找到了再次起飛的方向。
公共政策和社會法治的報道,總是會人言言殊、眾口難調,尤其是當專業判斷和普通人的直覺相悖之時,比如天價醫藥費、新勞動法等,即使是編輯部內部,也不容易統一意見。張進帳下的調查記者眾多,每個人都能言善辯、韌性十足,不把問題搞複雜絕不罷休。每次開會都能聽到他們唇槍舌劍、熱火朝天地討論。這時候性格謙退的張進就會展現出柔中帶剛的一面。他尊重獨立思考,從來不把自己的意見凌駕於同事之上,但亦不會輕易退讓。每當此時,我們都會感嘆,只有張進能夠如此耐心、如此思路清晰地予以調和、鎮壓桀驁不馴的八方諸侯。
張進最讓人服氣的是他手起刀落的編輯速度。只要由他來主持封面,總編室就會慶幸能睡個好覺。他天生有一種從雜亂無章的初稿里排沙揀金、化繁為簡的能力。對此,他總結過一種「框架式寫作法」的技巧,傳授給一代代的年輕記者。與之相應,在指揮大規模的突發報道方面,他的部署、調度和應變能力也讓人讚歎。同事們經常回憶起他和王爍在掛著西南地區地圖的辦公室里部署地震、洪災報道的場面,頗有指點江山、大軍團作戰的風采。
對於記者,張進付出的是保姆式的關懷,尤其遇到各種變故,張進都會設身處地地為記者謀劃。《財經》、財新20年,進進出出的記者不勝枚舉,當時的年輕人變成各奔前程、事務繁雜的中年人,但大家對於張進的感情始終是親人般的深厚。

如今塵破光生,照遍山河萬朵
回顧來看,2000年到2009年《財經》時期應該是張進新聞才華充分釋放的時期,這似乎和中國當時的經濟騰飛、蓬勃向上、自由奔放的時代特徵相契合,即使去掉回憶濾鏡,也是以美好溫馨的畫面居多。
2005年,張進曾經難得地出國訪學了一次,當時留下的趣談尤為豐富。多年不用的英語早已生疏,把小費說成「little fee」的梗被傳頌了多年。還有一天,他遇到晨練的美國老太太,由衷地伸出大拇指「good body!」忍俊不禁的老太太告訴他這樣的flirting是不禮貌的。
後來我在財新網上讀到張進對這次訪學經歷的一篇追憶。這是他某晚在德州一個邊境小鎮的酒吧聽到的歌曲,講述一個牛仔為追逐愛人被殺的故事,他聽了很多遍,又專門上網把歌詞記錄了下來。張進在回憶里寫道:「德州小鎮,我呷著酒,似聽非聽,似想非想。我想像著這個牛仔的命運:為不能自拔的愛情所驅使,經歷了千辛萬苦,寧可付出生命,最後果然以失去生命而告終……這不也是當今很多都市人的命運么,儘管他們的命還在……一路困惑,無所依、無所信,潦倒困頓,且敗且行;逐漸地,心腸逐漸變硬,感情也逐漸枯竭了……
最後費莉娜終於把我給找到
親吻著我的臉頰跪倒在我身旁
我將死在費莉娜溫暖的懷抱中
送上輕輕一吻費莉娜別了
回蕩在酒吧里這首歌,節奏總那麼一成不變,似感嘆如低吟。在吉他的伴奏下,歌者的嗓音顯得非常感人。這是一種奇異的憂傷,歌者唱出了心緒,聽者一次次被浸染,字字句句像鮮花那樣晶瑩和豐潤,刻進我的記憶里……」
即使是在最為愜意的時光里,無論身處何地,張進最激賞的還是那種帶有淡淡憂傷的韻律。作為社會觀察者,張進無疑是遊刃有餘的。也許是命運不願他在原地停留太久,要賦予他新的使命。
此後幾年變故迭生,讓他從一個冷靜的記錄者變成了不知疲倦的行動者。
2009年底,原《財經》團隊集體出走,從零起步創辦了財新傳媒。此後幾年,張進作為常務副主編、綜合報道板塊的負責人,管理責任也隨之加重。「只言旋老轉無事,欲到中年事更多」,其間父親生病去世對他的影響更為深重。
2012年初張進逐漸覺察到了抑鬱傾向,到「兩會」期間日漸加重,以至於無法工作。大概是初夏有一次我去看他,敲門許久也沒有人應。我以為他不在,在門口放了一本書就走了。後來他告訴我,當時他就在門內,但沒有行動能力。在最困難的時候,他說世界在眼中是沒有顏色的。
這種痛苦外人實在無法感同身受。然而畢竟是張進,在藥物幫助下,他在經歷了半年的折磨後,有一天忽然有了想看手機的想法,事後他解釋這是開始「轉相」了。趁熱打鐵,他開始自學抑鬱症的國內外醫療知識,憑藉一個優秀新聞工作者的學習能力,逐漸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論。
這真是一場英雄之旅。痊癒後的張進,很快把他的經歷寫成了「地獄歸來」一文,浴血重生的經歷、驚心動魄的文字,迅速引發了病友、家屬和醫學界的廣泛關注。
對於他展示傷口的舉動,我最初是很擔心的,生怕外界的反應會帶來刺激。不過此時的張進,已經開始有了新的思考。一來是要破除「病恥感」(這對大多數病人都是心知而口不能言的),二來是他對抑鬱症有了切膚之痛,正如他早年下到王家坪礦井一樣,已與病友的命運融為一體了。「迷時師渡,了時自渡」,六祖《壇經》里的這句話,觸動了他出版「渡過」系列著作的想法。
病癒後的張進,有一些肉眼可見的變化。他對於外在的名利依舊淡然,但是果斷地從坐而論道變成了行動主義者。從最初的為朋友諮詢,到和專家交流、開講座,再到出版書籍、辦公號、創建「渡過」這個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抑鬱症康復機構,最終張進選擇離開新聞業,全身心地投入到對抑鬱症患者救助的事業當中。
迷時師渡,了時自渡
2014年他還愛上了攝影,無師自通地把寫作和攝影當作治療的一部分,因為表達、傾訴和觀察,都會激發對生活的熱愛——「當翻閱照片,我看到生命之河從我的眼前流過。於是,我與世界、與內心實現溝通,收穫了理解與感動。」
有一年冬天,我和他開完會回辦公室,當時天降小雪,他堅持步行,手持相機,隨時拍下觸發他的瞬間,身形矯健、活力四射,讓小他11歲的我自嘆弗如。
對於抑鬱症的機理和療愈我始終所知不多,因為實在是缺乏凝視深淵的勇氣。不過張進的敏銳和悟性顯然贏得了專家和病友的認可和信任。他考取了國家三級諮詢師,2017年還入圍了中國心理學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人。
2017年4月,他啟動了抑鬱症患者尋訪計劃——去全國各地,尋找有代表性的患者,進入他們的生活環境中,描述他們的人生境遇,以及他們的社會關係對其疾病和命運的影響,從而為當代中國的精神健康現象,提供一個真實、完整的解釋。這是張進告別新聞生涯後又一次全國性遊歷,正如他在20多年前對自然風物的熱愛,這次他走進了更多人的內心。
一年後,《渡過3》出版,「渡過」也從傳播知識階段,進入到實際解決問題的階段。2018年3月5日,他在「渡過」公號提出「陪伴者計劃」的概念,此後還在杭州富陽建立了「渡過」基地,為心理困境青少年回歸社會提供更長程的全方位專業支持。
張進的思路並非全然創新,一位北京三甲醫院的專家探訪了浙江基地後,感慨說「渡過」做的正是他們想做的,但是由於無人擔責而無法落地。對此張進也很瞭然,「相較前兩個階段,尋找抑鬱解決方案階段有質的不同,從此『渡過』走進了一個兇險莫測的領域,這對我們又有巨大的誘惑——價值實現」。是啊,實現社會價值,一直才是張進心之所念。他把浙江基地視為病人療愈的「中途島」。不過在我看來,這也是他的「理想國」,是他一磚一瓦搭建的「新和諧公社」。
從自渡到渡人,張進的這次綻放更加耀眼,也越加忙碌。然而2020年以來的疫情,不斷打斷他的工作進程,動不動的隔離和彈窗只會徒增沮喪。更糟糕的消息在2022年4月傳來,張進被確診肺癌,而此前他因為忙於浙江基地的項目,已經耽誤了有一個多月。此後北京疫情加劇,腫瘤醫院地處高風險,手術也一直推到「五一」後才得以實施。
5月23日手術結束後的下午,我居然就收到他發來附有照片的微信,報平安之餘還說出院後要寫一篇疫情中的護工,反映他們在疫情中的遭遇。我連忙告訴他好好休息,但他還是略帶興奮地表示,以後「渡過」要關注癌症病人的抑鬱問題。
今年手術前後,我陸續見過張進四次,算起來是他離開財新後見面最為頻繁的一年。每次見面,我都驚訝於他的忙碌,他在著手寫《渡過》第五部,在管理200個近十萬人的微信群,在緊鑼密鼓地安排順利交班,以便從事務性的工作中解脫出來。談笑之餘,他也會擔心肺癌後的進展,以及靶向葯帶來的咳嗽和手指損傷。
8月2日張翔來京,一起吃完飯後我送張進回家。快到終點時,他忽然陷入沉默,似乎被車窗外的暗夜深深吸引。那一刻我莫名產生了不祥的預感,這些年來他一直在不停地燃燒自己,綻放出了難以想像的能量,為什麼命運對他如此不公呢?太史公在《伯夷列傳》中質問:「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我也有同樣的疑問,也許是這使命太過沉重,也許這個世界本來就配不上張進的善良和純粹……
張進去世後,時隔兩日,我才慢慢接受他的離去,並發了一個朋友圈,是為紀念——

張進是最為本色任真的人,不喜偽飾矯情之流。他喜歡《儒林外史》里的市井奇人,喜歡《道德經》,喜歡萊蒙托夫,喜歡魯迅的《孤獨者》和《在酒樓上》,喜歡西藏的壯美和神秘。他對人間的苦難有發自內心的同情,對人性的缺點也有著清醒的自覺。他從不扮演崇高,卻做了最崇高的事業,他從來謙抑自晦,卻閃耀著最溫暖的光芒。張進,我們的好兄長走了,應當有更多的人認識他記住他。
文/張繼偉(財新網總編輯) 供圖/渡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