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出版制度的時候說道:「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說的是沒有出版自由的結果,也代表了一定的言論自由傾向。

馬克思是從爭取言論出版自由開始政治生涯的,無論馬克思學會英語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作品,還是學會俄語在俄國的報紙上發表作品,都在利用言論出版自由爭取政治權利。而資本主義社會並非要實現人人言論自由,而是要加以限制。有了書報審查制度,就會限制馬克思主義者的言論,宣揚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觀點。同時很多出版物也被限制,被篩查。資本和權力注入出版界,審查出版物,只讓出版一些不痛不癢的文章,或者有著娛樂消費導向的東西,而一些帶有思想印記的東西並不能出版,就更別提影響人了。很多所謂偉大的作家並不是真正的偉大作家,而是被資本和權力承認的所謂偉大作家,也是為資本和權力鼓吹的作家。蘇聯的麥德維傑夫寫道,這些偉大作家:「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又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信徒,可是他們的作品卻豐富了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作品只是在作家死後才問世。」「起敗壞作用的只是受檢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惡————偽善是同它分不開的。」作家生前出版的作品大多受到書報審查制度的約束,並不能表達自由的觀點,也不能直面社會真相,說出內心真實的話語。而他們沒有出版的作品在死後出版,倒是說了真話,抒了真情。被審查之後出版的作品要麼改頭換面,要麼大量刪削,要麼重新改寫,都是為了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而不是表達真理或社會良心。
人們看多了這樣的作品會以為描寫的是真的,社會就是那個樣子,其實已經被作品欺騙了,或者說被作家和資本家合夥欺騙了。他們需要傳達資本家的聲音,表達資本家的利益訴求,甚至直接傳遞消費主義價值觀,傳遞享樂主義價值觀,目的在於刺激消費。而消費增長了,資本也就迅速增值了。

麥德維傑夫寫道:「政府只想聽見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卻欺騙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騙。至於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上有時陷入迷信,就是什麼都不信,或完全離開社會生活,變成一群只顧私人生活的人。」資產階級政府控制媒體,製造一些新聞事件,或者說只是發布一些經過審查的新聞,卻不會把所有的新聞全都發布出去。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只是要人們看到他們想讓人們看到的東西,而且還要強調這種新聞是正確的,全面的,權威的。於是,人們統統被洗腦,卻還以為自己看到了真實的新聞,看到了領導人的雄才偉略,看到了資產階級政府的豐功偉績。他們盲目迷信,不是迷信政府,就是迷信權和錢,還有的迷信神靈和命運,卻最終要否定自己,因為自己沒能耐。只有成為資產階級的成員才會成為有能耐的人,而越是追求,就越是陷入資產階級設置的陷阱。資產階級要底層人努力奮鬥,爭取進入上流社,。而事實上他們早就堵死了底層人的上升通道,提高了進入上流社會的門檻,也就可以保證資產階級的純正屬性,而不會弄很多自以為是的底層奮鬥者進來。
這一切似乎都和資產階級限制出版自由有關係,而越是限制,人們就越不自信,甚至投向了神學的懷抱。資本主義控制出版自由會產生人們失去信仰的結果,還會催生很多怪異的派別,甚至生出很多不是文學的文學,不是文藝的文藝,只是政治傳聲筒,或者只是為了宣揚資本運作的好處,只是帶動人們消費的作品,卻不是事實,也不能打動人心。資產階級會毀壞原有的藝術形式,用資本堆積起來的藝術形式表達資產階級的訴求,甚至直接為資產階級支配的經濟發展張本,卻無視藝術本身的規律。要是用資產階級打擊和摒棄的藝術形式來重新創作藝術作品,似乎才算是走上了藝術創作的康庄大道。
現代派和後現代派似乎是資本主義控制出版自由之後生出的變種,卻日漸強大,甚至以自殘來反襯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和不公。只是,這樣「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藝術方式漸漸發展成變態的藝術形式,甚至一些作家筆下的人物不是身體殘疾者就是精神變態者,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而真正可怕的並不是這種藝術形式,而是人們認可了這種藝術形式,甚至無動於衷。於是,魯迅筆下愚昧而又麻木的一群人再次出現,雖然穿著華麗,住著樓房,不愁吃喝,但依然具備民族劣根性,甚至比阿Q還要自戀和愚昧,也就真的弄得階層固化,社會結構穩定不變了。

原來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穩定是保證資產階級利益的穩定,而不是保證勞動人民利益的穩定。勞動人民只是資本家眼裡的羊,資本家要「薅羊毛」,而且要世世代代「薅」下去。為了保證這種正當性,資產階級就要控制出版自由,最終塑造屬於資產階級的世界,也最終要穩固地統治下去。不過,以前封建統治階級也是如此實行的,只不過到了一定的時間,不得不被先知先覺者推下台。或許,統治階級的腐朽性是從控制出版自由開始顯露的,只不過他們自以為是,又聾又瞎,假裝聽不見看不見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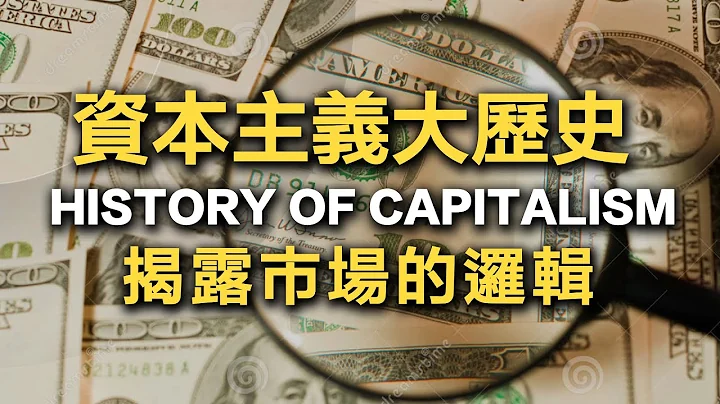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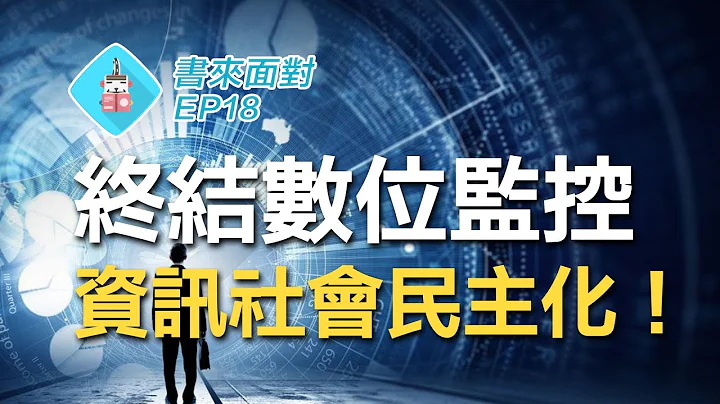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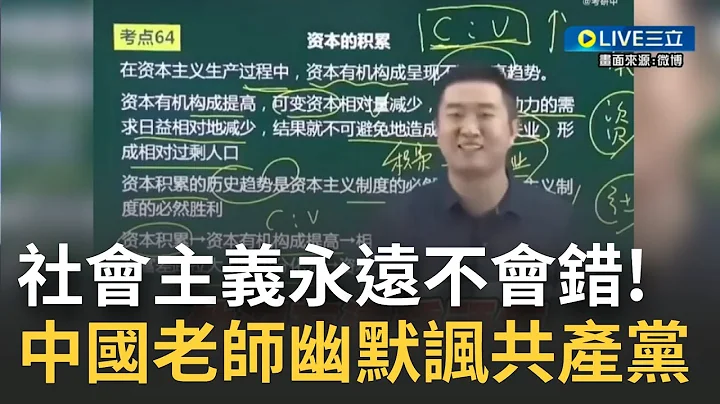





![[Chinese movie 2023]Poor girl helps disabled shareholder, changes fate!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2qSlT5aVHg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zmX0URNZaXthUulfqkBykMpzB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