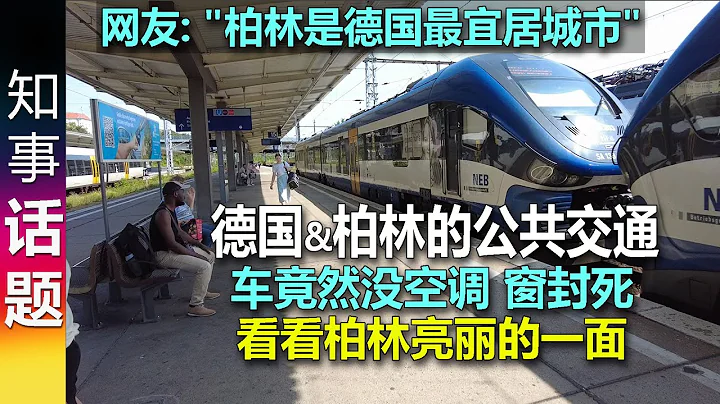前言
城市貧困問題的產生並不是隨機和暫時的,而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不僅有長期的歷史積澱,而且也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不斷嚴峻和深化。貧困所引發的一系列狀況和問題需要相應的舉措來應對,所以反貧困政策應運而生。就 19 世紀德國城市的反貧困政策而言,其提出和實施既有很深的歷史淵源背景,也受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影響,其社會表現形式也具有當地特色。

宗教改革伊始德國的濟貧傳統
自中世紀始,貧困就一直伴隨著人類社會。出於憐憫和道德宗教責任感,向窮人、老年人、寡婦和孤兒提供物質以及非物質形式的救濟,是世界上所有文明的一項社會倫理規範和實踐。基督教文明更是從最開始就特彆強調這一職責,通過各種形式的體系、機構及活動塑造了個人和團體的實際利他主義形象。就教會而言,「通過教會個體成員的救濟援助來完成利他主義的工作是基督教會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說是「教會的一項基本功能」。

所以,從宗教改革開始,神學改革家們就密切關注貧困、乞討等社會問題。馬丁·路德在《九十五條論綱》中也反覆強調幫助窮人和善行的重要性,「遇見需要幫助的人而棄之不管,卻將錢用於買贖罪券,買的不是教宗的特赦而是上帝的憤怒」。在濟貧觀念上將救贖和善行分割開來。可以說,宗教改革是解決貧困問題的一個突破口,其中濟貧改革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西方社會貧困救濟具有悠久的歷史,宗教是其形成的基礎,濟貧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神恩濟貧觀念。德國在宗教戰爭耗盡精力之後,所有政治力量都集中於國家君主手中,開始通過更密集的社會制度以及活動來克服國家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困難。

其中,消除貧困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任務,國家的相關機構和運作方式也在逐漸的形成過程中。德國的濟貧模式也極具特色,「最先開始嘗試有關社會救濟制度化的地區是維滕伯格,該地提出了共同錢箱計劃,於 1520 年末或 1521 年初由維滕伯格市政議會通過,其得到路德教的支持。」共同錢箱的募捐所得會用於社會救濟,為弱勢群體和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並且會定期籌集資金。
從城市的各階層中選出管理人員,「他們要掌握申請救濟者的收入、人品以及出身等,還需要判斷出救濟者是否有從事工作的能力」。雖然這一救濟政策是臨時的,亦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為以後德國其他城鎮的貧困救濟政策奠定了基礎,對其進行了補充和繼承。可以說「共同錢箱」是新教濟貧邁向制度化的第一步。馬克思·韋伯曾說:「人們對貧困和濟貧問題態度的轉變受到新教思想的影響,濟貧制度開始作為一項社會政策投入運用,並具有一定的現代意味。」

19 世紀上半葉德國工業化興起的影響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西方國家相繼進入工業革命時代。各國開始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這引起了社會的貧富分化,人口、就業等都隨之發生轉變。這也導致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城市貧困化及相關的社會問題出現,產生了大量的弱勢群體。社會經濟轉型時期城市貧困群體的主要成員包括年老體弱者、失業和低收入者、單親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以及外來移民等。

工業化時期國家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引起了日趨嚴重的城市貧困問題和社會排斥現象,同時也影響到城市的土地利用、居民的空間分布和貧困的分布。隨著大中城市的迅速發展,大量的貧困現象相伴而生,雖然城市化的速度在不斷加快,但是貧困人口的數量並沒有相應減少的趨勢。
隨著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興起,鄉村和手工業作坊的勞動者逐漸聚集起來,同時也產生了一大批窮困的無產者。資本積累的反面也是貧困的積累,財富積累的一個沉重代價便是有更多人成為社會貧困者,社會貧富差距逐漸拉大。新興的工業社會需要大量的資本流動、土地市場以及新興技術的發明和運用,當然也需要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其中包括遷移到工業地區適應工作需求的跨境流動工人。

19 世紀德國人口急劇增加為工業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反過來,工業化也推動了德國城市的快速發展。社會進程的加速,生活水平的提升,德國人口的平均壽命有了顯著的提高,與之而來的就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即社會老齡化問題凸顯。相當比例的老年人生活在貧困狀態下。城市民眾的健康狀況惡化也受到貧困的影響,需要社會的廣泛關注。一個國家的人口死亡率是衡量這個國家健康狀況的重要標準之一。嬰兒死亡率作為城市人口死亡率的一大重要分支,其變化與城市人口死亡率的變化息息相關。

城市化快速發展過程中產生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城市化也給德國城市帶來了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如公共衛生環境惡劣、傳染性等疾病蔓延、公共服務缺失、大規模失業等。面對如此棘手的各類問題,城市管理者不得不採取新的城市管理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在眾多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中,表現最明顯的是貧困問題。
城市中大量的人口湧入,農村的勞動者進入城市以尋求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更好的生活環境,這必然會出現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由此導致居民貧富差距的分化,居民會受到社會因素以及自身情況的影響在社會生存中處於貧困狀態。

而且出身於貧困家庭的人所受教育及工作條件較差,其生病率高,死亡較早。原來城市中的
居民以及後來轉移的居民都會面臨生存環境衛生條件惡劣等問題,還會因為失業、疾病、年老等失去收入來源,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這些問題就增加了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導致酗酒、盜竊、搶劫、鬥毆等事件時有發生,犯罪案件增加,社會治安出現一系列問題。
為解決這一問題,市政採取相應的舉措進行社會救助。在 19 世紀初期德國開始制定對於貧困人口的最低救濟標準,但大多數州沒有能力實現,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城市開始探索更加具體可行的方案來解決貧困問題。

城市中還出現了階級分化不斷嚴重的狀況,隨著新技術的投入和新城市的發展,尤其是新的生活方式出現更加速了這一分化,社會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以城市交通方式為例,在柏林市內乘坐軌道交通每月所需的費用相當於一名建築工人每月工資的五分之一,這使得工人根本沒有能力享受城市發展所帶來的便捷生活。除此之外,以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為代表的舊有中產階層受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影響逐漸衰落,而城市的「新型中產階層」如公司職員、科研工作者和公務員等隨之而生。這些變化讓城市成為階級衝突最集中的地方,各種形式的罷工和遊行屢見不鮮。

德國社會貧困問題
在德國工業化開始之前社會貧困問題就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尤其在工業門類較少的地區往往最為嚴重。隨著國家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貧困問題愈加嚴重。1780 年到1850 年間,德國人口從 2100 萬增長到 3500 萬,增幅達 67% ,而正是在社會秩序中缺乏財產和安全位置的社會群體增長最快。
人口增長伴隨著農業、技術貿易以及原始工業製造業的結構性危機同時發生。貧民階層的產生受到若干不同因素的影響。在南部地區,可利用的土地所生產的糧食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更無法產生出一定的必要利潤,無生存技能也沒有足夠財產的人被迫離開家園,他們自然成為社會貧困階層的一部分。

面對外國的出口以及早期的國內機械化生產,手工紡織業生產的衰落是導致貧困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其破壞了原始手工業者的經濟生存能力。第三類陷入貧困危機的主要群體是行會手藝人,職業自由的建立導致了許多行業的人滿為患,但是由於熟練工將自己設定為行業的獨立生產者,其數量受到行會的限制,很難進入其他行業謀生。這些因素再加上對移民的有限利用,以及早期的工業製造業無法提供替代性的就業機會,最終凝結成了大規模的貧困危機,給城市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19 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城市和地區的貧困人口佔到四分之一。 而且還出現了新型貧困現象,這不同於因身體問題或個人不幸造成的自然貧困,也不同於社會邊緣群體,他們可以通過最艱苦的工作來維持最低生計,但是他們陷入賣淫、吸毒等惡習中,這種情況在貧民窟、工作間以及監獄新兵中逐漸普遍,這也加重了社會的貧困危機。

結語
19 世紀上半葉開始,德國步入工業化浪潮,從傳統的農業社會逐漸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型,城市迅速發展起來。工業化時期德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帶來了新的社會風險和社會問題,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貧困問題,突出表現在城市貧困階層人數增加、城市住房困難、民眾工資水平低、工人問題嚴峻等方面。所以德國城市的反貧困政策也在逐步調整,日趨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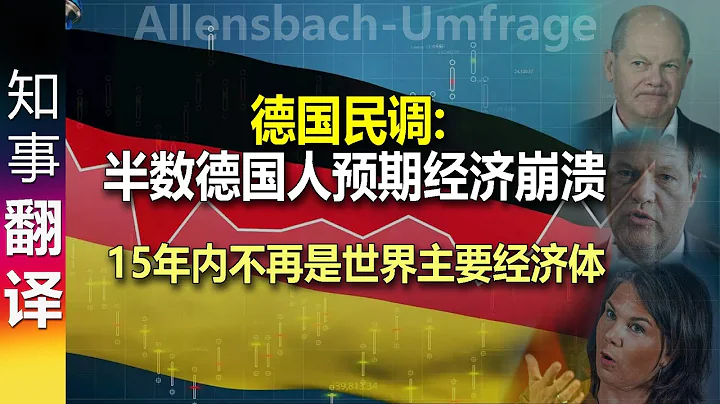
![[ENG SUB] 失能人口 人才去哪兒?你我老之路 邁入高齡社會準備好了嗎?!【特別報導精選】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vWLjfCzRKI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8b5Q_6MdbkwsetqSk4wjCmb3F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