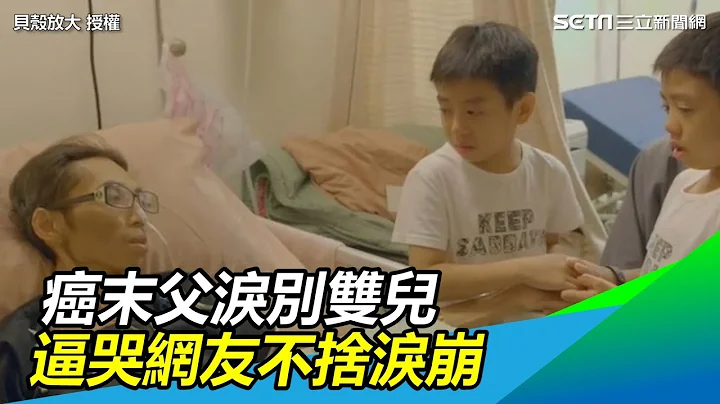「這男孩不行了。」
「我們還能把他救回來。」
在燒傷科病房內,醫生們評判著B.J. 米勒的命運。
19歲的普林斯頓大二學生米勒在一條廢棄鐵路上戲耍攀高時,被電弧擊中了金屬手錶,11000伏的高壓電流經過他的手臂,一路向下,從腳底穿出。米勒被彈出約10米遠,雙腿冒煙。
一個護士出現在米勒的病床前。也許是因為注意到米勒睜大的雙眼,她讓其他人安靜下來,並握住他的手。米勒已記不清她說了什麼,但感到很安全。後來,他知道了她的名字:喬伊。
在燒傷病房的兩個月里,喬伊一直照顧著米勒,讓他體會到被照護的感覺,還有依賴他人生存的恐懼和感激。
米勒死裡逃生,但失去了雙腿與一隻胳膊。這段經歷喚醒了內心的一些東西:對痛苦和死亡的深刻理解,以及利用這一點來幫助他人的願望。再後來,米勒也像喬伊一樣,來到許多人的病榻旁邊,支持他們度過生命最後的時光。
如今,51歲的米勒成為美國安寧療護和緩和治療的「一張名片」。看診、演講 、著書……多年來,米勒一直致力於幫助人們,在走向生命終結時少些痛苦、多些意義。
緩和治療一直是關於好好活著
事故發生一周後,醫生切除了米勒雙腿膝蓋以下的部分。隨後,米勒又經歷了15次手術,其中一場切除了他左臂肘部以下的部位。
「媽媽,現在我和你有了更多的共同點。」做完截肢手術後,米勒對母親說。

米勒
米勒的母親蘇珊是一位脊髓灰質炎後遺症患者,這種漸進性的疾病使得她的身體不斷退化,最後不得不依賴輪椅。年長4歲的姐姐麗薩,則是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接受心理治療。目睹母親和姐姐各自的掙扎,米勒早早就明白,生活總是有暗面。儘管人生跌入谷底,米勒亦努力說服自己,痛苦不是一種反常,而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這種積極的心態在最初主要是一種自我催眠。內心深處,米勒被巨大的不安和羞愧所折磨:走出病房,我將是誰?別人會如何看待我的身體?我還可以做什麼?
對身份和人生意義的思考激發了米勒對藝術的熱愛。回到普林斯頓大學後,他開始攻讀藝術史專業,希望能從創造性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在那些失去了胳膊、鼻子、耳朵的古代雕塑中,米勒意識到,不朽的傑作與他是如此相似,殘缺也可以是藝術的一部分。路易斯·沙利文和密斯·凡德羅等現代建築師亦讓米勒著迷,他們剝去建築矯揉造作的裝飾,歌頌結構本身的力量與美。在研究藝術史的過程中,米勒開始修復他與自己身體的關係。他學著發現身體別樣的美,並逐漸放棄遮蓋假肢。
「痛苦讓我獲得了一種謙卑感,但我也得到了一種新的自信:我可以適應痛苦,與之共存。」米勒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為了從與疼痛和殘軀共處的經驗中尋求意義,從藝術史專業畢業後,米勒進入醫學院,學習復健醫學。「如果病人走進診療室,發現醫生和自己一樣,這對病人一定會有正面的影響。」米勒說。
然而,在醫學院的最後一年,米勒的人生再次遭遇變故:姐姐麗薩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一直到逝世後,心理醫生才確認她患有雙向情感障礙。米勒沒有覺察姐姐的不妥,這讓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治病救人。加之醫學實踐的現實和米勒的理想相距甚遠,他準備離開醫學界。
就在那個時候,米勒偶然選修了一門緩和治療的課程。「這是一個改變一切的地方」,米勒在2020年的一檔播客節目中講述了與這門臨床學科相遇的故事。在威斯康星州醫學院實習時,他目睹了腫瘤學專家大衛·魏斯曼醫生與一名患者溝通病情。各項指標顯示,患者已時日無多。米勒形容,那是一場「非常棘手」的對話,「傳統上,醫學界並不擅長處理這種充滿心理負擔的內容」。魏斯曼醫生坐在患者床邊,坦誠地告訴患者,她的心臟狀況不容樂觀,「在離世前,你有什麼願望,希望得到什麼樣的照料?」那個女人的臉上沒有震驚或憤怒,而是解脫。
那一刻,米勒明白,他找到了真正可以積極利用自己經驗的方式。
「醫學中的其他學科治的是病,而緩和治療醫的是人。」米勒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緩和治療是與你所在的現實合作。它非常誠實地審視你所經歷的現實,擁抱你的主觀性。」換言之,在緩和治療的世界裡,醫生不會試圖掌控一切,患者亦可以指導醫生為自己服務。
許多人誤以為緩和治療病房只是人們在生命最後階段去的地方,但事實上,緩和治療是一個更加開放的概念。緩和治療關注患者的願望,緩解患者身體、情感和精神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在患嚴重疾病的任何階段,患者都可以尋求緩和治療介入。而專門為臨終階段患者設計的安寧療護,是緩和治療的一個子集。在國內,安寧療護的早期譯名「臨終關懷」更為人熟知。米勒強調,「緩和治療從來不是關於死亡,它一直是關於好好活著,直到生命終結。」
在臨終前隨心所欲地生活
米勒有一個騎摩托車的夢想。鑒於他的截肢情況,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年輕的機械師蘭迪·斯隆決定試一試,為米勒改裝一台特別的摩托車。
米勒終於如願以償。斯隆為他造出了一台可以用單手加速和剎車的摩托。提車那一天,米勒騎著摩托奔向夕陽,發現自己在頭盔下淚流滿面。
一年後,斯隆出現在米勒的診室,他確診了一種極為罕見的癌症:間皮瘤。患有這種癌症的人一般有長期的石棉暴露史,且平均年齡在50歲至90歲之間。斯隆只有27歲。
確診時,腫瘤已經侵入斯隆的肺部、橫膈膜、心臟,並擴散到腦幹。放療和化療都無濟於事,且帶來了可怕的副作用。
斯隆的身體迅速衰竭,生命預期只剩下幾周。儘管如此,斯隆仍然渴望贏得與癌症的戰鬥,拒絕接受終局將至的事實。
否認現實是患者面對死亡的常見情緒。「從本質上說,否認實際上是一種有效的應對機制。」米勒在其與肖莎娜·伯傑合著的《人生除此無大事》一書中寫道。「然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否認就會形成阻礙,讓你無法看見生活的全貌。」米勒亦寫道,人們在面對死亡時產生的複雜情緒,如否認、恐懼和悲傷,都與渴望有關,認識到這種聯繫「能夠讓痛苦具像化,讓我們對曾經擁有的健康、能力或親密關係心存感激。」
米勒意識到他必須幫助斯隆調整預期。在制定治療方案前,他問了斯隆一些問題,比如「你最喜歡自己哪一點?」當時斯隆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愛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
通過談話,米勒確定了護理目標,即確保斯隆還能去感受並表達自己的愛意。斯隆放棄了那些只會給身體增加更多負擔的抗癌手段,搬進一間小而美的安寧療護中心。他相信米勒的承諾,可以在那裡隨心所欲地生活。安寧療護中心24小時的醫療團隊和志願者,仍會幫助他在餘下的時間內儘可能地保持舒適和清醒,這也卸下了斯隆母親和好友的照護負擔。同時,斯隆敞開病房的門,歡迎更多的朋友來探望。
在安寧療養中心的日子裡,斯隆樂此不疲地迎接著訪客。他們一起玩電子遊戲、熬夜、喝酒、抽煙、去最喜歡的餐廳吃飯……他打破了所有慣常的臨終規則。斯隆的母親鮑德溫說,儘管他承受著身體的痛苦,但他很享受這種感覺。「直到最後,他總是說:好吧,我們還有一天。你想做什麼?」
在去世前不到36小時,斯隆出海航行,微風拂面,陽光在背,親友環繞……從前天氣好時,他常這麼做。
在入住安寧療養中心的第八天,斯隆離開了人世。他捐贈了自己的遺體,交給醫院進行科學研究。
鮑德溫說,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斯隆都在做自己,「在拿到一張糟糕透頂的牌之後,這可能是最佳結局」。
人生除此無大事
關於死亡的談話並不受人歡迎,但如果是米勒說,人們往往會願意聽。
曾與米勒一起共事的心理治療師卡倫·桑切描述過這樣一個時刻:一位患有晚期胰腺癌的海軍陸戰隊老兵總是沉默寡言,拒絕溝通。但當米勒走到跟前,老人開始落淚,敞開心扉。
「看到他站在面前,我們就知道他曾經遭受痛苦,曾經處於他所談論的深淵的邊緣。這給了他一種其他人可能沒有的權威。」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麗塔·查倫評論說。
當米勒來到創意設計公司IDEO辦公室,就如何重塑緩和治療的形象、使社會受益進行諮詢時,編輯部主任肖莎娜·伯傑覺得自己找到了一位老師,「完全被點燃了」。
為了展開一場關於如何重塑與死亡關係的對話,IDEO在辦公室里搭了一個安寧的空間:一頂純白的圓頂帳篷里燭光閃爍,米勒與十個參與對話的人圍坐成一個圈,聽他們分享對人生最後時刻的暢想。人們有一些關於臨終的美好想像,比如躺在冰島的冰山上迎接死亡。當輪到伯傑分享時,她慚愧地哭了起來。

伯傑
早年間,伯傑創辦了一本生活方式雜誌,主張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生活的設計師。然而,當父親患上了失智症後,伯傑發現,面對衰老和死亡這樣重要的人生課題,自己其實毫無頭緒和準備。
伯傑的父親患病前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工程學教授。隨著大腦功能日漸衰退,他失去了一切自信和獨立的來源,病情也因抑鬱進一步惡化。在生命最後的幾個星期里,伯傑的父親已神志不清。那一天來臨時,伯傑能做的就是找出父親舊日里喜歡的磁帶來播放,並且在他耳邊說她愛著他。伯傑說,她不知如何與父親討論他的感受,也不知道如何讓父親以他想要的方式體面地死去。「我們不知道這些問題是如此的重要。」伯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我們生活在一種將死亡視為有選擇的文化中。好像如果我們戒煙,吃西蘭花,每天走上一萬步,就可以避免死亡。」伯傑說道。「大多數人最終都像我一樣,不由自主地在疾病、喪親和悲痛中上了一堂速成課。」
「B.J.米勒醫生有一個大膽而美麗的願景,關於我們如何接受死亡,如何讓生命更有意義。」伯傑說,她被此深深吸引,也希望這些經驗能為更多人所知。因此,伯傑向米勒拋出了橄欖枝,兩人合著了《人生除此無大事》一書。這本人生告別指南按照時間順序講述生命如何一步步走向終點,並為提前計劃、病中、臨終和逝後四個階段將面臨的問題提供參考。
書中提到,每個人都應該為死亡做一些文書工作。比如,準備生前預囑,提前做出醫療護理決策,以備你處於重病晚期時無法自己做決定。「這不僅幫了你的親友一個大忙,也是在幫助你自己,確保你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得到你想要的照顧。」米勒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米勒的同僚們將其稱為緩和治療領域的「大使」。除了著書,他還出現在各種會議、電視和電台中,談論疼痛與上千次替代性的臨終體驗教給他的東西。工作之外,米勒對生活一樣充滿了熱情。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他騎著斯隆為他改裝的摩托車,或是穿著短褲和短袖衫慢跑。他說,在臨終病房學到的關鍵一課是,要享受這個神秘、瘋狂、美麗的世界。
「我的一部分很早以前就已經死了。但是,我針對這個事實重新設計了我的人生,當你意識到你在生命中永遠可以找到美好的事物和有意義的事情時,我可以告訴你們這是一種解放。」在一場題為《人生盡頭有何求》的TED演講中,米勒說道。
記者:陳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