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小南 張禕(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6-02-11)
人們常說「書畫同源」,與繪畫相類,書法有著審美、娛情甚至遊戲的一面。宋代的文學家、藝術家將不同的藝術形式融匯無間,無論繪畫還是書法作品,都蘊涵著當時文化菁英的學養與情操。但就功能而言,二者有明顯的不同。
與繪畫相較,書法在現實生活中承載著更為直接的社會功能,是人們用以溝通信息的中介;無論在察舉科舉中,無論是為官任吏者,都無法須臾離開書寫技能。作為自古以來的實用技藝,書法體現著士人的基本素質,也是謀生的手段之一,在古代的官場和民間長期受到重視。
目前傳世的宋代書法作品,多是士人手跡。就其書法風格而言,有「院體書法」,常用於官方文書的撰寫抄錄;也有「文人書法」,文人墨跡與其詩文作品,往往構成為「一體兩面」的欣賞對象。就其內容而言,屬於原創者,往往為公私文書、詩文、題跋之類材料,大多可直接作為原始史料利用,其中有一些本身即是政治史資料。

司馬光手書
下面即以筆者注意到的一些宋代書法篇章為例,圍繞兩宋時期官員告身、詔敕指揮、御前文字等方面的內容,擇要介紹此類材料在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可能的意義。
一
唐宋時期的官員告身(或曰「官告」,即委任狀),如《朱巨川告身》、《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等,早為制度史研究者所注意。
在宋代,官員告身依其級別高低和除授職務輕重,分別由翰林學士知制誥和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者)負責命詞,前者屬於「內製」,後者則為「外製」。在目前傳世的書法卷帙中,有北宋中期授予司馬光的兩份官告。一是日本熊本縣立美術館所藏熙寧二年(1069)司馬光充史館修撰的告身,是北宋元豐改制之前的外製官告;二是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元祐元年(1086)的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是改制後的內製官告。作為書法作品,這兩份材料久為博物館界所熟悉。本文將嘗試解讀兩份官告文本之內容,從中觀察宋代與人事除授相關的政令文書之運轉流程及其呈現方式。
(一)
熙寧二年(1069)司馬光充史館修撰告身(圖1),是北宋元豐改制前的一份外製官告。

圖 1 熙寧二年司馬光告身(日本熊本縣立美術館藏)[1]
該告身全文共五十九行[2]:
1. 敕:策牘之書,論譔所職,
2. 必資良直之美,用暢婉微
3. 之風。我得名才,允當遴選。
4. 以尓翰林學士兼侍讀學
5. 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
6. 知制誥、編修歷代君臣事
7. 跡、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
8. 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
9. 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
10. 對臣寮所上封章、柱國、河
11. 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
12. 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
13. 金魚袋司馬光,學足以通
14. 古今之變,文足以昭典冊
15. 之華。執經露門,視詔鑾
16. 苑,而介靖之操既表儀於
17. 禁塗,論議之公亦補削於
18. 時道。朕惟國必有史,官
19. 難其人,所以謹後世之傳,
20. 明四方之志。載筆之命,皆
21. 曰尓宜。固能詳前代著作
22. 之規,舉一時褒沮之法,惟
23. 尓所善,弗假訓言。可特授
24. 依前右諫議大夫、翰林學
25. 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充
26. 史館修撰,散官、差遣、勛、封、
27. 食實封、賜如故。
28. 熙寧二年八月 日
29. 中書 令 使
30. 中書侍郎 闕
31. 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臣宋敏求 宣奉行
32. 奉
33. 敕如右,牒到奉行
34. 熙寧二年八月 日
35. 侍中 使
36. 門下侍郎 公亮
37. 給 事 中 使
38.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 珪
39. 八月八日未時都事孫日新
40. 左司郎中 付吏部
41. 左仆 射 在中書
42. 右仆 射 闕
43. 吏部尚書 使
44. 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兼侍講兼權判 維
45. 尚書戶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兼權同判 鼎臣
46. 吏部侍郎 使
47. 吏部侍郎 闕
48. 左 丞 使
49. 告: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
50. 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編修歷代君臣
51. 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
52. 公事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
53. 所上封章、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
54. 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55. 敕如右,符到奉行
56. 主 事 闕
57. 殿中丞、直史館判 軾 令史劉 琰
58. 書令史樊 德宣
59. 熙寧二年八月 日下
該文書以「敕」字發端,從第1行至27行,是由負責命詞的外製官員(知制誥)根據宰相機構下達的詞頭起草的外製詔命(制詞)。詔命開篇,從「策牘之書」至「允當遴選」,是圍繞新授職任「為官擇人」之語;繼之而來的「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直至「賜紫金魚袋」,是被除授者原本的差遣、散階、本官、勛、封爵、食實封、賜等名銜;「學足以通古今之變,文足以昭典冊之華」云云,則是針對司馬光本人的褒諭與期許之詞。「可特授」之後,是新予除授的職銜,應當是宰相機構進擬,並由皇帝認可裁定的。據王應麟《辭學指南·誥》,外製詔命的一般形式是:「敕:云云,具官某云云,可特授某官」[3],此份外製文字的格式與之完全相同。
第28行是制詞完成的日期。29至48行體現著詔敕文書形成之後,按照三省出令程序「流轉」的官員簽署格局。其中,29至34行,形式上是中書省官員對於詔命「宣、奉、行」,及將敕書轉發至門下省的程序;35至38行,是門下省官員的署銜;39至48行,是尚書省承接制敕程序,以及尚書省官員的籤押。值得注意的是,三省從首長到諸司要員,實際上多不在位,非「使」即「闕」;即令在中書省以「知制誥」身份宣奉行者、在門下省以「給事中」身份籤押者、在尚書省以「判」吏部流內銓身份署銜者,事實上也多與該文書的實際形成與發布過程無關[4]。
49至59行,則是經官告院簽發的「告」本身之文字,完整頒布了司馬光的全部職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編修《歷代君臣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官告末尾,第56至58行的署名,是供職於官告院的官吏。所謂「殿中丞、直史館判 軾」,是當時充任判官告院的蘇軾。

南宋告身局部
在北宋前期的兩府體制之下,官告中以「三省」為名羅列的簽署程序,並非除授官員的實際流程;在宋代的傳世文獻中,對於詔命簽發的方式缺乏清晰記載。存世的官告實物,使研究者有機會窺得北宋前期「雙軌制」的運行方式[5]。
我們看到,外製詔命之下,是按照三省六部出令程序排列的官員簽署格局。事實上,北宋前期,原屬唐代三省六部負責的實際職事,早已歸屬到發展成熟的差遣系統之下。三省六部的大多官稱僅止用來標誌官員的身份與級別。在這樣的背景下,官告中三省、吏部官員的簽署,其實與詔命頒行的程序無關。北宋前期官告的這種籤押格式,是三省制形式上的延續,體現出傳統三省程序與現實差遣系統的折衷。

南宋司馬伋告身局部
宋神宗元豐(1078-1085)年間的官制改革,將原來朝政中樞「中書門下--樞密院」二府並舉的體制,改變為「三省--樞密院」體制。宰相機構的拆分重組,使政務運行有了不同於前期的方式。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重回政令運作之前台,使得除授詔命的運轉流程「歸一」。也就是說,北宋前期的中央政務,實際上是在二府體制下運行,而體現在官告上的簽署形式,卻如唐制般呈現著三省制的樣貌;元豐改制之後,造令、行令職責回歸三省,簽發官員除授文書的實際部門與呈現的情形基本吻合。
(二)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元祐元年(1086)的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圖2),是北宋元豐改制後的內製官告。

圖2 元祐元年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台北故宮博物院藏)[6]
這一告身長卷,同樣是由制詞、籤押程序及「告」文構成。其中的制詞部分由翰林學士知制誥鄧潤甫撰擬,與《宋大詔令集》中所收錄的《門下侍郎司馬光拜左相制》[7]、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九《司馬光左僕射制》[8]文字相同。
王競雄先生在其《〈書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研究》[9]一文中指出:「本院所藏《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系屬制授告身,於元祐元年(1086)頒發,正值新官制推行之際,可以略見當時正式文書作業的情形。」並且提出,元豐改制之後,告身文書的運作流程,應由三省連貫操作,依序首先應由中書省簽署宣下,而這篇告身與元祐三年范純仁拜右相告身[10]一樣,在制詞之後,即接門下省審讀簽署記錄,因而存有疑問。事實上,進拜宰相的制授告身在宋代本屬「內製」(元豐前後都是如此),並非中書舍人起草進畫,而是由供奉內廷的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命詞。元豐改制「循名責實」,告身簽署程序原則上應與實際除授程序相符,「內製」命詞擬定後既無需中書省「宣奉行」,直接頒降門下省施行,因此中書省官員並不列銜其中。
門下省籤押的文書程序,可以參考日本學者中村裕一恢復的唐代開元(713-741)年間制書體式:
侍中具官封臣 名
黃門侍郎具官封臣 名
給事中具官封 名 等言
制書如右。請奉
制付外施行。謹言。
年月日
可 御畫[11]
根據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所藏范純仁拜相告身,北宋元豐改制後門下省簽署乃至帝王畫「可」部分,與唐制基本相同:
侍中 闕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 大防
給事中臣 臨 等言
制書如右,請奉
制付外施行,謹言。
元祐三年四月五日
制可[12]
范純仁與司馬光兩份拜相告身,「侍中」皆「闕」,職位虛懸。這是因為當時的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即門下省長官,侍中虛位實不除人。
在司馬光拜相官告上系銜的門下省官員,有尚未到任的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被除授者本人,未謝)、尚書左丞權門下侍郎呂公著和給事中范純仁。而同屬門下省的這幾位官員,目前被截為兩段,皇帝批示的「制可」二字,插在門下侍郎與給事中的署銜之間。對照以上文書體式可見,這一次序實有問題。這恐怕是該告身在流傳中一度斷裂,重新裝裱時,因對宋代制度不熟悉,接裝顛倒所致。正如王競雄先生所指出,按照正常文書流程,皇帝「制可」應在門下省程序完成、標註時日「元祐元年閏二月 日」之後[13]。

宋代告身,後皆視之為書法上品
司馬光與范純仁的拜相告身,都依宋代的官告之制,用「五色背金花綾紙十七張」[14]。各類官告以其用紙質地、尺幅規格、色彩紋樣、色背白背、張數多寡等等,體現出官僚等級制度之莊重森嚴。
二
現存宋代書法作品中,有一些詔敕文書。其中有賜予臣僚個人,作為指示、獎諭或表示體恤的;也有頒發給特定部門,作為政務「指揮」行用的。前一類詔敕的現存實物,有《賜毛應佺敕》、《蔡行詔》及《答虞允文詔》等例;屬於後一類的,則有《方丘敕》及若干御筆手詔。
(一)
我們先看賜予臣僚個人的詔敕文書。
一般而言,稱「詔」或「敕」,有級別高下的區分,所謂「賜五品已上曰詔,六品已下曰敕書」[15]。就文書本身來看,在命詞者、措辭、用印、用紙方面都有等級輕重之別。通過以下書卷實物,大致可以觀察到這些區分。

圖3 賜毛應佺敕(北京故宮博物院藏)[16]
《賜毛應佺敕》(圖3)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敕文之後,有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張雨所作題跋,稱該帖是「唐明皇手敕毛應佺知恤詔真跡」。《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據此題作「唐,無款,行書毛應佺知恤詔」。到明代後期,張丑曾推測該詔書為宋太宗時期頒出[17]。
然而,上述兩種推斷都無法合理解釋敕文首句「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之語義。其實,所謂「三聖」是指宋太祖、太宗及真宗,這一敕書應頒出於宋仁宗時期。南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卷四「天聖中毛應佺守竇州,朝廷賜慮囚敕書」條下,全文著錄了這篇敕書[18],正可作為佐證。
今藏遼寧省博物館的徽宗《蔡行詔》(即《行書蔡行敕》,圖4),是宣和(1119-1125)年間蔡行請辭殿中省長官職務時,徽宗頒出的不允詔書。

圖4 蔡行詔(遼寧省博物館藏)[19]
四川省博物館藏南宋孝宗朝《答虞允文詔》(即《行書答虞允文敕書》,圖5),也是一份不允詔書,從其內容來看,該詔書頒賜應該是在乾道四年(1168)春天,虞允文時任資政殿大學士、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20]。

圖5 答虞允文詔書(四川省博物館藏)[21]
以上三篇詔敕文書,皆以「敕某某」開篇,這也是類似書卷通常被定名為「賜某某敕」的主要依據。但若仔細觀察內文中的措辭方式,不難注意到「詔」與「敕」程序化表達中的細部區分。像《賜毛應佺敕》呼毛某為「汝」,詞尾雲「故茲示諭,想宜知悉」;而《蔡行詔》和《答虞允文詔》則稱詔書的被受者為「卿」,詞尾則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此外,褒獎類的敕書,會說「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如《包孝肅奏議》卷九所附《敕書下安信軍通判殿中丞張田》[22]等例。而君王的御札,則往往以「故茲札示,想宜知悉」結語。
從形式上看,詔敕開端,都有較大字體書寫的「敕」(「勅」),尾部署有「某日」和獨立明顯的「敕」字。從《賜毛應佺敕》和《蔡行詔》來看,尾部的「敕」字與詔敕正文及畫日是在彼此拼接的兩張紙上,中間有騎縫鈐印。《答虞允文詔》末尾缺「敕」字,可能是流傳中斷裂遺失了。《賜毛應佺敕》、《答虞允文詔》上所鈐璽印為「書詔之寶」;《蔡行詔》所用為「御書之寶」,表示該詔敕屬於皇帝「手書」,以增重其事。
(二)
收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方丘敕》(圖6),是用於宣布朝廷舉措的詔敕。

圖 6 方丘敕(遼寧省博物館藏)[23]
除了首尾的跋語以外,該書卷由兩部分組成:主體部分是致祭方丘以後準備給嬪妃「加寵錫」的詔敕。詔敕的文辭,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結尾;文末署日,不出年月,並有獨立的碩大「勅」字,與前述頒賜臣僚個人的詔敕形式一致。
該書卷後面附連著另外一份文書,前有御批「依奏」,且加蓋「御書之寶」璽印。其主體是前執政鄭居中大觀四年(1110)十二月進呈之札子。從內容來看,前部的詔敕與後面御寶批複的札子之間並沒有直接聯繫,應該是後來的收藏者裝裱在一起的。
宋代的詔敕,文獻中有不少著錄。但即便是熟知典章制度、甚至經手相關程序者,也很少記載時人習見的文書體式。若討論這類問題,關注其演變脈絡,只能依靠實物原件。現實中的類別、情形,當然比較複雜,文書體式的施行及稱謂,也有靈活之處;而從先後時段中不同類型的這四份書法材料來看,北宋元豐改制前後直至南宋時期,普通詔敕的基本體式應該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三
在宋代文獻中,「御前文字」是一相對專門的概念[24]。以帝王名義自內廷頒出的命令文書,廣義上都是御前文字。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御前文字曾經廣泛行使,成為用途相對固定化、制度化的文書體式。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即所謂「御筆」、「手詔」之類。
吳曾《能改齋漫錄》中說:「天子親札,謂之御筆。」[25]趙升《朝野類要》則說,手詔「或非常典,或示篤意」[26],是詔書中挾天子個人威嚴、體式尤重者。而眾所周知的是,宋代的「御筆」或是「手詔」,並不一定出自皇帝親筆,可能字句既非親擬,墨跡亦非親書。正如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親筆與御筆內批不同》一條所說:
本朝御筆、御制,皆非必人主親御翰墨也。祖宗時,禁中處分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崇觀後,謂之御筆。其後,或以內夫人代之。近世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寶。又有所謂親筆者,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27]
宋代皇帝頒降的御前文字,名目繁多,格式、印畫形式不一,可以區分出許多類型。御前札子(簡稱「御札」)是其中典型的文書體式之一。與一般針對個人的詔敕以「敕某某」開頭不同,御前札子都在文末用「付某某」表示。二者作用相同而形式互異。相對於普通詔敕,後者通常也會被稱作「手詔」。例如《華陽集》載有王珪代皇帝起草的《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手詔》,末句說:「所乞宜不允。付富弼。」[28]
流傳至今的御前文字,例如徽宗給付劉既濟的御筆手詔(碑刻拓片,圖7)、紹興七年(1137)高宗賜岳飛手敕[29]及紹興十一年高宗賜予岳飛的親筆批札(圖8),應該都是御前札子,文書末尾有「付某某」字樣,其後則是押字和璽印。與一般詔敕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之類用語不同,御前札子在「付某某」之前,有時會用顯得親切直接的「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如圖8)、「故茲親筆,卿宜知悉」[30]、「故茲親札,想宜知悉」[31]之類表述。

圖7 徽宗付劉既濟手詔拓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32]

圖8 宋高宗賜岳飛批札(局部)(台北蘭千山館藏)[33]
「御筆」、「手詔」往往非皇帝親筆,而目前所見徽宗朝題額為「御筆手詔」的石刻,皆以瘦金體書寫,聯繫到內廷善書吏人對於「奎畫」的仿效,臣僚對於「御筆頗不類上字」[34]的批評,都使我們注意到,所謂「御筆」,在當時是通過特定書法風格(筆法)體現出來的[35]。
四
理論建設的滯後和一手資料的匱乏,始終是困擾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突出問題。要求得研究中的切實突破,離不開材料範圍的再開拓與史料內容的再解讀。具體來說,不僅要充分利用正史等傳世文獻,也須要深入開掘、認真面對存世的書法卷帙以及繪畫作品等可能提供之訊息。
王充在其《論衡》卷十三《別通篇》中說:「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36]如果學者將眼光聚焦於古代政令運行的方式與實態,則官告、詔敕等文書,作為官方政令的承載物,無疑是政治史研究的關鍵對象。
而傳達民間信息的文書,也或多或少與當時的各類事件、人物、社情民意相關。目前我們所接觸的宋代史料,尚缺乏足以衝擊既往研究體系的新發現。流傳至今的原始狀態的文書,除去一些石刻碑碣外,基本上是作為傳世書法保存下來的。這種狀況,使得書法作品的多重意義日益充分地彰顯出來。
(本文原刊台北《故宮學術季刊》第29卷第1期,2011年10月)

[1] 圖片取自日本熊本縣立美術館網站,網址為http://www.museum.pref.kumamoto.jp/common/UploadFileDsp.aspx?c_id=15&id=483&set_pic=1&gzkbn=0
[2] 錄文參見[日]下中邦彥編:《書道全集》第十五卷《中國10·宋Ⅰ》,163~164頁,東京,平凡社,1954;[日]久保田和男:《宋代に於ける制勅の伝達について:元豊改制以前を中心として》,見日本宋代史研究會編:《宋代社會のネットワーク》,201~202頁,東京,汲古書院,1998。本文根據圖版略有改訂。
[3] 參見王應麟:《玉海》(合璧本)卷二〇二《辭學指南·誥》,3810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4] 相關討論,參見朱瑞熙:《宋朝「敕命」的書行和書讀》,載《中華文史論叢》,2008(1),101~120頁;張禕:《制詔敕札與北宋的政令頒行》,31~38頁,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9。
[5] 對於相關問題及其背後原因,學界已經予以注意並開始有所討論。可參見劉後濱:《「正名」與「正實」——從元豐改制看宋人的三省制理念》,載《北京大學學報》,2011(2),122~130頁。
[6] 圖片見王競雄:《〈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書法述介》,載《故宮文物月刊》第284期,2006年11月,14~15頁。
[7] 佚名編:《宋大詔令集》卷五七《門下侍郎司馬光拜左相制》,287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
[8] 徐自明編著,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卷九,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條,542~5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9] 載《中國書法》,2008(1),89頁(該文原載《大觀——台北故宮書畫特展》)。
[10] 范純仁拜相告身,目前有三份存世,一藏蘇州博物館,一藏南京博物院,另有一份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制詞文字可參看《宋大詔令集》卷五七《同知樞密院范純仁拜右相制》,289頁。書畫鑒定家楊仁愷、傅熹年指出,蘇州博物館所藏范純仁告身當是複製品,並非原件(參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六)》,339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另外兩份中應該也只有一件是原本。
[11] [日]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43~44頁,東京,汲古書院,2003。
[12] 參見張禕:《制詔敕札與北宋的政令頒行》,43頁。
[13] 王競雄前揭文,89頁。
[14] 參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六一至六二、六五至六六,影印上海大東書局版,2653、2655頁,北京,中華書局,1957;宋敏求著,誠剛點校:《春明退朝錄》卷中,19~2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孫逢吉:《職官分紀》卷九《官告院》,《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全書》」)923冊,247~250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15] 楊億著,李裕民輯校:《楊文公談苑·學士草文》,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6]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九)》,4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7] 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三上,《四庫全書》817冊,75頁。
[18] 參見曾敏行著,朱傑人標校:《獨醒雜誌》卷四,37~3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 見《遼寧省博物館館藏書畫選》,載《中國書畫》,2004(10),23頁。
[20] 參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乾道三年二月辛巳、五年六月己酉條,1194、1204頁。
[21]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七)》,1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2] 包拯:《包孝肅奏議》卷九《進張田邊說狀》附《敕書下安信軍通判殿中丞張田》,《四庫全書》427冊,167頁。
[23]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五)》,33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從其固定程序的結尾用語來看,似應稱之為「方丘詔」。
[24] 對於宋代御前文字,包括其作用、形態的研究,已經有不少學術成果。例如王育濟:《論北宋末年的「御筆行事」》,載《山東大學學報》,1987(1),54~62頁;[日]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筆手詔》,載《東洋史研究》第57卷第3號,1998,1~34(393~425)頁;楊世利:《論北宋詔令中的內降、手詔、御筆手詔》,載《中州學刊》,2007(6),186~188頁;方誠峰:《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載《漢學研究》第31卷第3期,2013年9月,3~-67頁。
[25]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御筆》,26頁,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
[26] 趙升著,王瑞來點校:《朝野類要》卷四《文書•手詔》,83頁,北京,中華書局,2007。
[27] 李心傳著,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一《故事》,671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
[28] 王珪:《華陽集》卷一八《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手詔》,《四庫全書》1093冊,127頁。
[29] 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可參見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圖版I-7及解說(何傳馨撰),339頁,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30] 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宋兩朝御札墨本·高宗皇帝》,《四庫全書》第815冊,293頁。
[31]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四八《奉詔錄三·宣示付吳挺御筆》,《四庫全書》第1148冊,620頁。
[32]《崇真宮徽宗付劉既濟手詔》,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繆荃孫藝風堂舊藏)。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43冊,53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題作「賜項舉之書」。
[33] 原件藏台北蘭千山館。圖片取自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第40卷《原色法帖選頁》,1~2頁,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0。該御前札子在岳珂編:《鄂國金佗稡編》卷三《高宗皇帝宸翰卷下·紹興十一年》有著錄(王曾瑜校注本,4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34] 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二《歷代帝王帖·徽宗皇帝諸閣支降御筆》引蔡絛《國史後補》,《四庫全書》813冊,579頁。
[35] 參見方誠峰:《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50~51頁。
[36] 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卷一三《別通篇》,5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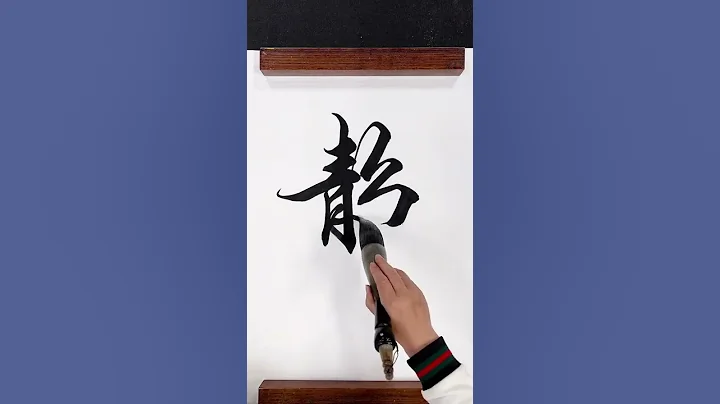



![[MAMA 2022] IVE, KEP1ER, NMIXX, LE SSERAFIM, NEWJEANS - 'Cheer Up' Lyrics (Color Coded Lyrics)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emQIKe2tGl8/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itWecJGXwnCsgIXjiSuzCmdM-1w)
![NewJeans在宣布獲大賞後全員毫無反應 「你們忘了嗎?我們是NewJeans啊」XD| [K-潮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VpJrVDAgBLs/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XE8uvu_gvrtmhqxrfNkwM21qLA)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 SSERAFIM&NewJeans - CHEER UP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d2heDnR3sj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AaOJ1FOuMVt8zl0aAdxxx1s2FQ)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SSERAFIM&NewJeans-ELEVEN+WADADA+O.O+FEARLESS+Hypeboy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Jks7TIDfnk/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Y-vECgvowNPEf_1BO1TlRrKZw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