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從區划上宋朝沿襲唐朝也大體是分為三個層級(路,府,縣),但是地方的權力運轉邏輯與唐朝大為不同。簡而言之,地方中間這一級全是流官,名義上都是中央派下來的。後來雖然變成真正的地方官,但是有帥、漕、憲、倉四類中央官員負責監督地方官。地方財富都要上繳中央。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宋朝的治國思想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和地方限權相結合,地方有什麼事都要看中央的臉色,要不根本無法獨立生存。這在一個封閉的地理環境中可能會比較穩定,但是在一個四面環強敵,隨時可能爆發大規模戰爭的環境中,地方顯然缺乏隨機應變和臨時募兵守城的能力。所以宋朝時期外敵入侵往往會勢如破竹。

除此之外,宋朝在兵役制度上也是按照這一邏輯。中央禁軍和地方廂軍完全不是按照一個標準選拔和保障。廂軍實際上就是雜役,完全沒有戰鬥力。中央禁軍四面為戰,來回周轉。軍隊調防頻繁,造成將不識兵,兵不認將,以當時軍隊的機動性而言根本無法完成戍邊駐防,平定內亂,外御強敵的重任。時間一長,禁軍中的年老吃餉士兵比例逐漸提高,軍隊戰鬥力越來越弱。到了南宋,實際上各將領都是自己募兵訓練,自己養兵,所以皇帝很忌諱,生怕唐朝藩鎮割據篡位再度重現。

一味地否定這種強中央弱地方的統治方式顯然是跳脫時空限制後的上帝視角。不過若是宋朝外部環境沒有這麼惡劣,也許這種方式未必如錢穆先生所言是最壞的。宋朝的商品經濟繁榮度是歷史公認的,這與地方官權力不大,管制不了商業不無關係。假設一直這樣,在理學思想的控制下,也許再過幾百年,宋朝會出現一種與新教倫理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商品經濟模式。加之宋朝終其一世都沒有打壓,誅殺文官的陋習,也許會有一種憲制萌芽出現?

不過歷史沒有假設,正如羅馬帝國被野蠻人所滅,宋朝即便商業發達,還是敵不過鐵騎。可以肯定地說,宋朝之後的後世王朝對商業貿易的放鬆再也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對地方權力的限制則一直延續宋朝的思路,除末年大亂,各朝代地方官再無軍權(血親貴族掌兵又是另一個故事了),也再沒有統一的行政管理權和相對獨立的財政收支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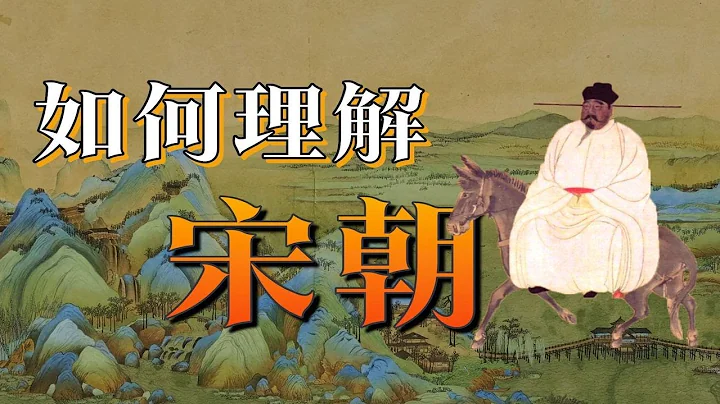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