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論美國20世紀地位崇隆的新聞界人士,恐怕沒有人超過李普曼。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他用手中一枝筆,把文字的影響力發揮到了極致。他出訪各國,時常受到各國元首接見,風光不讓美國大使。
不過,有這能耐的美國新聞工作者,不只李普曼一人。比他小4歲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也能做到,只是,她能做到這一點,是在1930年代的中國紅都延安。史沫特萊後來回憶說:
「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裡提著一袋花生米。……」「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里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

史沫特萊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生於1892年,與李普曼是美國同一代新聞人。論在美國的地位,史沫特萊當然難望其項背,但論在中國的知名度,史沫特萊恐怕不惶多讓,反而更多的人只知道史沫特萊。因為她是著名的「三S」(即著名美國記者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一,是最著名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她深入探訪過延安,也輾轉華北、蘇北,跟隨前線的八路軍、新四軍採訪,她積極利用自己的國際關係為延安爭取援助,後來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著名外科醫生柯棣華來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源自她的熱心推薦。「皖南事變」後最早把事變消息捅到《紐約時報》的,也是史沫特萊。
她最著名的著作是朱德的傳記《偉大的道路》一書。這是她上世紀40年代離開中國之後,在國外寫成的。她身體欠佳,1950年即在英國病逝,沒有來得及訪問她延安時的老朋友領導下的新中國。

李普曼
我這裡講這個故事,是想說,中共後來在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爭中,是軍事的勝利,也是敘事的勝利,而在最艱苦卓絕的時期,「延安故事」在全世界的成功傳播,為中共打破封鎖,贏得國際同情助益最多。這一切的背後,體現的是延安時代的中共領袖對國際傳播規則的熟稔,當時的延安有蘇聯記者,國統區也有蘇聯各大新聞機構的記者,但當時的中共領袖毛澤東提議選擇一個「可以信賴的外國人」訪問根據地時,第一個入選的,是斯諾,著名的密蘇里新聞學院培養的美國記者,後來英美主流媒體記者不斷到訪延安,跟《紅星照耀中國》有莫大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幾乎每一位來訪記者,都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親自接見。斯諾曾回憶,他與毛澤東會「一連談上幾小時,有時差不多談到第二天黎明」。所以,史沫特萊一個便條,毛澤東會帶著花生米欣然前往,絕不是偶然。用今天的話來說,延安時代的中共領袖,為提高領導幹部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做了最好的示範。
回頭再說一句李普曼。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夕,1月份,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拜訪李普曼,帶去了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向李普曼發出的訪華邀請。這一年3月,中國方面再次發出邀請,但這個時候,李普曼已經是83歲的老人,他自感身體無法承受一次遙遠的跨洋旅行,兩次邀請他都婉言謝絕了,於中國,於李普曼本人,當然都是一種遺憾。但一年之中,兩次上門誠邀,說明即使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共的最高領導層也深諳國際傳播中輿論領袖的價值。
來源:各界雜誌2022年第9期
作者:王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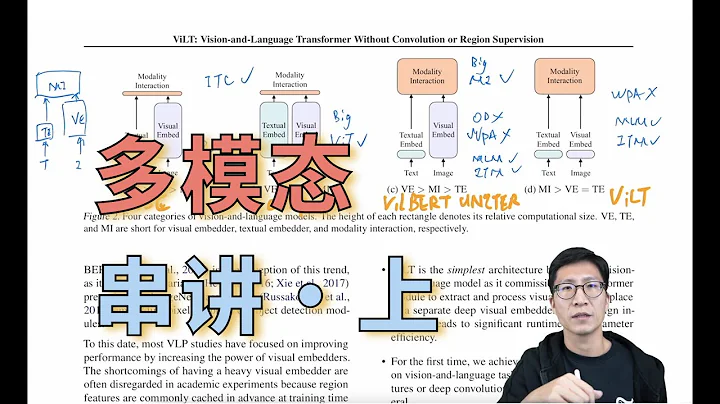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