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的革命戰爭年代,整個中國,朱德是最被民間神化的一個人物,也是最富傳奇色彩的大英雄。
美國人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戰士們視他(朱德)為神明,中國民間流傳他有各種各樣神奇的本領:四面八方能夠看到百里以外,能夠上天飛行,精通道教法術,諸如在敵人面前呼風喚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槍不入。也有人說他有死而復活的能力”。
德國人王安娜在《中國——我的第二故鄉》中也寫道:“農民們說,他(朱德)是千里眼,能夠看透遠處的東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師,不但能夠在敵人面前放起煙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騰雲駕霧。”
署名“紹源”的一位作者在他編譯的1946年4月出版的《朱德自傳》的小序中這樣寫道:“朱德在中國,已跟三國里的古代英雄們一樣變成傳奇式的人物了。進退迅速,難以捉摸的軍事行動,在敵軍看來,正如幻影一樣不可思議,而非凡迷信的人們就說他,作為共軍總司令的朱德,是一個魔術家。朱德的形象,被裹在各種富有色彩的幻想的外衣里。”
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地方老百姓都流傳說:朱德是天上的武曲星下界,他的掌心長着一顆常勝痣,每當八路軍與日本鬼子打仗的時候,只要朱德一揮手,八路軍便無往不勝。
1944年,朱德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有這麼一句話:“比如說,我個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頭六臂”。
處於統治者的對立面,在大量醜化宣傳的背景下,朱德的被傳奇化甚至神化,完全是其所創造的一個個軍事奇蹟造就的!
連他所帶的部隊中的將士,都對他“帶點神秘式的信仰”(肖克回憶),也就難怪那些對他並不了解的普通老百姓對他的神魔化的想象了!
但現實中朱德本人的形象,卻是一個顯不出有任何英雄色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
德國人王安娜描述初次和朱德見面,朱德給她的感覺時說:“就像一個勞累過度的老農民。這個“匪首”,怎麼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個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無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點也不引人注目。”
愛潑斯坦談到他對朱德的印象時說:“從他的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他是一個勇猛善戰的指揮員和身經百戰的戰略家。”
海倫.福斯特也說:“朱德沒有什麼軍人氣概”。
無疑,人的外部形象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人的性格和思想。
有的人喜歡突出自己,便總是着意於處處將自己表現得不同凡響、高人一等,有的人不希望引人注意,各個方面便都力求普通,與眾人混同;有的人精於演戲,表情動作便豐富多彩,有的人樸素實在,便給人感覺呆鈍痴憨;有的人注意小事,總是事事精明,看起來便很是伶俐聰明,有的人不拘小節,常常小事糊塗,看起來便有點愚笨無能;有的人喜歡顯示自己的男子氣概,便在眾人面前總是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有的人意識到剛強的害處和謙下的好處,便時時注意讓自己表現出溫和謙恭。
總之,性格和思想,由內在而外表,顯現於言談舉止,表現於打扮裝飾,即使是同等智力、能力或勇力的人,久而久之,也會形成完全不同的形象:有的人會給人以傑出的印象,有的人則會給人以平凡的感覺。但一個人真實的本質,在有洞察力的人的眼裡,總是會透過表面的形象,最終慢慢或突然顯露出來。
抗戰時期,一位中央社記者在報道朱德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雖僅有一天的晤談,他那起初給我的平凡形象,已經給不平凡的談話,特殊的風度完全衝破了。
的確是的,世界上有許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種平凡的外表下隱藏着。”
史沫特萊在描述了見到朱德後的第一印象,“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裡的農民老大爺,而忽略過去”,很快接着寫到:“我在這一瞬間,有了這樣一種感覺:不論以他的哪一部分來看——從聲音、動作,以至他的每一個腳步,都充滿了大丈夫氣魄。”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與外國友人
青年時期,特別是滇軍時期身着軍裝的朱德,其相貌給人以極其剛毅威猛的感覺,那是一個一眼就能讓人感覺到傑出的朱德形象,但中年和老年的朱德則讓人感覺平凡普通,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朱德所經歷的一些非常的苦難或者傷心經歷,以及在受到佛教影響和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後的思想變化和行為變化(佛教和共產主義都主張人人平等)。
所以,朱德外表的“平平無奇”和“沒有什麼軍人氣概”,相當程度上也是一種長期有意識地剋制自我,不突出自我,追求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導致的結果。
朱德的思想中包含着相當明顯的隱士思想的成分,對應於外表,朱德的平凡相貌也正像一個隱身衣,這個“隱身衣”,一方面常常能在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中保護他免於危難,另一方面也常常會使他在當時或以後被人忽視甚至輕侮。

36歲在上海時的青年朱德
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朱德和毛澤東,他們都是俯視歷史、雄視天下的曠世英雄,他們都是上天安排的在這個風塵中作主、在這個蒼茫大地上主宰沉浮的人物,他們都是承載着這個有着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大國命運的中流砥柱!
朱、毛之所以能夠並稱,根本原因便在於此!在同一個國家,而且在同一個陣營內,兩個人能同時享受“萬歲”稱呼,這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差不多已經是絕無僅有了,但更奇的是:這兩個人在領導工農武裝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過程中,竟然能以這種基本並列的地位融洽相處約二十年之久!這個奇蹟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兩位偉人的無私品質所共同成就的,但更與朱德的大度、對權力的淡泊,以及在功名上的有意識的自隱緊密相關。
1926年朱德在給朋友艾承庥的贈詩中這樣敘述自己的心跡:“我本江南一鯫生,十年從事亞夫營。身經滄海羞逃世,力挽狂瀾豈為名。……錦繡山河壞虎狼,火熱水深民望救;我欲回天力自強,安危度外不思量。”
從這幾句詩里我們可以看出,朱德對於名利、權位的淡薄,首先根源於他本來就有的隱士性格和思想,所以,詩中抒懷時就有“逃世”的說法;而他終於“羞逃世”,要“力挽狂瀾”,要“回天”,乃是因為國家和人民的苦難,使他這個“十年從事亞夫營”、“身經滄海”的人不能坐視不管。所以,他投身革命的目的完全是無私的,就是為了救民於水火,正如海倫.福斯特所說,“戰爭在他看來,並非一種建功立業,而是一種結束苦難的手段”。如果是為了一己之名利,以他當時的名位,又何必投身革命,“安危度外不思量”呢?這也就難怪海倫.福斯特說朱德“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就難怪當革命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和聲勢,或者取得了一些大的勝利,各方面的頌揚接踵而至的時候,朱德就開始不斷地推功。
1944年,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朱德說道:“我們切不可居功。群眾風起雲湧,烈士犧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們的。離開了群眾,我們什麼事也做不出來。比如說,我個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頭六臂,實際上,我只是廣大群眾事業與功績的代表中的一個而已。一定要記住,如果有功,功是黨的,是群眾的。”
在1948年5月,在華東野戰軍第一兵團團以上幹部會上,朱德說:“解放軍打了很大的勝仗,很多人說是我的功勞,我就知道他們把我作為人民解放軍的代表來說的。我個人應當認識,解放軍的勝利是全體同志的功勞,我不應該誇大我自己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麼能承受得起這樣大的榮譽呢?人家把功勞歸給我,我就把功勞往下面推,我想你們也要這樣推才好。”
斯沫特萊說:“從前早就有人對我說過,他(朱德)是一個單純、親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絲毫沒有使自己成為個人英雄的興趣。”
王安娜說:“要讓朱德談他自己的事情是很困難的,但當請他談紅軍的事情時,他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滔滔不絕。”
追隨朱德參加南昌起義的趙鎔(中將)說:“有人認為‘十六字訣’是毛主席創造的,其實是朱德創造的。朱總是從來不講他的貢獻和他的優點、長處的,無論如何也不講。我就曾問過他:‘十六字訣不是您提出的嗎?怎麼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說:‘只要對革命有利,誰提的都一樣。’”(註:事實上,毛澤東、朱德對“十六字訣”都有貢獻)
朱德的女兒朱敏說:“他(朱德)在我們子女面前,從來不談自己幾十年來的革命事迹。有時候,我的孩子們要他講講他的經歷,他或者搖搖頭,或者擺擺手,對孩子們說:‘我沒有什麼的,就是跟着毛主席。’‘你們應該學習毛主席的光輝歷史。’‘我們這一代人,以毛主席為代表。’”
解放前,朱德推功,把功勞推給工農群眾和普通士兵,因為大家把功勞放在他的頭上;解放後,朱德甚至在親人面前都從不言功,或者就把功勞推給主席,毋庸置疑,除了本身的謙虛和無私,這也是一種政治智慧和對時代的順應。
廬山會議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說朱德“一天總司令都沒有當過”,朱德笑着答道:“那就請你批評好了!”老領導誘敵深入的戰術,林彪見的可太多了,就這一句話林彪就再不說話了,後來,朱德對康克清談到他當時的想法,說:“說我連一天總司令也沒有當過,這沒關係,這對別人一點損害也沒有,只是否定了我自己。”
文革時期,“朱德的扁擔”被改編成“林彪的扁擔”,朱德聽到後笑道:“扁擔可以先借給他用幾天,遲早還是要還的嘛。”
看看朱德對待個人功勞和名譽的態度,沒有無我的精神,沒有非同一般的善良,沒有“腹中天地寬,常有渡人船”的度量,沒有常人難以企及的內在的力量和智慧,如何能做到這樣的豁達呢?動物中,最有力量的大象、獅子、老虎等,平時都顯得遲鈍而溫和,而兔子、老鼠等弱小動物則非常機靈,稍有風吹草動便會立即產生劇烈反應,力量並不很強的狼或者狗,則動不動就嚎叫或者狂吠不停。所以,外部的溫和和貌似愚鈍常常是內在自信和強大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
康克清在延安對海倫.斯諾談到朱德時說“他喜歡和普通戰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們促膝談心。他過着普通戰士的簡樸生活,必要時也和戰士做一樣的工作。他的綽號是‘伙夫頭’,他看上去就象一個普通士兵。有時清閑下來,他就去幫助農民種地。他還常常從河谷挑糧上山。”
老八路劉玉珠回憶說,在延安時,他記憶最深刻的是經常能在延安的便道上碰到撿糞的朱德,“當大官的一點架子都沒有!”
1942年,國民黨愛國將領續范亭到延安考察,當他見到仰慕已久、威名遠播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時,不勝驚訝。他萬萬想不到作為總司令的朱德,竟然穿着跟普通戰士一樣的粗布衣衫,跟普通農民一樣地鋤地種菜、擔尿挑糞,舉止形象跟一個老農完全沒什麼區別!續范亭大為感動,揮毫賦詩曰:“敵後撐持不世功,金剛百鍊一英雄;時人未識將軍面,樸素渾如田舍翁。”

朱德和老師張瀾
《朱德農民情結之謎》中說:“在老家馬鞍公社,他(朱德)見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懷裡,見到老人就讓坐在自己身邊。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聲鼎沸,笑語喧嘩,誰主誰客,難分難辨,好個熱鬧景象。”
朱德的孫子朱和平回憶說:“爺爺喜歡在別墅一層那寬大的圍廊里下棋。棋盤一擺,便圍滿了觀戰的人,連鄰院的孩子也跑過來。觀戰者裡面沒一個守規矩的,這個喊“拱卒”,那個喊“跳馬”,還有的嚷嚷“出車”,全都嗷嗷叫着支招,更有甚者,還把手都伸到了棋盤上,就差替下棋的人動子了。可爺爺和他的對手置嘈雜的喊聲於不顧,還是靜靜地按照自己的棋路挪動着棋子。在北戴河,只有我家的小樓里,才會不斷傳出這種熱鬧的歡笑,同附近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等(周恩來住處在國務院部門的區域)院子里的寧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這就是朱德!這就是那個有着顯著的隱士色彩和普通人特徵的朱德!正是因為有這個不喜歡出風頭,不與人爭名奪利,沒有官架子,總是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人的朱德,才有了那個形象上看起來也很普通的朱德。
跟朱德有較深接觸的著名軍旅作家劉白羽曾動情地描寫朱德說:“你面對他時,你無法想象他竟是那樣一個叱吒風雲、所向披靡的統帥。是的,他盡了一個統帥的責任,他從血流成河、荊榛遍地之中殺出一個新世界,但他絲毫沒有沾染統帥的威風凜凜、盛氣逼人的習氣,他創造了那樣多豐功偉績,好像都與他無份無緣似的。”

八路軍朱德總司令
1940年9月6日重慶《新華日報》有一篇題目為《如火如花的老少年》的文章,其中寫道:“我們在全部世界歷史上,讀到看到了不少氣焰萬丈煊赫一時的將軍人物,但真正成為群眾的領袖,象這樣‘平淡見英雄’的偉人,卻只有朱德將軍一人!”是啊,縱覽世界歷史,還能找到第二位象朱德這樣從衣着到言行如此普通,為人如此平淡,與士兵和群眾如此親近的總司令么?
黑格爾說:“仆妾眼中無英雄”。這是因為仆妾離英雄太近了,英雄的一切與他人無異的平凡之處甚至缺點,都在仆妾面前暴露無疑了。
所以,有些人想在眾人面前顯示自己傑出,想讓別人認為自己是一個英雄,便總是會在言談舉止上、行為上、服飾上,處處將自己表現或者打扮得非同一般,一有機會就會擺擺架子,耍耍威風,讓別人感到難以接近。
而朱德卻不同,他將自己一切普通的地方完全表現在別人的面前,朴樸素素、平平常常,從不擺架子嚇唬人、裝樣子糊弄人,從不讓人感覺難以接近。
“仆妾眼中無英雄”,這句話還有另一個解釋,那就是:仆妾終究是仆妾,他們的智力無法辨別英雄與凡人的區別。
許多人往往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以為那陽氣外露,動不動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的就是勇敢,以為那聰明使盡,事事精明的就是智慧,以為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就是傑出。
所以,他們根據朱德的形象和處事行為,便認為朱德既不威猛,也不聰明,甚至什麼能力都沒有。
殊不知太陽升到最高的地方便會下落,麥子成熟之後麥穗就會下垂,一個人的智慧、力量達到一定程度時,他就不再求上,而是趨下,不再是逞強,而是示弱,不再事事精明,而是在許多事情上能糊塗就糊塗,不再是追求突出,而是趨向普通,即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一個人內在高明到極致的時候,行為處事便會只求恰如其分,平平常常。
所以老子也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朱德
1958年7月初,朱德來到蘭州,興緻勃勃地攀登蘭州的五泉山,非要鳥瞰市容不可。前往干佛閣的半路上,一座橫在山道上的牌坊出現在朱德一行的視野。抬頭望去,只見牌坊正面橫書七個大字:“高處何如低處好。”
朱德反覆琢磨:“這七個字意味深長啊!”
“後面還有七個字呢!”有人在一旁介紹。
“我們快去看看寫着什麼?”朱德興緻盎然。穿過牌坊,背面七個大字映入眼帘:“下去還比上來難。”
朱德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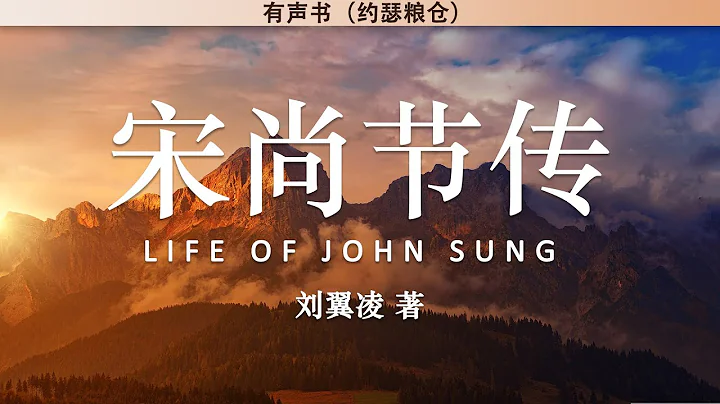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