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遠村

母親從上海打來電話,嚴肅地囑咐我:「慶娃,疫情鬧騰得我回不去,你再帶上5萬塊錢,備上八色大禮,對了,再買兩條好煙,儘快去西張營謝謝你張表叔。唉,這不經事不知道人家的實誠金貴。咱娘們對你表叔,做得不妥當,欠著人情呢!」
一

母親給我提起的這個表叔,叫張書誠。說起來,按我們老家的話,叫「掛邊子表叔」。他和我父親是發小,是我已出五服的一個同族大伯表姨家的孩子。小時候,走親戚常到我們柳河灣來,因為喜歡跟著我父親逮魚摸蝦,就成了好玩伴。論年齡,他比我父親小兩歲,便親切地叫我父親「忠義哥」。這是因為我父親大名叫柳忠義的緣由。
兒時在一起玩得好,等長成青少年,我父親和這個張表叔還在當時還是公社建制時,被各自的大隊選派到由公社武裝部組織的民兵營搞過集訓,時間大致有兩個月。練的就是一些隊列和刺殺、射擊動作。兩個人訓練之餘,便又多了接觸機會。
本來,這次民兵訓練,我父親和我張表叔的友誼按一般情況也不會加深多少。
「嘿,那可不是一般情況,是啥子情況哩?」我父親和我張表叔在一起聊天時,就不止一次地說過,「那可是二般情況。」
原來,在那次民兵集訓中,曾發生了一次青年民兵與駐地村民的械鬥。械鬥起於晚上看露天電影,由一個民兵在當地幾名女青年跟前說挑逗話誘發。那次,雙方一開仗就打得很亂。
我父親那次正碰上跑回駐地拿了半自動步槍衝出門的張表叔,就驚問一聲:「書誠,咋還敢動槍呀?槍是空彈匣,有啥用?你這一動槍,性質就變了。可不敢,可不敢!」
「槍上還有刺刀哩,總比個燒火棍強。整殘一個是一個!」張表叔就說,「咱也叫地頭蛇們瞅瞅,咱基幹民兵也不是吃素的!」
我父親聽了,立馬奪下了張表叔的槍,硬是把他拉進了屋裡,勸導道:「嗨,你以為這是和國民黨、土匪打仗啊?兵民一家哩,何況是民兵調戲婦女在先。」
「母狗不蹺尾巴,伢狗能上身?還不是那幾個小閨女在電影場上浪擺的。」張表叔分辯,「他媽那個匹,我就聽不得他們罵民兵沒一個好東西。我出來說句話,就挨了他們一坷垃。」
我父親好說歹說,才算安撫住了張表叔的情緒,把槍放回了營地。也幸好是這一放,讓張表叔躲過了一個處分。
那次械鬥,還真有其他民兵也挺槍上了場。結果,槍被村民搶走了3支,有一支還是經過大排查在一個池塘里找到的。這事就驚動了地區軍分區和公安局,派了大批人員徹查根由。丟槍的那個民兵還被判了一年刑,動槍的和參加械鬥的民兵都受到了拘留或處分。張表叔幸有我父親作證,說明那晚上他是理智戰勝了衝動,沒有參加持槍械鬥,這才沒被辦案人員在「二般」情況下追究刑事責任。
「我跟你爸,也不是一般關係。」在我小的時候,張表叔就對我說,「你爸這個人,重義氣,看得起窮朋友,可交!」說著,他還自豪地告訴我:「我結婚的時候,家裡還住的是爛草房,不過,蓋的可有一條上海產的純羊毛毛毯。那可是你爸送給我的大禮哩!我穿的軍大衣,也是你爸送給我的哩!」
二

「說起你爸,也真是窮大方。」我母親曾在我面前抱怨,「這個張書誠,他也不知上輩子給你爸辦過啥好事,反正你爸對他就是好。你爸在部隊剛提干,一個月也就幾十塊工資,給張書誠買毛毯就花去兩個多月工資。後來,張書誠蓋房子,找他借錢,一張嘴就是500塊,你爸錢不夠,還找戰友借了200塊。」
我曾問過我母親:「那你和我爸結婚的時候,張表叔拿了多少賀禮?」
「可別說拿多少賀禮了。他讓老婆給縫了兩床土布棉被,只拿了60塊賀禮,還說是祝賀我們日子過得六六大順哩。」我母親就不屑地說,「就這你爸還替他辯解,說農村人掙錢不容易。農村行禮一般都是十塊八塊,上30元都是大禮了。還說他老婆縫那可是純棉花被子,還是花格子彩色繡花被面,上頭是手工繡的龍鳳呈祥和麒麟送子,是藝術品,可不能用多少錢來衡量。主貴著哩!」
「我聽說張表嬸後來綉十字綉,一幅也賣過好幾千呢。人家是心靈手巧,算民間能工巧匠呀。」我就說,「那兩床被子,我結婚時你不是還給我一床。美得你兒媳婦直誇是原生態,環保產品呢。」
我母親就笑笑說:「那這都是後話了。你那個表嬸要不是後來腦梗手不靈便了,咱真要叫她再做兩床繡花棉被,她肯定得做。你張表叔家,占咱家光太多了。對了,你知道他家啥時候才想起還咱家那500塊嗎?到你結婚前才還的。你爸那時一個月工資都兩三千了,說什麼也不要他還了。但他倒說得派場,啥子一碼是一碼,非要還。結果哩,錢是還了,你爸聽說他添了孫子,又給他送了200塊賀禮,還買了一個嬰兒搖籃,錢又懟去了一多半。」
母親這樣一說,我不由得就想到了張表叔那個流著長鼻涕的寶貝兒子狗剩。狗剩比我大兩歲,在我記事的時候,每年的夏收和年根之前,張表叔都要到我家串兩次親戚。來家裡的時候,春夏時節多是帶上兩隻雞,或一竹筐大約150個雞蛋和鹹鴨蛋。年根再來的時候,照例是帶著雞鴨或兩隻兔子,再帶些芝麻葉、小磨香油和綠豆什麼的。一住就是個把星期。有好幾次,就帶著他的兒子狗剩。
那時候,我家就住兩間平房,客廳里也擺著一張床,那是我和弟弟晚上睡覺的地方。張表叔一來,我爸就讓我和弟弟調到裡屋和我母親擠一張床,他呢,則和張表叔同榻,晚上盡聊些兒時的人事和當下的農事。張表叔有時也像小學生那樣向我父親問這問那,我父親也就不厭其煩地向他介紹在外的見聞。兩個人總是能低聲聊到深更半夜。聊天的時候兩個人還抽煙。儘管我母親總是提醒我父親開窗通風,每天屋子裡還是煙霧繚繞的。
張表叔每次來家,胃口都是出奇的好。他帶的雞鴨和雞蛋鹹蛋自然很快都吃完了。我父親就買來牛肉豬肉雞魚,又從外邊買來油條、大包子,每頓都是大碗吃飯,大塊吃肉,晚上還要再來二三兩白酒。表叔在我家吃住的那段時間,我和弟弟儘管也看不慣他的不講衛生,比如把饅頭放在桌子上,亂扔煙頭等,但對那段時間家裡天天像過年似的伙食,倒是十分滿意。
張表叔來家是好招待,走的時候,我父親總是要給他備上好煙好酒,還給他塞上一些零花錢。我家的舊衣服和鞋子,也總是由我母親收拾成大包小包,讓他帶回去。那些衣服許多都是八成新,只是在城裡已不時興;有的就是新的,只是找個借口說是樣式不怎麼地什麼的,好讓張表叔收下時不用推辭。狗剩來家幾次,回家的時候,總是被我父母給換得一身新裝。
狗剩直到娶了媳婦,這才不再跟張表叔一起來我家串親戚了。過幾年,倒是他的兒子又成了張表叔的小尾巴。他們來我家,照倒是要住幾天。不過,我家的居住條件在新世紀後已大為改觀。我父母這時已單獨住一套三居室。他們再來,已是吃住不愁了。
這個時候,我父親已經接近退休,卻患上了肺氣腫,已不再抽煙。張表叔卻依舊煙癮大。不過,他知道抽煙對我父親不好,也就強忍煙癮。實在想抽煙了,就去樓下猛吸一根。
三

我父親是在69歲這年去世的。還是因為肺氣腫誘發的心肺功能衰竭。
我張表叔得知我父親逝世時,就急忙從鄉下趕到了我家。見了已躺在水晶棺的他的「忠義哥」,我表叔只是摸了摸好兄弟那早已冰硬的雙手,深沉地叫了一聲:「哥呀,往後想您了叫我上哪裡找您呀!」接下來就泣不成聲了。
我父親停靈那兩三天,張表叔就那麼跟掉了魂一樣守在水晶棺旁,晚上也和我與弟弟一起守靈。他就那麼默默地守著,晚上總讓父親的靈柩前香火燃燒著。時不時地,總見他用衣袖擦著眼角。
送走了我父親,張表叔在我父親去世周年、兩周年、三周年的祭日,以及每年的清明節和農曆十月初一,都要從鄉下來為給我父親燒紙。我母親很感動,在去我弟弟在上海的家養老時就對我說:「你這個張表叔,也確實對你爸有感情。不過,他也年歲大了,明年他再來給你爸燒紙,你給他說說就別再非到墳頭過細禮了。」
這就到了去年我父親去世四周年的忌日,張表叔讓狗剩開了一輛麵包車,帶了火紙、冥幣和饅頭、水果等祭品去了陵園我父親的墓前祭奠。我記住了母親的囑咐,就在執意留下張表叔和狗剩去飯店吃飯後,又特意為他們送上了一箱酒、一箱火腿腸,這才對張表叔說道:「張表叔,我爸也去世三四年了,您這也年年來祭奠他。您這年紀也大了,行動也不方便,往後,就不用再年年來過這個細禮了。人死不能復生,心到神知就中。再說了,疫情也嚴重。」
我這樣說著,張表叔和狗剩還並不介意。狗剩還說:「現在我也算有車了。我爹每年都是在我柳伯的這幾個紀念的日子老早就念叨著。讓他來吧,來了就是看看我忠義伯的墓碑他心裡也踏實哩!」
我聽了狗剩的話,就說:「還是別讓張表叔再年年大老遠跑來跑去了。心意有了念叨念叨就行了。對了,你們就是不來,要是家裡有啥困難,可別忘了告訴我們一聲。我媽也叮囑我,要盡量幫助你們哩!」
「唉!那行吧!」我這麼說了之後,就見張表叔的面容有些板正,長嘆一聲,表示聽從了我的意見。
不想,狗剩卻輕笑一聲說道:「老弟呀,俺們現在過得也還差不多,沒啥困難哩。不過,還是要謝謝你們的好意。」
狗剩說著,就把我送的禮物往車下提,對我說:「我爹眼下也不吸煙不喝酒了,肉也不咋吃,你還是把這些拿回去吧!」
「嗨,你這娃子,咋恁不懂事?」張表叔見我有些尷尬,就訓了狗剩,又笑著說,「那中,我們就回去了,代我給你媽問個好吧!」
說完,張表叔就上了車,狗剩一踩油門,車便轟地一聲開走了。
張表叔這一去,往後確實就沒再來祭奠過我父親,確且地說,是沒有再到城裡跟我聯繫。陵園裡在清明和十月一時有比我還早為父親燒的紙錢,擺的供饗。到底是哪位這樣做的,我總猜想是張表叔的作為。想想我對張表叔的那番話,就又覺得說得有些欠妥了。
疫情期間,我的生意大受影響,尤其是花大價錢盤下的一個飯店,裝修後本想在全面封控放開後迎個食客盈門,誰知卻趕上了人人宅家不出門。這投資眼看是虧定了。
也不知道是誰添油加醋,就把我的經營狀況傳成了負債想跳樓。這消息就傳到了我張表叔的耳朵里。
前幾天,我張表叔就又讓狗剩開著麵包車,徑直來到了我家。見了我就掏出了5萬元,說明了來意:「這錢不多,先給你救救急。家裡還有幾頭牛要賣,再湊個五六萬不成問題。娃子,誰都有個三災八難。只要挺過去,人在,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我還沒到資不抵債的境地,自然是不能收下張表叔父子這份厚禮,便向他們說明情況。狗剩就說:「老弟,俺家也是幾十年得你家我忠義伯的濟,我爹這是真想幫幫你,你別屈了他的心意哩!」
「娃子,俺們這些年日子真的寬綽多了。你遇到困境,客氣了可真小看你張表叔了哩!」
我聽張表叔這樣急赤紅臉地表白,當時也沒了主意,只好把錢收下了。張表叔父子見狀,這就連飯也不吃,開了車一溜煙返回了。
我向母親彙報了張表叔父子的義舉,母親聽了很感動,就特別囑咐我,要給張表叔一家雙倍的報答。我聽了母親的話,雖說是表面應下了,可是,我還不打算急著這麼做。
為什麼呢?我真願意借著這次傳言,在張表叔父子面前扮演一次受助者,讓他們在遙祭我父親的時候,多一些欣慰。
(圖片選自網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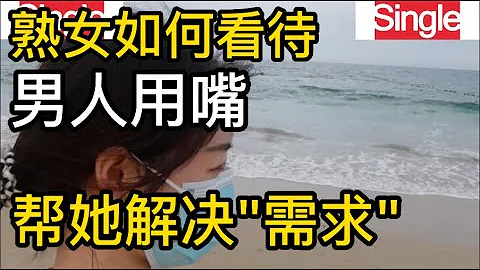











![【搞笑】虧成首富從遊戲開始 [EP176-255] #小說 #繁體中文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lx1W-xi5aE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DQfu9hgfmB9IOhrITD1fLKK0Rf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