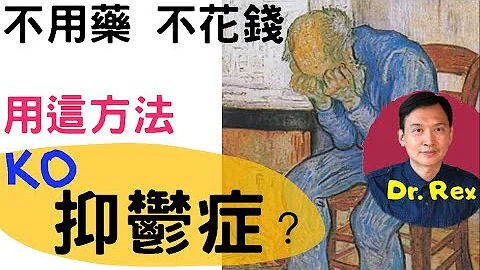「2021年10月,我被確診為重度抑鬱和重度焦慮,身邊的家人朋友無法理解我的痛苦,對於我的種種病症和表現,他們覺得我是『裝病』、是『矯情』。糟糕的家庭關係和人際關係讓我陷入了自我否定。」這是高三學生任瑜(化名)罹患抑鬱症之後的切身感受。
每一個抑鬱症患者都有一根屬於自己的導火索,任瑜的導火索是「不良關係」。
任瑜的家庭是比較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父母有著明確的分工——父親做些小生意維持全家生計,習慣對家庭成員發號施令;母親對丈夫唯命是從,嚴格遵循「嚴父出孝子,慈母多敗兒」的育兒理念。「父親嚴厲且固執,從小到大,我沒有一次能達到他的要求,而且永遠也不會達到;母親很少對我表露愛意,只會板著臉告訴我哪裡做得不夠好。」在任瑜的回憶中,父親就像高高在上的審判官,而母親則是斬殺她快樂的行刑手。
任瑜清楚地記得,初二那年臨近生物會考的一天晚上,自己發起了高燒,她向母親申請休息一個小時再複習,結果父親回家看到她早早躺在床上,沒問緣由就把她劈頭蓋臉罵了一頓,還不顧她的哭喊和反抗,把她生拉硬拽到書桌前做題。母親向父親解釋後,父親不僅沒有道歉,甚至還埋怨母親「慣孩子」。回憶中最後的畫面,是她渾身無力地坐在書桌旁,一邊抹眼淚一邊聽母親嘮叨:「你爸不是故意這樣對你的,畢竟馬上就要會考了,他也是為了你好,你吃點葯堅持堅持吧。」
父親對任瑜有許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不許和學習不好的同學玩、不許和男同學一起玩、零用錢不許買和學習無關的東西……一旦自己違背了「家規」,父親就會言辭激烈地批評她,母親甚至會找老師、同學「討要說法」,這讓她感到無比羞恥和愧疚。久而久之,任瑜的內心深處產生了很難化解的矛盾,一方面她深愛著自己的父母,因為他們與她是有著最親密血緣關係的親人;另一方面她對父母充滿了憤怒,成長路上的無盡委屈隱埋在樁樁件件往事中,強烈卻無力。
沿著「不良家庭關係」順藤摸瓜,可以想見任瑜在並不美好的家庭生活中形成了敏感、自卑、自我苛求、易悲觀、自尊心極強的性格。升入高中後,面對陌生的環境,她迫切地尋求「夥伴關係」的庇護,為了和同伴們「捆綁」生活,任瑜在交往中顯得十分卑微,總是無條件地滿足別人,甚至為了給朋友「出頭」打過架。後來,這些所謂的「朋友」覺得她「太黏人」「太無趣」「沒有主見」「情緒不穩定」,紛紛棄她而去,她徹底淪為孤零零的一個人。
最令任瑜感到尷尬和無助的事情就是上體育課,每逢雙人或多人項目時,她都找不到一起練習的夥伴,只能靜靜地躲到角落裡看別人活動。任瑜覺得自己「被全世界拋棄了」,她開始逃離同學和老師的視線,變得更加怯懦、孤僻,還總是敏感多疑,無論是女同學們三兩成群地討論校園「八卦」,還是青春期男同學們稍顯幼稚的玩笑,都讓她極度厭惡,她總是隱隱猜測同伴背後討論的對象是自己。
起初,任瑜並沒有覺得自己生病了,只是認為自己不適應高中生活,加上對身材和外貌有些自卑,還有敏感內向的性格,導致自己不善交往。可是慢慢地,這種自我否定越來越強烈,她的思想變得越來越偏激,和家裡人的矛盾也越來越多,厭學甚至厭世情緒出現得也越來越頻繁,用她的話說,「整個人被一種巨大的『無意義感』包圍著」。終於,在一次學校組織的抑鬱指數自測後,母親在學校心理老師的建議和督促下帶她去看了專業的心理醫生。最終,任瑜被確診為重度抑鬱和重度焦慮。
即便在醫學如此普及和發達的今天,任瑜的抑鬱症還是被家人和同學「妖魔化」,父母認為她那些抑鬱癥狀是「無病呻吟」,是對家長權威的故意對抗;而那些不了解抑鬱症的同學覺得任瑜得了「精神病」,不敢與之接觸。正因如此,她懷有深深的「病恥感」,不願和旁人透露自己的病情。好在,如今在醫生和老師的幫助下,任瑜逐漸恢復了正常生活,並在醫生的建議下開始學習自我療愈。不久前,她讀了一本名為《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的書,與書中罹患抑鬱症的蛤蟆先生產生了強烈的共情,看到蛤蟆先生最終在醫生和朋友的幫助下重獲新生,她也湧起了強烈的信念。那天,任瑜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人魚小姐也要去看心理醫生。總有一天,我也能在日光下放聲高歌。」
突圍「壞關係」,穿越抑鬱的漫長旅程
策劃 | 曹霽
「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這樣形容抑鬱症。抑鬱症不是簡單的「壞心情」,而是一種疾病。不久前,抑鬱研究所聯合多個機構共同打造了《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在抑鬱症患者群體中收集了6670份有效問卷,調查數據顯示:50%的抑鬱症患者為在校學生;18歲以下的抑鬱症患者占樣本總數的30%。其中,77%和69%的學生患者表示在人際關係和家庭關係中易出現抑鬱。
為更好地理解青少年抑鬱症,幫助青少年走出不良關係的影響,《教育家》邀請專家,針對青少年的「關係型」抑鬱進行解讀,以期推動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張榮華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思想政治教育系副主任
發展與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所長

孫凌
天津市精神衛生中心兒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兒童專委會委員

王一集
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教授
上海市心理健康與危機干預重點實驗室研究員
關係危機為何易引發抑鬱症?
王一集:人具有社會性,需要通過建立關係滿足社交需求、建立歸屬感。對於青少年來說,最重要的人際關係無外乎家庭關係和同伴關係兩大類。
就家庭關係而言,青春期的親子關係本身就面臨一定挑戰,因為這個時期青少年會產生獨立自主的發展需求,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秘密,可能會有意無意地疏遠父母。如果此時父母不能很好地順應、尊重孩子獨立自主的發展需求,比如一味要求孩子事無巨細地向自己報告、包辦孩子生活或學習中的一切,又或者不尊重孩子的隱私,都會對親子關係造成危害。所以,在青少年時期,父母無微不至的照顧和指導可能會成為這個階段親子關係的挑戰。
隨著青少年年齡的增長,同伴關係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他們需要通過建立積極互惠的同伴關係來滿足自己的歸屬需求,或通過鍛煉自己的社交技能獲得重要的社會支持。然而,建立並維繫一段積極互惠的同伴關係並不簡單,由於青少年正處於自我意識覺醒階段,他們在強調自我認識的同時也在擺脫「以自我為中心」,這個過程可能出現的從眾、排斥、拒絕、孤立甚至欺凌等,都容易演化為重大的壓力性事件,給青少年造成心理創傷。此外,青少年在同伴關係中的「滑鐵盧」可能會使其形成負性的歸因偏差,比如覺得自己很失敗,不配得到他人的支持和關愛等,這種對於自我的消極認知也是抑鬱的導火索。
張榮華:根據美國心理學家德西和瑞安等人提出的自我決定理論,人有三種基本的心理需要:關係感、能力感和自治感,即感到自己與他人是有良好聯結的、感到自己是有能力的、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三個基本需要被破壞,就容易影響心理健康,帶來抑鬱。
親子關係不良,如父母在管教過程中對兒童的心理控制,會破壞其自治感和能力感,如果持續較長時間,就會導致兒童習得性無助:「無論我說什麼,你都不聽,無論我做什麼,都沒有用」,從而感到絕望、無助。有研究發現,焦慮與抑鬱的共病率約60%,繁重的學業加上家長的高壓管理,使兒童處於持續的壓力和焦慮當中,長此以往就容易導致抑鬱。
夫妻關係不良會讓孩子感覺家是充滿衝突、冷漠和暴力的,長期處於這種缺乏溫暖、關愛的環境中,兒童的關係感會嚴重受損,以致在人際交往中常常感到孤立無援。在學校環境中,如果兒童缺乏同伴交往,在遇到壓力和困境時缺少社會支持,同樣會影響兒童的關係感和能力感;同伴關係不良還會導致兒童產生孤獨感,這些都是引發抑鬱的因素。
孫凌:抑鬱症發病的關鍵誘因之一,就是「不安全的親密關係」。簡單來說,就是長期處於一段被非常信任的人打擊卻不能反抗(也不能離開)的關係,這種矛盾觸發了抑鬱症的開關。比如,被好朋友背叛或詆毀、被父母長期否定或辱罵等。這些親密關係中,最難逃離的要數親子關係。從臨床案例來看,絕大部分兒童心理問題的成因都與家長不當的培養方式有關。
親子關係是孩子成長過程中最直接的環境因素,如果處理不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使孩子覺得壓抑、委屈、不被理解和信任,甚至會出現暴躁、憤怒、自我傷害、攻擊性增強等情況;如果長期處於不良的親子關係中,還可能影響孩子對自我的客觀判斷以及未來的成長,不知道如何與他人建立並維繫親密關係,以致在未來的職場、交友、婚戀中遇到一系列問題,增加產生心理障礙的風險。


兒童青少年抑鬱症有哪些表現?
孫凌:抑鬱症會對兒童青少年的主觀感受、學習、人際互動與生活品質產生嚴重的損害。患兒在臨床表現上通常具有較多的隱匿癥狀、恐怖和行為異常,其整體的社會功能遭受嚴重破壞,進而增加家人與社會的負擔。不少報告指齣兒童青少年抑鬱症病情較成人更嚴重、病程更長、療效更差、自殺率更高。早期發現、診斷與持續治療對兒童青少年抑鬱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同年齡段,抑鬱症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學齡前期的兒童,由於語言和認知能力尚未發展完全,缺乏對情緒體驗的語言描述能力,往往表現為對遊戲沒興趣、食慾下降、睡眠減少、哭泣、退縮、活動減少;學齡期的兒童可表現為注意力不能集中、思維能力下降、自我評價低、記憶力減退、自責自罪、對學校和班級組織的各種活動不感興趣、易激惹、睡眠障礙、攻擊行為和破壞行為等,嚴重者或表現為頭疼、腹痛、軀體不適等隱匿性抑鬱癥狀;青春期患者的抑鬱癥狀明顯增多,表現為心情低落、思維遲滯、理解和記憶力下降等。與成人不同,兒童青少年常主訴煩躁而非抑鬱,焦慮、激越較為多見,常伴有攻擊或破壞行為、多動、逃學、說謊、夥伴關係不良、自傷等異常行為。
許多家長和教師認為的「孩子不聽話」,其實可能是孩子在發育過程中的神經發育不良或罹患了某些神經發育障礙,無法管控自己,並不是主觀故意行為,例如多動症(注意力不集中,衝動多動,不遵守紀律等)、抽動症(不自主地眨眼、咧嘴、出怪音)、發育性學習障礙(閱讀困難,計算困難,講了很多遍還犯同樣的錯誤)、孤獨症譜系障礙(社交差,不會看眼神)等。另外,兒童罹患情緒障礙時會表現得懶惰或煩躁,容易發脾氣,這都是疾病使然。
王一集:對不具備專業知識的父母、教師和兒童青少年而言,想要識別和區分抑鬱症並不簡單,但也有跡可循。目前就兒童青少年來說,更常見的是間斷性的「抑鬱情緒」而非「抑鬱症」,二者要嚴格區分開來。但如果抑鬱情緒長期未得到緩解,很可能會隨著情況惡化影響青少年正常的生活功能,最終轉化為抑鬱症。
兒童青少年抑鬱症雖然誘因各有不同,但大多數還是與其原生家庭、親子關係等緊密相關,其表徵也是相似的,主要為持續性的情緒低落、對自己產生負面評價,易激動也易疲勞、對什麼事情都提不起興趣等。一旦受到自身抑鬱情緒的困擾,兒童青少年更有可能出現社交退縮的傾向,使不良人際關係和抑鬱形成惡性循環。
張榮華:抑鬱症主要表現為持續的情緒低落、缺乏活力、感到壓抑。兒童青少年抑鬱主要表現為厭學,可能逐漸發展為輟學;厭世,嚴重的可能發展為輕生的想法和行動。除了這些明顯的負面表現,我們也經常會發現,一些看起來很快樂的孩子也患有抑鬱症,那是因為抑鬱的反面不是快樂,而是活力。缺乏活力,對事物缺乏興趣、感到厭倦是抑鬱症的突出特徵。

如何讓「好關係」成就好未來?
張榮華:無論是家庭還是學校,家長和教師都要注重對活力的喚醒,這意味著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更不能是單方面的壓制或付出。通過滿足關係感、能力感和自治感三種基本心理需求,可以有效預防和改善青兒童少年抑鬱。
從家庭教育來看,在親子關係與溝通中,父母要傾聽和尊重孩子的意見,避免心理控制,滿足兒童自治感的需求,但不意味著沒有規則、不管教,而是在制定規則的過程中,要基於平等、民主的溝通達成一致。面對規則,家長要「溫柔且堅定」,避免「暴躁地堅定」破壞兒童的關係感。夫妻關係要和睦,給孩子營造一個溫馨、和諧、有安全感的家庭氛圍,家庭成員之間的良好聯結是改善兒童抑鬱的關鍵因素。此外,家長也要響應「雙減」號召,讓兒童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避免兒童學業壓力過大,把孩子的「個人時間」和「成長空間」還給他們自己。
從學校教育來看,要堅持五育並舉,尤其不能把學業成績擺在學生成長、成人的首位。教師不能一味用權威或經驗主義「壓制」學生,更不能因為個人好惡或主觀印象評價和管理學生,而是要倡導平等、民主、合作的師生關係。當學生有持續的情緒低落、睡眠問題、厭學、人際關係困擾情況時,家長和教師要多加關注,積極學習心理學知識,做到早發現、早治療,科學防治。
孫凌:生病的孩子往往有個生病的家,很多家長只看到孩子的行為表現,卻看不到背後的情緒和精神因素,把問題簡單定性為不愛學習、叛逆或者意志力薄弱。長此以往,導致孩子的抑鬱之路「道阻且長」,甚至出現自殘、自殺等傾向。我們非常理解家長的教育焦慮,以及對孩子未來的競爭焦慮、生存焦慮,但是一定不能忽視了教育的本質和成長的規律。
第一,要重新審視對孩子的教育目標,從對學習過分的關注轉變為對孩子整體成長的關注。要知道,我們要的是一個身心健康、陽光、有良好適應能力的孩子,而不是一個被迫成為學習機器而喪失了快樂能力的孩子。第二,遵循孩子身心發展的客觀規律。大腦發育、心理發展因人而異,家長要接納孩子的全部,帶著希望和發展的眼光靜待花開。第三,尊重孩子的個性喜好,不輕易否定孩子的興趣、想法和朋友,讓溝通變得順暢;及時回應認可,讓孩子不斷獲得價值感和成就感,樹立自信。第四,家長要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只有自己保持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才能給孩子輕鬆、愉悅的成長環境。第五,無論哪個年齡段,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身心健康的前提,家庭成員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穩定、有質量的睡眠,不熬夜,搭配合理的飲食,適度的戶外運動等。
青春期的孩子面臨「依戀情感」的轉移,從依戀父母逐漸轉向依戀同學、夥伴和異性朋友。渴望夥伴關係是青少年成長的一種表現,但很多家長不能正確看待孩子對自己的「疏遠」,時時捕風捉影、過分擔心,導致對孩子的過分干涉、保護和限制,親子衝突也就在所難免。如果父母能夠意識到夥伴關係是孩子成長的必需,多鼓勵孩子交往,面對孩子不良交往關係時,在信任的基礎上適時地表達自己的擔心,保持良好互動關係,那麼孩子的成長一定是溫暖而愉悅的。
同伴是兒童青少年的社會支持,是情緒宣洩的樹洞,也是心理發展和思想演變的同路人。教師要鼓勵學生多與同伴交往,建立各種形式的團體,如足球隊、興趣小組等。此外,教師也不能放過學生之間相處的細枝末節,及時關注被孤立、被欺凌、實施欺凌的學生,正確引導學生開展健康的同伴交往,引導家長樹立科學的育兒觀。
王一集:健康的關係是積極互惠的,孩子能夠從這段關係中得到滋養,變成更好的自己。學會分辨什麼是積極良性的關係、什麼是負面惡性的關係,對於兒童青少年來說非常重要。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對於那些在社交技能方面存在缺陷的孩子,很難建立長期穩定的同伴關係,所以他們更有可能會尋找有相似境遇的同伴滿足自己的歸屬感需求,比如同樣被他人排斥的孩子、同樣家庭生活不幸福的孩子等,這類關係我們稱之為「偏差同伴」。由「偏差同伴」組成的團體會造成問題的互相強化,對兒童青少年的長期發展而言是不利的。對此,家長和教師需要科學對待,從根源解決問題,給予孩子更多的關愛與關注,幫助他們建立彼此接受、彼此尊重、求同存異、互相支持、積極互惠的同伴關係,這需要家庭、學校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糾正不良的校園和社會風氣,包容和理解兒童青少年群體的多元文化。家長和教師需要不斷調試教養方式,尊重孩子的每一個想法。同樣,尊重也不意味著全盤接受,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合理糾偏,讓孩子通過自己的力量找到解決之策。
除了對和諧成長環境和教養氛圍的營造,我們還要關注青少年患者的康復環境。雖然公眾如今對抑鬱症的認知度越來越高,但許多關於抑鬱症的迷思和刻板印象依然流行,亟待加強科學普及。通過加強醫校社合作,開設相應的課程,可以讓學生儘早幫助自己識別病症或為他人的康復提供支持,讓教師和家長學會科學處理。此外,抑鬱症的康復並不意味著患者受損的生活功能和社會認知會自然而然地隨之恢復,所以除了要對疾病對症下藥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患者受損的生活功能和社會認知進行相應干預,比如鼓勵其參與社會活動、增加健康的人際交往等,幫助患者回歸正常生活。
— END —
來源 | 本文刊於《教育家》2022年12月刊第1期,原標題《突圍「壞關係」,穿越抑鬱的漫長旅程》
策劃 | 曹霽
設計 | 朱強
統籌 | 周彩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