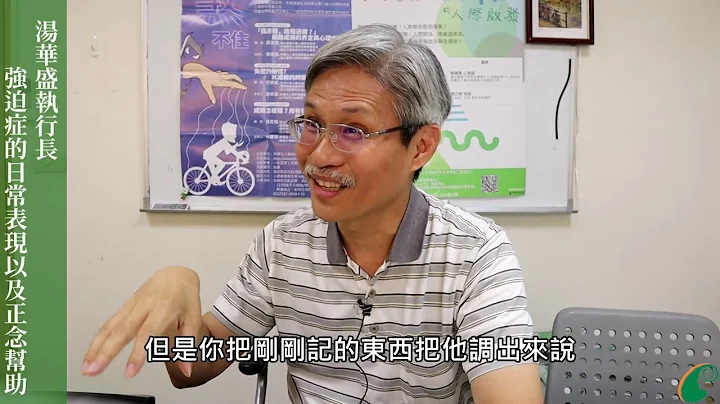心魔的要求與指使
人性之所以充滿魅力,是因為她是獨一無二,靈活自由的,有理性,亦有感情。她會指引一個人的人生方向,並會隨著人生體驗而不斷成長,並完成自己天賦的使命。但當一個人的內心被黑暗的力量掌控,那麼人性就會被壓制,最終成了一個沒有真實的情感與靈魂的空殼。此時,心魔的指令會幻化成各種「應該」,他終將失去作為一個人的自由與靈活。他所做的一切並非出自於他的真心,而猶如一個提線木偶一般被操控。
因為他不曾被真正愛過,所以他不相信自己是可愛的,有價值的,他必須依賴理想化自我的幻想而活,並最終被這個他塑造的東西所掌控。應該不僅來自於理想化的幻想,也來自於維繫理想化自我的存在。此時,他就猶如吸血鬼,而各種應該之物,就是他賴以生存的基礎,他需要不斷地攝取,永無止境,才能維繫虛假的自我不至於在現實面前破碎。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很用力」,缺少隨性與自然,不過最後他得到的並非是幸福與成長,反倒是衝突與痛苦。他也會奇怪,為何別人的追求帶來的是幸福,而他的執著卻帶來了痛苦。也許問題就出在「強求」,畢竟別人是想要別人尊重,並不是一定被人尊重;別人是想要進步,但不是一定要成長;別人是想要被人接納,但不是所有的人;別人是希望自己完美,而不是一定要完美;正常人的需要也是有止境的,但患者的慾念卻是無止境的。就如同一位患者形容他媽媽對他的要求:考了第一名媽媽會責怪他為何不是全校第一;考了全校第一還會責怪他為何會有做錯的題目;就算他成了馬雲,他媽媽還會問他為何不是比爾蓋茨。
「應該」在每個人身上的體現各有不同,這和他理想化自我的形象密切相關。如果他所塑造的形象是聖潔的,那麼他就應該沒有任何人性的污點,充滿愛心;如果他的人設是戰無不勝的強者,那麼他就絕不能認輸和被傷害;如果他維繫的是人見人愛的品質,那麼他就應該讓每個人都滿意,不得罪任何一個人;如果他誤以為自己是完美的化身,那麼他也就無法接受自己任何的缺點與不足;如果他自認為自己是一個偉大的人,那麼他就不能失敗,不能被凡人超越,此時他的幸福就來自於碾壓別人的快感,他要在所有的方面勝過別人。
當「應該」就取代了一個人的真實的情感,就算他善良,孝順,勤奮,熱情,這些也只是一種完美的表演而已。就算他表面熱情,但這不是來自於他真的愛別人,只是害怕被別人嫌棄。
一位患者寫到:我都不知道真實的情感在哪裡,發自內心的情感好像都沒了,做的事情要麼是因為恐懼,要麼就是給自己爭光添彩。自己的內心沒有愛了,我覺得一個連自己都不愛自己,討厭自己的人,他是不會去愛別人的,也不會去愛這個世界。為什麼我不能無條件地愛自己,原諒自己。我始終活得小心翼翼,我長大了啊,可以養活自己了,為什麼我還是要去討好身邊的人,怕他們離開我,拋棄我,討厭我。三十多年,我一直這樣活著,我都不知道真實的自己和內心的情感在哪裡了,我把真實的自己丟了,很小就丟了,我應該做個怎樣的人早就取代了我本來是個怎樣的人。
也許,在生活中他懂得如何關心別人,如何共情,如何察言觀色。看似他懂事和明理,但從本質上來說他缺乏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畢竟他沒有心,缺乏真正的情感。看似他有很多朋友,但從本質上來說他不愛任何人,不敢讓任何人了解真實的他,朋友的數量只是他維繫安全感的手段。有時,為了人際的和諧,他也不敢表達任何反對意見,就算委屈自己也從不和別人發生衝突,在生活中他只有該與不該,而沒有想與不想,甚至都規定了說話的時候應該用什麼表情,來回應別人,而完全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實情感來生活。
患者喪失了對自己的忠誠,從此從「自轉」變成了「公轉」。所謂自轉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為了自身的利益來活;而公轉就是為了別人著想,在乎別人的感受,把別人看得比自己都重要。

雖然他會把「公轉」看成美德,但實際上他和一台適應良好的機器沒有什麼區別,他不敢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因為真實對他意味著醜陋。此時,從人的屬性上來說,他早已經不再是一個真正,真實的人了,他就如同一個木偶,一個瓷娃娃,沒有生命力與活力。他努力維繫他自認為應該具備的品格,他努力成為別人希望他成為的樣子,他努力成為一個不被嫌棄的人,但結果他卻丟了他自己。
一位患者寫到:我好累。我又開啟了機器人模式。我這個機器人沒有心,是一個空心機器人。我吃飯、睡覺、散步。我知道該幹嘛,不該幹嘛,冷靜得可以,理智到不行。這種理性是個障眼法,可以騙過所有人,可以瞞天過海。說謊的終極模式就是將自己一起騙了。洗腦的最佳模式就是先將自己洗腦。我知道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什麼時候該做出什麼反應。我知道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怎樣的心態才能將我最好地保護起來。我甚至連每一個表情都經過思量。可是我沒有心,我將心藏起來。這是一篇空心人日記,這是我多年來的生存方式,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
當一個人失去了人性的自由與靈活,就算微信聊天和朋友圈這種小事情,他也總是要斟酌再三,多一句,少一句,該發還是不該發他都糾結。當應該對他的生活掌控的越來越深,甚至是應該先吃蘋果,還是先吃麵條;應該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是從左面走,還是右面走都會糾結。一位女性患者,在飯店撿了五毛錢,本來想收著,但又焦慮,畢竟這違反了她道德的應該,最後還是給了老闆。
所謂的「好人」只不過是壓抑了自己的情感,以維繫好人的假象,這樣既騙了別人,也騙了他自己。在這個人畜無害的形象背後,實際上壓抑了太多對他人及這個世界的憤怒與不滿。但他不敢表現出自己的人性來,甚至不敢意識到,當一位女性患者在分析中發現在聖潔的外表下其實隱藏著一個自私,小氣與狹隘的心的時候,她突然崩潰,匍匐在地上打滾,因為她不敢面對,這就是她自己。
一個人越是躲在聖潔的背後,在內心深處就越是隱藏著一個壓抑扭曲的靈魂。他會感覺有兩個自己,一個是殘暴的,一個是聖潔的。他只敢讓給別人看到白的部分,而黑的部分他則深深地壓抑了,有時甚至連他自己都意識不到其存在。一個人越把自己塑造成好媽媽,好爸爸,好領導,好同事,好孩子,內心就越沒有愛,外在的情感只是掩蓋了他內心中的冷漠與扭曲。所以,當一位「好媽媽」在孩子沒有聽話,沒有按照她的期待來發展的時候,她竟然會在夢中咒罵孩子醒來,或夢到推開孩子的房門,孩子已經死了。此時,我一點都不奇怪,畢竟孩子只是維繫她完美的工具,當孩子破壞了她完美的形象與要求,她當然會氣急敗壞。不過因為她有好媽媽的應該,所以她壓抑了憤怒,但憤怒並沒有消失只能在夢中戲劇化的表達。她只是應該正經,強大,聖潔,完美,撕下這些面具,在她內心深處實際上是空的,荒蕪的,甚至是黑暗的,沒有一絲光亮。
就算患者意識到了應該與標準的病態,但依然停不下來,畢竟這股力量是想讓他變好,方方面面的好,只要他不能接受自己的不好,那麼就會依賴這股力量並被其指使。所以,應該具有強制性,和地主對農夫的逼迫,納粹集中營的皮鞭沒有什麼不同。一位患者在評價這種應該之暴行的時候談到:這就如同水晶做的鞋和鋼鐵做的衣服,就算並不合身,他依然非要往裡面塞,就算自己的身體已經血肉模糊他都不會在意。
因為虛假的自我是一個東拼西湊的工藝品,看起來很美,但實際上並非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具有矛盾性——各種應該的指令之間,應該與現實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將破壞他作為一個人的有機整體性,並最終演變為內心的撕裂。
他應該正常,應該乖,應該有好的形象,應該超過別人,不應該吃虧,不能比被人差,但又不能招人反感。但這些應該本身是不兼容的,畢竟一個人不能既要和諧,但又不能吃虧;既要做強者,還要做聖人;既要凌駕於他人之上,又要讓別人覺得自己有修養。例如,一位患者開始試圖維繫好人與和諧的應該,在生活中他就會處處隱忍,但壓抑了一段時間,他又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傷害,那麼他就會想辦法報復對方,但報復的行為又引發了他的恐慌,這又和之前維繫的完美的形象不符。並且經過治療他又意識到過度順從與聽話都是不正常的,而他又有正常的應該,所以他又逼迫自己決不能做老好人,結果一反常態,開始「逆反」——任何順從別人的安排都被他認為是病態。此時,他想要辭掉工作,因為工作是媽媽安排的;他想要改掉孩子的名字,因為名字是老婆取的;他想要吃麵條,如果爸爸做的是菜飯,那麼他也一定要吐出來。累積了一段時間,他又發覺自己罪孽深重,內心的法庭又宣布自己有罪,他又覺得自己傷害了別人,之後他內心滿是愧疚感想要補償別人,但補償行為過後,他又覺得這是懦弱的表現,之後又開始和別人發生衝突,與此反覆永無終結。
不僅應該與應該之間,應該與本性之間也會存在衝突。一位男性患者,他要求自己要成為一個絕對的強者——他不能被欺負,傷害,不能認慫,不應該和那些弱者一樣任人擺布,一旦吃虧,一定要變本加厲地還回來,他要讓那些傷害過他的人匍匐在他的腳下求饒。這時他就好像一個好鬥的戰士,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自尊的維繫上。所以在別人眼中的小事,在他這裡都涉及到了面子與自尊,他必須爭回來。例如,不管是走路還是開車,他從來不會讓路,因為這樣就好像自己輸了,就算迎面走過一個人,他非要頂撞過去,不能讓路,這樣才能顯得他無所畏懼;在和別人目光對視的時候,他也非要等別人主動移開目光,不然就好像自己怕了對方;在教室里別人過了三八線或位置的空隙比他大,他都要擠回去;在做節目主持人的時候,他也必須是C位,一旦沒有符合他強者的應該,就會引發他的恐慌與憤怒。他的憤怒不僅會演變成一種對他人的報復性的衝動,也同樣針對自己,這時他就會嘲笑自己:看你是那麼的弱小,是個人都敢欺負你。
但這樣卻讓他變得撕裂,畢竟他表演的強大與骨子裡的弱小之間成了一種衝突,他只是假裝強大,而不是真的強大。雖然他看似渾身長滿了刺,不過他內心卻非常恐慌,他怕被打,被殺,擔心再次成為那個連他自己都瞧不起的懦弱的人。
理想化自我就好像一個裝修良好的店面,或粉飾良好的公司賬目。而這一切的背後卻是一個黑心的血汗工廠,一個拿著鞭子的魔鬼,不斷地在抽打,恐嚇,威逼利誘,不斷地逼迫和壓榨他。
在沒有看清楚心魔的邪惡,他痛恨的並不是這些壓迫他的應該,他恨的是無法達到應該的自己。無論多小的事情沒有做到應該之要求,都會引發他強烈的自責與自我攻擊。這種攻擊可以表現為很多形式,有輕度的自責與自卑,有中度的自我憎恨,還有極端的自我毀滅。應該彷彿成了他個人化的法律與清規戒律,不能有任何的違反,不然他的內心就會展開對自己的審判。
所以患者經常會後悔與反省,如果白天做了什麼不好的,讓他不滿意的事情,他就會陷入到深深的自責,有時甚至會在夢中驚醒。為了避免犯錯,他會經常性地監控自己的言行,就好像一雙眼睛在一刻不停地盯著他。他就好像生活在電影《竊聽風暴》的情節,他的一舉一動都在被監聽,一旦有任何「非法的行為和思想」就會被逮捕,他內心中就好像有一個東德國家情報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權控制著他自己。
一旦心魔的指令(應該)沒有實現,那麼他就會受到無情的鞭打,甚至想要毀掉自己。但患者可悲之處在於,他已經被心魔洗腦,被應該控制,他往往會認為他應該的,也是他想的,結果喪失了反抗的能力與動力,一味地貶低自己,認為自己無能與無用。

他的內心好像有一個聲音一直都在苛責他,否定他,嘲諷他,無論怎麼做都無法達到那個聲音極致完美的要求。例如,一位女性患者,雖然眼部的整容手術都已經進行了三次,不過她依然有衝動要繼續手術,因為那個聲音依然會說她眼睛不夠完美與自然。後來她學習了心理學,當給別人做諮詢的時候,那個聲音依然在批評她理論知識不夠,雖然她的患者對她很滿意。她意識到做任何事情都會有一個聲音在背後要求和指責他,如果她索性不做了,那個聲音依然沒有放過他,依然在責怪她無能和逃避。而冷靜下來的時候,她突然意識到這像極了小時候媽媽苛責她的口吻,無論她如何努力,如何完美,在媽媽的眼中她永遠都是醜陋的,無能的廢物。
這種自我審判有時也具有滯後性的特點,也就是秋後算賬。當他有失敗和不足,被人討厭或有人對他不敬,這些小的事情往往在常人眼中並不會當回事,但卻會在患者心中不斷累積,累積到一定程度爆發。例如,一位患者甚至想把自己手指頭剁掉,而引發衝突的事情往往是他之前說過別人壞話,和親戚發生過衝突,小氣地沒有把水果分給婆婆或幻想和別人曖昧。因此患者極容易崩潰,表現形式有抑鬱發作,揪住自己的頭髮,匍匐在地上,會咬,打,用刀割,或把頭往牆上撞。這似乎成了他平復內心衝突的手段,成了他減壓的方式,當不順利的事情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控制不住地爆發。
患者也會把這種強烈的自我譴責與憎恨外化,認為是別人對他有敵意,看不起他,甚至想要傷害他。例如,一位患者當聽不清楚別人說什麼時候,他總是擔心別人在罵他,說他有病,此時他就會強迫性地讓被人再說一次,就算別人回應了他,不過他依然不放心,認為對方沒有說實話。當然,這種敵意並非是來自於外界,而是內心——不是別人憎恨他,而是他一直在內心中憎恨他自己。
有時,自我憎恨也會反應在夢中,諸如,他會夢到大便和垃圾跑到了自己的身上。嚴重的時候他甚至可以聽見一個聲音以第三口吻說:你都這麼失敗了,怎麼還不去死?
一位女性患者做過這樣的一個夢:一個她討厭的女性,記不清臉,但自己憎恨她,她和一個男性殺了她。之後自己很得意,因為她做公交車回去,而沒有開自己的車,她認為這樣警察就不會找到她了。也許夢中那個看不清臉的女人,正是她自己。一個人,越想活在完美的自我之中,就越是想「殺死」現實中這個不完美的傢伙。
當患者無論怎麼做都無法滿足應該的指令,無論怎麼做都無法逃避自我的責罰,那麼他只能通過拖延、逃避和依賴來緩解衝突。畢竟,不做就不會犯錯。一位患者拖延很嚴重,比如,大學的畢業論文,不到最後一刻,他是不會交的,而學校的考試他從來都不參加,一來他認為學校的考試沒有意義,太簡單了,不代表自己的水平,另一方面,他擔心現實來檢驗他的能力,讓他意識到自己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優秀。他通過逃避和拖延維繫了自負,也逃避了沒有達到應該時候的壓力與責罰。所以,他從不敢認真地生活,畢竟一認真他就輸了。
有的患者也試圖逃避現實,逃避生活,逃避責任,藉此來逃避應該,但只要應該還在,逃到哪裡都不是桃源。例如,一位男性患者移民美國,因為他在中國待不下去了,因為在這裡他有太多的失敗,諸如,學生時代他被打過,做生意的時候失敗過,追求女孩也被拒絕過,自己也在不斷地衰老。他幻想在美國就可以重新開始,就可以不必面對自己的失敗。
剛到美國他喘息了一段時間,但時間一長他的挫敗感就開始慢慢累積,例如,雖然他總是試圖做一個完美的父親,但現實中他卻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他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爸爸,內心中有對女兒強烈的虧欠感。為了逃避這種負面的情緒,他又從美國逃回了中國,不過老婆的電話又引發了他新的愧疚,他覺得這樣就沒有陪伴孩子成長,沒有符合一個好父親的應該,並且也沒有盡到一個男人對家庭的責任。他又開始了新的自恨,認為自己的罪行無法原諒。
最終他只能通過藥物和女人來緩解焦慮,但這又觸碰了他作為一個好人的應該,緩解焦慮的方式最終又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最終成了一個「罪孽深重」的人,認為自己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之上。但按照他如此完美的標準,這個世界上又有幾個人配活呢?
一位患者寫到:內心長了一隻蛀蟲,它一直在啃蝕我的心,讓我潰不成兵,百孔千瘡。這隻蛀蟲便是高標準、嚴苛甚至非人類的要求。一點不會就自卑,一點不懂就卑微,一點沒做好就糾結好久,總是批判自己,認為自己不好。我其實已經比很多人優秀了,若把我的標準放到任何一個人身上,他們就都不要活了好吧!明明一個普通人,天天用非人類的標準要求自己,她不痛苦到要死要活才怪呢!我總能挑出毛病來,總能一眼瞄準自己或別人的缺點,眼睛犀利無比,充滿審視。容易自卑的人,不在於她真的不夠好,在於她的標準太高,她永遠夠不著達不到,所以永遠都不滿足,對自己不滿意。我的標準假設是100,別人的標準便是30,我自己本身能有60,在別人的標準那裡,我理所當然自信!我不該自卑的,錯的不是我,是這個高標準。
如果患者怎樣努力都無法達到這些「高標準」,他也會選擇依賴,依附於一個看似完美與強大的人,似乎就成了一種對自己的救贖。此時,他會表現為無法自己做決定,選擇困難,依賴強者與權威。小時候他依賴的對象是父母,之後是某個人生階段中自負有主見的朋友,結婚後也許配偶就承擔了這樣的角色,如果他開始心理治療,那麼治療師就成了他依賴的對象。依賴給他的好處有兩個,一來,降低他犯錯的概率;第二,就算犯了錯,也不是他自己的錯,而是出主意的人,這樣他就避免了內心的責罰。
此時,他會事無巨細地把生活中的瑣事說給他依賴的對象,讓他們幫自己做決定,做選擇,就算這些事情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諸如,是否應該刪除一個他討厭的人的微信,是否可以拒絕一個朋友。
這樣的患者往往是在壓抑的家庭中長大,有一個強勢的媽媽或爸爸(一般而言媽媽居多),這個家長往往控制欲極強,什麼事情都教他該怎麼做,做了之後還會不厭其煩地來糾正他,非要孩子做的和自己想的一樣。一旦孩子不受自己控制,他也許會責罵,也會變得冷漠,也許會用哭泣讓孩子內疚。一位女性患者就算高中了都不能決定自己買什麼樣的衣服,梳什麼樣的髮型,甚至拍照的時候媽媽都指揮她該用什麼樣的表情,就算上大學了,媽媽依然會一天一個電話,一個電話一個小時,讓她來彙報這一天都做了什麼。雖然她也很煩,但卻成了習慣,她的「臍帶」依然沒有剪斷,遇到她難以解決的問題,她也會習慣性地問媽媽的意見,這樣她和媽媽成了一對病態的夥伴。

想要脫離應該的掌控,就要放下理想中自己的幻想,也要在每次痛苦與掙扎中加深對應該的認識。如果能放下一些應該,想必他生活的域限就必然會被拓寬,他的自由度必然會被擴大,所以每一步努力都是值得的。
隨著對自我認識的加深,遲早有一天他會覺察到,他應該的並不是他真的想要的,也並不能讓他幸福,只會給他帶來無盡痛苦與掙扎。當他發現自己就好像是一個傀儡與附庸,沒有任何自由與權利,此時,他才會產生對自我的同情,對自由產生渴望,想必這才是真正建設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