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南一案暫時平息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天,一位武官打扮的人在太監的引領下來到了嘉慶皇帝的御座跟前,但見那人"撲通"一聲跪倒,先是一陣嚎啕大哭,哭得嘉慶帝莫名其妙。嘉慶帝畢竟是一國之尊,胸有成府,有容人的海量,耐著性子等那人哭完之後,和顏悅色地問道:"你有何事,有什麼委屈,請慢慢地說來,朕為你做主!"
"我乃受水師提督派遣,特來向皇上彙報近來海疆情事!"
"海疆情事,近來海疆情況怎麼樣了?"嘉慶急切地問道。
嘉慶皇帝即位以來,有兩件事最令他感到頭疼和棘手。第一件事就是前面已經敘述的白蓮教農民起義,第二件事就是浙、閩、粵等地海盜不斷滋事,擾得沿海居民無法生產和安定地生活。而且這海盜是內外勾結,兵匪一家,勢力甚為強大。這外部勢力是最為棘手的因素之一。

乾隆五十一年,清朝的藩屬國安南(今越南)曾經發生了一場爭權奪利的內亂。安南國內的阮光平、阮光纘父子(俗稱"新阮")發動政變,從其國王黎維祁手中奪去政權。這一行為引起了黎維祁的外甥阮福映(俗稱"舊阮")的強烈不滿,他遂以正統自居,號召人民群眾起來反抗,最後雖然阮光平、阮光纘父子基本上鞏固了統治,阮福映的勢力也仍舊存在。"新阮"雖然經過一番爭戰取得政權,但是也處於國破民窮、財政困難的境地,為維護其統治,阮氏父子就唆使其官兵出海為盜,掠得錢財與阮氏政權"分紅",從而彌補其財政上的一部分虧空。這些海盜的目標首當其衝地就指向了勢單力薄的中國商人,同時不斷騷擾沿海居民,沿海居民為此災害連連,叫苦不迭。乾隆皇帝曾因此發兵征討安南,暫時解決了問題。

但是到了嘉慶在位時,海盜仍常年出沒於沿海,特別是嘉慶二年,一批海盜在羅亞三的率領下竄至中國沿海,為非作歹,作惡多端,引起沿海人民的強烈憤怒,震動了清廷。清朝出動水師,經過艱苦作戰,俘獲了這批海盜。經嚴刑拷打審訊,查明這批海盜的頭目為羅亞三,內有安南總兵官十二人,安南烏槽一萬餘號,並有繳獲的官印、旗幟等實物為據,這都足以證明海盜實受安南國王阮氏的支持。此時正被農民起義困擾得焦頭爛額的嘉慶帝,雖然感到這是屬國安南對天朝上國的至上尊嚴的明目張胆的藐視,如果此時出兵討伐安南,也可以說名正言順,師出有名,能夠得到人民的擁護。但嘉慶帝經過審慎考慮,沒有像他父親那樣好大喜功,而是十分克制,只是通過軍機處諭示兩廣總督說:"……是此次烏槽夷匪,皆得受該國王封號,其出洋行劫,似該國王非不知情,若令會合,彼豈肯聽從,且內地人民出洋為盜,尚不能官為禁止,何況外夷,倘安南藉此抵飾,何從與之三分辨,又豈值因此生事,興師征討該國耶?!去慶等唯當於閩、粵、浙三省洋面,通同會擒,遇有外洋駛入夷匪,無論安南何官,即行嚴辦……"
處理對外關係問題一向如此謹慎的嘉慶帝,此時又該當何為呢?
來人聽嘉慶帝詢問海疆情況,且口氣是那樣的焦急,那樣的關切,急忙用衣袖揩乾了眼淚,抬起頭回答道:"我皇聖明,我等大清水師官兵,向來恪遵皇上旨意,從不輕開外釁,而是忠於職守,嚴格訓練,日夜巡邏,常備不懈,時刻守衛著我大清海防。但那些外夷海盜,看我等官兵並不主動擊出,以為示弱,不斷滋生事體。同時海寬洋闊,我等兵少力薄,儘管我們都盡了力,但仍有一些海盜不斷窺探時機,出沒於沿海各地,擾我居民,劫我商人,沿海居民人心惶惶,正常的生產貿易無法進行,人們毫無安全感可言。此次事件,更是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次情況如何?"嘉慶帝打斷來人的說話焦急地問道。
"這次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一日,我大清漁船、商船為避風浪,進入一處三面環島,只有一處狹窄入口的天然避風良港。不料一群埋伏多時的海盜殺了出來,不大一會兒,男人被海盜殺死、打傷,女子大都被海盜們擄掠而去。劉振東、張大明二人大難不死,到大清水師提督府報告了情況。我水師官兵義憤填膺,很快來到那伙海盜藏身的避風處。進到港內,就見那伙海盜們有的在狂飲大嚼,有的在淫辱那被掠擄的女子。大家看到這不堪入目的一幕,個個怒不可遏,爭先向前,殺向那海盜,很快這批在漁民、商人們面前不可一世的海盜們,紛紛敗下陣來,一部分負隅頑抗的被殺,一部分跪地求饒的被俘虜,從繳獲的物品中,我們還搜到了這樣一件物品,請皇上過目。"
說著,那位軍官把隨身攜帶的一個黃布包裹遞了上來。嘉慶帝打開一看,眉頭不禁擰成了一團,原來,那包裹里包的正是安南國國王賜給這批海盜的印璽和文書,且文書中白紙黑字,說得清清楚楚,海盜的槍支彈藥、船隻補給由國家補充,搶得財物後四六分成,視財物的多少,功勞的大小,分別給予加官晉爵。這嘉慶帝怎能不氣!
來人向御座上看了看嘉慶帝一眼,顧不得嘉慶帝正在氣惱,又繼續說道:"卑職在此謹向皇上表達我官兵的殷切心情,請求皇上快發義師,征討安南,為我民復仇,揚我國威,安我社稷,固我海防!"

嘉慶帝聽完了來人的敘述,示意下人把來者帶下去安排食宿,殷勤招待,以示慰撫。嘉慶帝捻著其稀疏的鬍鬚,眉頭擰成了一個"川"字,陷入了沉思。這安南國王,仰承聖恩,不思回報,卻助紂為虐,擾我邊民,掠我商人,著實可恨。"為民復仇,揚我國威,安我社稷,固我海防",民心所向啊,名也正,言也順,如果真的發那麼一支義師,打那麼一仗,既滅了安南國海盜的威風,也長了我大清的志氣,也能為我的皇帝生涯增光添彩,後來的史書也能大書特書,名垂青史!但這"打仗"二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嘉慶帝作為一位三十多歲當上皇帝的人,雖然少了一些年輕皇帝的血氣方剛,但他對國家的事務是相當了解的。其父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為圓其所謂"十全老人"的夢想,不管條件具備不具備,仗該打還是不該打,最後硬是打了那麼多的仗,成全了其所謂的"十全武功"。雖然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的古訓,使得嘉慶帝對其父的行動不能有半點非議和微辭,但他的心裡是十分清楚,正是他的父親乾隆皇帝幾乎敗光了其祖上的產業,使他接下了一個爛攤子。如今內顧尚且不暇,還能輕言對外開戰嗎?大清的國力還能經得起戰爭嗎?一系列的問題縈繞在嘉慶帝的腦海之中,嘉慶帝一時無法做出決斷,他決定把這一問題交給大臣們議一議。
"眾位愛卿,"嘉慶皇帝向御座下掃了一眼,發現御座分兩旁站立的大多數子可能是被剛才來人的陳述所感染,臉上出現了難抑的憤怒之情,說道,"剛才來人所述的情況,想必你們已經聽到了,朕深為沿海居民遭此不不幸,深表惋惜,你們看,我大清該不該興發義師,征討安南,以示懲罰!"

"皇上,"伴隨著一聲宏亮的聲音,一位兩鬢染霜,鬚髮皆白,臉上刻滿雪雨風霜的皺紋的老臣從隊列中走了出來。"臣下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嘉慶定睛一看,走出來的大臣原來是先帝時的老臣辜一銘,這些年來為鞏固大清社稷沒少出謀劃策,忙謙和一笑,說道:"請講,朕就是要你們各抒己見。"
"臣下竊以為,陛下聖聰,德加四海,兼統萬國,兆民悅服,這安南國本我大清朝藩屬,理當是年年來朝,歲歲來貢,以報聖恩,然而安南國不識君臣之禮,非但不履行屬國之責,反而不斷縱容其官兵犯我沿海,劫我商人,掠我居民,如果不出兵征討,以示懲罰,這勢必有損我大清皇朝的尊嚴,此應出兵征討理由之一;出兵征討的理由之二,沿海居民屢遭海盜騷擾,生產生活無法正常進行,群情激憤,此時出征乃順天理、得民心之舉;出兵征討的理由之三,我大清朝不僅只有一個安南屬國,還有那朝鮮、緬甸、廓爾喀等國,如果任由其縱容海盜而受不到懲處,這樣我大清朝的其它屬國也可能紛紛效仿,因此我皇理應興發義師,征討安南,為我民復仇,壯我國威。"

"臣以為不可,出兵打仗乃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萬萬不可輕舉妄動。"又一位大臣急切地從隊列中站了起來,走到嘉慶的御座前。"請慢慢講來,朕願聽聽你的高見,"嘉慶帝說道。"臣以為,出兵打仗最講究的就是那'天時、地利、人和',從這三方面來說,我大清朝都不宜出兵打仗。第一,現在時值農曆七月份,正乃天氣炎熱之時,而安南國更是酷暑之地,如我軍勞師遠征,這兵士首先不能克服的就是酷熱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可能相當一部分士兵,不會死於敵人的刀槍之下,而要倒斃於中暑;第二,要出兵征討安南,遇到的又一個問題就是安南複雜的地形,特別是與我大清接壤之處,山高嶺峻,坡陡溝深,林密草深,荊棘叢生,敵人易於隱藏,而我軍處於明處,易受敵人襲擊;第三,如若我出兵征討安南,雖屬義師,但是到了安南境內,也會引起安南民眾的反感,同時,安南還會對其民眾進行蠱惑和煽動,我大清義軍必會遭到安南民眾的襲擊。基於此,臣以為萬萬不可出兵打仗,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請我皇聖斷。"
"不,這是一種懦弱的、懼敵的言論,"一位大臣怒氣沖沖地從隊列中站了出來,還未等嘉慶帝開口問他有何高見,他就急不可待地說道,"我大清建立一百多年來,兵多將廣,威加八方,德惠四鄰,外夷來朝,如今我皇屢出仁慈之念,而安南國不識大體,屢屢逞狂,理應徵討。首先,海盜的不斷騷擾,已引起我沿海居民的極大憤怒,民心可用,師出有名,名也正,言亦順;其次,安南國的阮氏政權並不鞏固,其國家可謂是國破民窮,民不聊生,財政困難,軍隊戰鬥力虛弱,毫無抵抗力;第三,我大清地域遼闊,物產豐富,我大清的軍隊這多年也從未停止過戰鬥,士兵經歷過戰事考驗,將領有指揮作戰的經歷。總之,我大清朝出兵安南,必獲全勝,請皇上速下決心!"

"恕我直言,此仗萬萬打不得。"又一位大臣從隊列中站了出來。"為什麼?"嘉慶帝問道。"我皇聖明,臣以為這仗不可打的原因如下: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敵我雙方的情況如何呢?臣以為,第一,我大清出師征討,是勞師遠征,天長日久,人困馬乏,而敵方則以逸待勞;第二,出師征討安南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軍需補給,而我南方地區及安南北部皆為山區,山高嶺崇,坡陡溝深,交通不便,運輸不利,軍需供給相當困難,如解決不了軍需供應,軍隊勢必會出現搶掠民眾的現象,這必將引起人民的反抗、不滿;第三,自從陛下即位以來,大清朝的統治受到川、楚一帶白蓮邪教的威脅,我朝費時九年,滅了這股賊眾,但為此我大清花費白銀不下億兩,造成國庫虧空、財政吃緊;第四,這……第四……"
"第四怎麼樣?"嘉慶帝問道。"臣不敢直言。""朕恕你無罪。""謝皇上,臣以為這第四,就是我大清朝的軍隊在鎮壓川、楚白蓮邪教的過程中表現不佳,並不是威武之師,而是紀律鬆懈,裝備不良,戰鬥力虛弱,憑這樣的兵力出師遠征,臣以為取勝的把握實在渺茫。"
嘉慶帝聽得這話雖然感到有點不自在,但也確實讓這位大臣說到了實處,只是自己不便說出,想想確是實情。就那烏合之眾的白蓮教徒,起初勢力並不十分強大,按說,大清軍隊一到,他們還不作鳥獸散,然而其勢力卻如燎原之火,最後整整燒了九年。
嘉慶帝理智、審慎且極為克制地處理了同安南的關係,諭示兩廣總督吉慶道:"海盜夷匪,得受該國王稱號,其出洋行劫,其國王並非不知情,若令會合緊賊,彼絕不肯聽眾,但若出兵征之,則勞師苦民。且內地民人出洋為匪,尚不能官為禁止,何況外夷。爾等可與安南交涉,並于洋面嚴以會擒,遇有外洋駛入夷匪,無論何國何官,一體逮拿,當即正法,毋庸解京。"
後安南內亂,皇上諭令絕不干涉其內政。安南雙方俱解海盜至大清,海疆於是平靜。

公元1809年,即嘉慶十四年,正月,某一天。點點的小雪花飄撒在偌大的京城。
雪花很小,也不甚密,但許是飄得太久,圓明園內一片素白。天是灰滾滾的,地也是灰深漾的,只有不停飄落的雪花,給天地之間罩上了一層冷清清的白光。
驀地,從圓明園內,傳出一陣雖不很整齊但卻非常清脆的吆喝聲:"安樂渡--"其聲遞相傳呼,悠揚不絕。仔細看去,福海的四邊岸上,擠滿了千姿百態的宮女們。雖是雪天,雖是這個難以分辨朝朝暮暮的時候,但宮女們身上的紅妝綠束,似乎也給這萬物蕭條的季節多少增添了一絲春意。
在宮女們的輕聲漫呼中,一隻彩舟緩緩地離了湖岸,慢慢地向中心島駛去。彩舟雖小,但裝飾得富麗堂皇,尤其是舟首的一條金龍,盤曲直指蒼穹,似是在對灰漾漾的天空發問。金龍的旁邊,筆挺挺地立有一人。此人雙眉緊鎖,目光迷離,像是蘊著滿腹的憂愁。顯然,能和金龍相依偎的,必是當今皇上嘉慶帝無疑了。
清例規定,若是皇上泛舟福海,宮女們必聚集四周,同呼"安樂渡",直到聖上登臨彼岸為止。往日,嘉慶帝在此乘船遊玩時,聽著宮女們此起彼伏的呼聲,心中還是很高興的,他會在有意無意中感到一種滿足,感到一種高高在上的威嚴。然而現在,宮女們都一聲接一聲的吆喝,他感到異常地刺耳。他竭力想把那些聲音從雙耳里驅趕出去,可是,那些聲音卻頑強地從他的耳里鑽到他的心坎里。他受不了,轉身對恭立在後的鄂羅哩道:"鄂公公,傳諭下去,朕不想再聽她們叫喊了。"
"是,"鄂羅哩連忙答道,"奴才這就照辦。"
鄂羅哩是宮中一名資深的大太監,自乾隆朝就近侍皇上,時年已近七十,虧得身體尚好,耳不聾眼不花。蒙皇上恩寵,叫他一聲"公公",他便越發對皇上盡心儘力了。因在皇宮日久,又常伴皇上左右,故他對皇上的心思往往能猜出個八九不離十。他知道皇上近來的心情不好,所以侍奉皇上就更加殷勤。

昨夜皇上留宿萬春園,他幾乎一夜未合眼,隨時聽候皇上的差遣。今天一大早,皇上就帶著他來到了福海的岸邊。看著皇上沖著空寂寂的湖面有些發愣,他便小心翼翼地道:"陛下,此時此刻,若乘一葉小舟在湖面上蕩漾,確有一番詩情畫意。只是,天氣正寒,又飄著雪……"嘉慶一揮手道:"鄂公公此言正合孤意。快去找一小舟來,朕要踏雪橫渡。"鄂羅哩忙道:"陛下,奴才剛才說了,天寒,又下著雪……"嘉慶突然大笑起來:"鄂公公有所不知,古人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朕雖沒有蓑笠,也無心去垂釣,但此刻乘舟橫渡,多少也能領略一些古人詩中的意趣。鄂公公,你以為如何?"鄂羅哩趕緊笑道:"陛下聖明,奴才這就去準備。"而實際上,鄂羅哩早已把彩舟和宮女們都安排妥當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上今日對宮女們的呼聲突然厭煩起來了。
鄂羅哩不敢怠慢,雙手在唇邊撮成喇叭狀,扯起太監們特有的又尖又細的嗓門叫道:"聖上有旨,從現在起,各種人等不許叫喊……"這聲音雖欠渾厚,但穿透力極強。叫了兩遍之後,岸上頓時變得鴉雀無聲。鄂羅哩稟道:"萬歲,她們不再出聲了。"嘉慶點點頭,看了看四周,又道:"鄂公公,叫她們都走開,朕不想見到她們。""喳!"鄂羅哩應喏一樣,又扯開嗓門叫道:"大家聽著,聖上有旨,從現在起,你們統統回去……"很快,岸上的宮女們作鳥獸散,一個個全沒了蹤跡。鄂羅哩不失時機地媚道:"萬歲,現在真箇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了。"誰知嘉慶卻不冷不熱地回道:"鄂公公,這個,朕已經知道了。"慌得鄂羅哩連忙掌了自己一個嘴巴:"奴才多嘴!"接著便禁了聲。
雪花在倏忽之間變得大了,又平地捲起了一陣陣的風。風裹挾著片片鵝毛,扑打在那條栩栩如生的金龍身上,也扑打在直立著的嘉慶身上。船,似乎也在微微地顫動。鄂羅哩看著動也不動的嘉慶,幾欲勸說聖上回艙或泊岸,但沒敢開口。而嘉慶,在小船駛到湖心之後,卻命船工停槳。小船,就那麼孤零零地漂在湖中央,任風雪侵襲著,任波浪衝撞著。

嘉慶的內心也一如他腳下的小舟一般不平靜的。這一點,鄂羅哩也是十分清楚的。十四年前,乾隆將皇帝的寶座內禪給了嘉慶。但在以後的四年里,在朝中說話算數的,卻不是他嘉慶,甚至也不是乾隆,而是那個富可敵國的和紳。所以,乾隆駕崩之後,嘉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處置和坤。若按嘉慶的實際想法,恨不能將和坤千刀萬剮,但念及和坤是先皇的寵臣,乾隆對他恩愛有加,所以嘉慶也只好賜和坤一條白綾讓他自決了事。嗣後的十年,嘉慶雄心勃勃,欲從根本上整治好官吏們的貪污腐敗之風,使大清王朝在自己的手中重放光彩。有誰知,貪官污吏們越治越多,治來治去,矛頭卻漸漸指向了乾隆。嘉慶不能不感到自己有些束手無策了。就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又困擾於白蓮教反朝廷之亂。

如今雖說反叛之患已平,但教徒們喊出的"官逼民反"的口號卻讓他久久駕舟的是一個眉目清秀的小夥子,歲數雖不大,但馭船的技術卻十分嫻熟。風雪中,小舟在湖面上行駛如履平地。嘉慶一時來了興緻,便問他道:"告訴朕,你叫什麼名字?"小夥子叩首道:"回聖上的話,奴才叫王小二。"嘉慶讓他起來,對鄂羅哩道:"鄂公公,回去後賞王小二五十兩銀子。"鄂羅哩"喳"了一聲。王小二連忙跪倒,三呼"萬歲"。
遠遠地,在小船的正前方的湖岸上,不知何時,已簇擁了一大群人。他們都是朝中的文武大臣。許是來得久了,他們的頂戴花翎上已積了一層薄薄的雪,打船上望去,煞是好看。
嘉慶下了船,在群臣的簇擁下一步一步朝正大光明殿走去。來到殿前,他忽地住了腳,抬頭望著殿門上的"正大光明"四個字,有些怔怔地出神。這四個字金光閃閃,是先皇雍正所題。他又不禁想起先皇雍正帝在《圓明園記》一文中曾詮釋過的先皇康熙親賜的"圓明園"三個字的意義:
"圓明意志深遠,殊未易窺,嘗稽古籍之言,體認圓明之德。夫圓而入神,君子之明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
"唉……"想著想著,嘉慶不由得嘆了一口氣,"圓而入神,明而普照……說是一回事,可真正做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了。"
嘉慶帝坐定、群臣禮畢,鄂羅哩宣旨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值此聖上五旬萬壽之初,特頒詔覃恩,加封儀親王永璇子綿志、成親王孫奕倫為貝勒,加慶桂、董誥太子太師,戴衢亨太子少師,鄒炳泰、王懿修、明亮太子少保。欽此!"

綿志等人出列,望嘉慶跪拜,齊稱"謝主龍恩"。嘉慶微微一笑,言道:"諸位愛卿,有本儘管奏來,講。"
綿志復出列,道:"陛下,奴才有本請奏。"
嘉慶道「講」。
綿志道:"陛下,萬春園歷來為宮中重地,然而至今尚無宮門,奴才奏請聖上恩准,為萬春園建一宮門……"綿志說完便緊盯著嘉慶的眼睛。嘉慶沉吟片刻,輕輕言道:"萬春園實為宮中重地,至今尚無宮門也委實有失體統,雖因剿滅教匪,國庫吃緊,但該辦的事也是要去辦的。這樣吧,朕就命你全權負責建造萬春園大宮門一事。另外,朕近日發覺,敷春堂,清夏齋,還有澄心堂諸殿,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損,你就一併將它們修葺一下吧。"綿志拜退:"奴才遵旨。"
綿志方退,另一人從隊列中走出。此人便是朝中朝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兩江總督鐵保。關於他,數月之後,曾引發了一段讓嘉慶簡直傷透了腦筋的故事。而此刻,他雄赳赳氣昂昂地向嘉慶奏道:"陛下命奴才等修治南河,可目前進展實在困難,最大的原因便是經費短缺,故奴才等奏請聖上將兩淮、長蘆、山東、河東、兩浙、兩廣、福建、陝西、甘肅九處的鹽價,每斤酌加三厘,這樣一來,每年可得銀四百餘萬兩,而又與民生無損,於民工有益。奴才叩請聖上恩准。"嘉慶聞言皺了皺眉,然後淡淡地道:"整治南河的經費緊張,這個,朕已知道,不過你剛才提到的那九處,從整治南河中得到的利益,有大有小,若一概平均加價,於理未妥,朕的意思,此事還應從長計議。"鐵保諾諾而退。

一時間,諸大臣再也無人請奏。鄂羅哩道:"有事請奏,無事散朝。"有幾個大臣互相嘀咕幾句,已準備離開。嘉慶也挪動雙腿,擬轉入內宮。就在這當口,一人飛步而出,單腿點地,口呼"萬歲"道:"陛下,奴才有要事請奏。"
眾大臣忙立定步伐,定睛一看,原來此人便是殿前御史景德。此人在朝中可謂臭名昭著,專營逢迎拍馬投機取巧之能事。對他,嘉慶也是很有些看法的,但此時,卻也只能耐下性子重新坐穩道:"你有何事?"景德激動萬分慷慨激昂地道:"今年是聖上五十萬壽之年,聖上五十萬壽,是國之大事,國之要事,亦國之幸事也。聖上之美德,雖堯舜亦不啻也。萬壽在即,理應大加鋪張,藉此以示皇恩浩蕩、澤及山川也……"
嘉慶有點不耐煩了:"你,到底奏請何事?"景德拜道:"奴才乞請聖上,在五十萬壽之正日,允內城演戲十日,後每年壽誕,都應如此,以表國泰民安、歌舞昇平之意。"嘉慶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只低低地問道:"御史大人還有事請奏嗎?"景德也許是太激動了,沒能聽出聖上的弦外之音,只漲紅了臉道:"陛下,奴才的話講完了,乞請聖上恩准。"
嘉慶盯著景德看了好一會兒,那眼光,是很有些分量的。末了,嘉慶轉向眾大臣:"諸位大人,你們還有誰也同意這位御史大人的建議?"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嘉慶把"誰"和"也"兩個字的字音咬得很重。眾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點面面相覷的味道。實際上,內中很有些人也是抱有和景德一樣的看法的,因為,去年的聖上壽辰,便是在同樂園的清音閣上擺了十數天的大戲,能有這個機會討皇上歡心,何樂而不為呢?然而,躊躇了半天,眾人卻無一開口。箇中原因,一是有人看出了皇上今年的做法與往年有異,不願多事,以明哲保身為上,二是好多人平日不屑與景德為伍,不想跟著去附和他。而正是這兩個原因,使得許多人至少是暫時保住了自己腦袋上的頂戴花翎。

嘉慶站了起來,慢慢地卻又重重地走到景德的面前,很響地咳了一下道:"御史大人,你知道諸位大人為何沒有開口嗎?"景德誠惶誠恐地道:"奴才愚鈍,奴才不知。""哈哈哈……"嘉慶大笑起來,忽又斂容言道:"依朕看來,你這個御史大人也真的是太愚鈍了。"說完,負手重新走回寶座。直到此時,景德方才悟出,自己今日的馬屁可能拍錯了,而且這還不是一般的錯,是大錯特錯。嚇得他雙膝一軟,"撲通"著地,口中連稱自己"該死":"陛下,奴才對聖上可是一片忠心啊,奴才之赤膽忠心,天地可鑒……""住口!"嘉慶勃然大怒,"朕自登基以來,便崇尚節儉,嚴禁奢靡,而你,作為殿前御史,竟妄言惑朕洞開此例,你,該當何罪?"景德這下是真的害怕了,連連叩首道:"陛下,奴才可是為聖上著想的啊……"嘉慶面色嚴峻地道:"依你溺職之罪,朕本當嚴加懲處。念你確也不完全出自私心,理可稍加減免。來啊!摘去他的頂戴花翎,發往盛京充差。若不思悔過,依然若素,便永不許回朝。散朝!"

眾大臣有的高興,有的慶幸,還有的在提心弔膽。這樣的事,何時會落到自己的頭上?所謂伴君如伴虎,一言不慎,便累及自己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只看他們,一個個忙如漏網之魚,急若驚弓之鳥,轉瞬間,正大光明殿內便陷入空寂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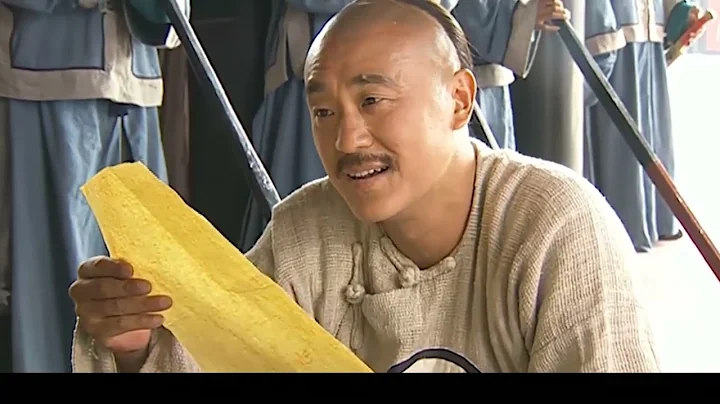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