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創 小王 MoneyKing
2022年馬上就結束了,今年基本跌了一整年,好在後面兩個月回了一些血。
不管是偉大的遠景敘事還是深刻的投資理念,都不足以撫平動輒20%以上的凈值回撤給投資者造成的傷痛。
有時候回顧歷史,回顧資本市場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事,看看大佬們在艱難時候的堅持也許能給自己充值一些信仰。
今天跟大家聊聊約翰聶夫,他是溫莎基金的管理人。
溫莎基金作為美國著名的共同基金,其性質就類似國內的公募,而約翰聶夫的操作經驗對我們研究公募基金有更強的借鑒意義。
約翰聶夫草根出身,最開始在克利夫蘭國家銀行做了8年證券分析師,研究汽車製造業、化工、金融等行業。
因為對汽車的深度研究和對寶麗來的成功發掘,逐漸成了研究組的頭頭,後來「為了追求更大挑戰」(賺更多錢)去了威靈頓基金公司,次年開始管理溫莎基金。
在約翰聶夫開始管理溫莎基金的投資組合之前,溫莎基金主要做「趨勢投資」。
巴菲特說投資像打球,而溫莎那時買的很多是前一陣子競相追逐到現在已經是垃圾的公司,約翰聶夫將這個比為「追趕打出去的球」。
通過對溫莎基金的拙劣表現進行詳細調查,他發現了這樣一個普遍事實:
溫莎基金買股票時支付了「過高的估值」,而約翰聶夫是低估值策略的實踐者。
一、約翰聶夫的低市盈率選股原則
低於平均值的40%-60%的低估值是約翰聶夫的基本準繩,但很多投資者目前對低估值有所誤解,認為那是撿垃圾的自我欺騙,是錯過偉大成長股的無力辯白。
「歌爾股份10倍估值,為什麼不買?」
其實低估值並不是簡單的為便宜而便宜,依然要結合公司的基本面,如果一個公司的基本面真的無可救藥或者有無法估計的利空可能,肯定也不願意買。
同時低估值要與高股息掛鉤,沒有好的分紅水平,低估值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為此約翰聶夫獨創了一個總回報率的概念,總回報率=(增長率+股息率)/市盈率,這個比率超過市場平均水平2倍的公司,就是約翰聶夫的首選。
低估值投資往往伴隨著人棄我取,而不管是業績、股價表現還是投資者情緒,周期股都屬於很難把握的一類。
不少投資者對周期股的態度往往是敬而遠之,但「買在無人問津時」符合約翰聶夫的投資理念,所以周期股通常占溫莎基金30%的倉位。
周期股的玩法與成長股完全不同,成長股是只要理論上盈利會繼續增長,估值就會繼續提高,但周期股的盈利高峰到來時,當一切指標顯示應該買入時,反而應該賣出。
二、對成長性的基本要求
約翰聶夫需要公司具備一定的成長性,對增長率的基本要求是不小於7%,但又未必是連續高於20%的明星高成長股,因為那種公司太貴。
一般,支撐股價上漲的動能是企業盈利的增長和人們對增長的預期水平。
格雷厄姆早在《聰明的投資者》中就指出,高成長股容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只要有一個季度的盈利預期有所滑落,或者高增長未達到預期水平,股價通常就會大跌。
所謂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即使高成長股業績符合預期,如果沒有大超預期,股價大漲的可能也不大。
低估值股票就不同了,它們幾乎不帶任何心理預期,業績不好人們也很少給予它們過重的懲罰,但前景一有改善的跡象,就可能激發投資人的人氣。
這大概就是躺平擺爛的教科書吧。
同樣,執著尋找十倍股對約翰聶夫也不適用,因為大多數知名成長股估值通常很高。
股價上漲不斷引來趨之若鶩的人群,進而推高其股價的上漲,如果支付過高的買入成本,意味著公司必須延續高成長,才能形成可觀的回報。
但這個過程總有極限,約翰聶夫不希望當它們的業績回歸正常,增長率回歸平庸時,再奪門而逃,更不想是最後的接盤俠。
所以等這些靚麗的成長股跌下神壇時,再去撿也不錯,但即使那時也要有所節制,嚴格控制買入比例。
三、該看的是價值
1999年納斯達克指數估值高達152倍,泡沫如火如荼。
已經退休的約翰聶夫在巴倫周刊圓桌論壇上篡改了1992年總統競選時克森頓的一句口號,直白地表達了他的看法:「笨蛋,該看的是價值!」提醒這是他見過最為高估的市場。
但市場並不會及時反映,直到大半年後,納斯達克才崩盤,但最多跌了有78%。
無數泡沫股永遠歸零,而即使真的是好公司,也將迎來10數年的漫長復甦之路。
「我認為成功並非來自個人的天分或什麼愚蠢的直覺,而是來自節儉的天性和懂得從各種教訓中學習。我歷久彌新的投資原則根植於此,而這個原則擁有無法磨滅的市盈率投資策略的優點。」
希望大家共勉,也希望2023年大家都有個好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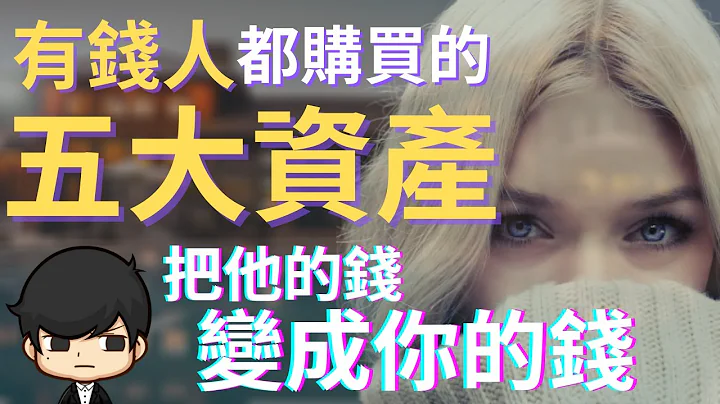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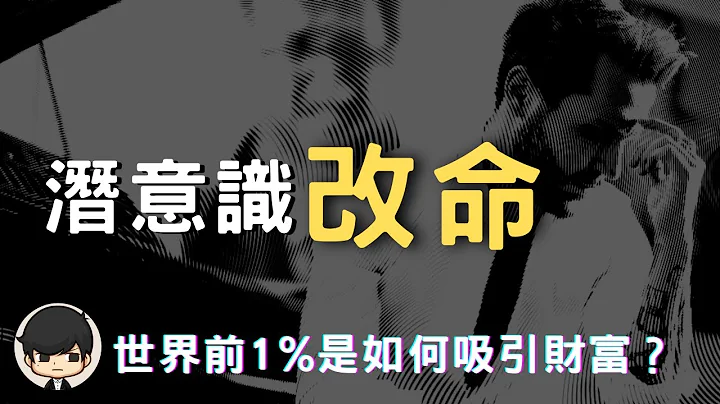
![G.E.M.【光年之外 LIGHT YEARS AWAY 】MV (電影《太空潛航者 Passengers》中文主題曲) [HD] 鄧紫棋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T4SimnaiktU/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DO5skNtCBBd8C64QjMGgw2N42b6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