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回忆我的老领导刘万寿老红军
讲述人:赵多鸿
记录整理人:张万忠
说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刘万寿的情况,我非常熟悉。她是我搭心眼里佩服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她曾任甘肃省古浪县裴家营公社石坡大队首任党支部书记,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她的大名常常出现在报刊杂志和其它传媒中,她的事迹和精神时时感动着的家乡人们,给家乡人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鼓舞和荣耀,是我们身边值得敬仰的模范人物,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们不但是墙连墙的邻舍,也是亲上加亲的亲戚,我的母亲与她是姑嫂关系,又是儿女亲家,我的二姐,是她的三儿媳。按照乡俗习惯,我叫她闫舅母(舅舅叫闫宗基),也尊称她闫奶奶。可外乡人,总称她为“刘老红军”“刘书记”或“刘奶奶”。
我是在她影响下长大的,也是在她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她见我人机灵,手脚勤快,有眼色,懂事儿,加之我母亲身体状况欠佳,家庭经济困难,推荐我到县政府当通讯员,她说:“到了公家地方,万万不能有贪心,办公室或者卧室里拾到钱,要分文不动,放到该放的地方;不要占公家便宜,不该拿的东西,坚决不要拿”。事情过去几十年了,通讯员虽没当成,但她的话我牢记了一辈子,也影响了我一辈子。
后来,她又推荐我到县水利局规划队工作。临行前,她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一定要争气,要珍惜机会,好好工作,希望我走出家门,到外面有更大更好的发展。在规划队三年里,我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学编制,搞规划,绘图纸,很快适应了本职工作,积极参与全县林带、渠道、道路、农田、村庄“五好规划”。正当满怀信心投身工作的时候,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夺了“当权派”的权,规划队受到冲击,逼迫自行解散,我从此失去了吃公家饭的机会。

十年前,我曾主持古浪县海子滩镇新市场楼房基建工作,有人诬告我贪污修建款,古浪县纪检委和武威市巡视组,先后派人来调查核实,我指着满墙的奖状和荣誉证书说:“这就是我,你们怎么查都行,查出什么问题我承担什么责任”。墙上有我参加甘肃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与省领导合影留念的照片,有“武威专区农业综合试验先进工作者”荣誉奖状;有参加古浪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有许多大队、乡“(公社)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经过深入调查、询问、对账、走访了解,最后水落石出,还我清白。纪检委的同志对我竖起大拇指,说我了不起!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
我感激闫奶奶,是她教会我如何做人,给我打好了人生底色基础,扣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我敬佩她、学习她,使我永远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
在刘万寿老人担任石坡大队书记的几十年里,我先后当过生产队长、副大队长、民办老师、赤脚医生、民兵连长。我对她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十分清楚,也非常敬佩。
她目不识丁,但讲话不管多大的场合,从来都是镇定自如,条理清楚,头头是道,比识字的人,听起来有条理,有趣味,更接地气,因此更有号召力。公社开会学习文件传达指示,她听一遍就能牢记,并向社员群众原原本本传达。她召集群众大会,或作“忆苦思甜”报告,一口气能讲几个钟头,口不干,舌不燥,让人受用。她工作起来不怕苦不怕累,比如:早上从石坡梁出发,翻过九沟十八坡的新泉沟,腊盘沟,到几十里外的老城大队、大岭大队办事,再返回所属的马家梁、西水沟、新井生产队检查工作,下午赶到裴家营公社开会,尔后连夜赶回家,还要坐在煤油灯下,为儿女们缝补衣服,料理家务。一天行程几十公里路,她脚下走路的功夫,是从长征路上练出来的,十里八乡人人皆知。
她的记忆力特别强,且能达到惊人的程度。全大队有多少人,男的多少,女的多少;耕地多少,牲畜多少,她都清清楚楚;具体到各队人口,男女人数,羊有多少,牛多少,骡马驴多少,队长说不上的,她能说上;有时听汇报,队长会计拿着本本说错的地方,她能当场指出来。各队的财产收入多少,她更是一清二楚。
公社干部下乡不愿意来石坡大队,因为石坡大队地方大,居住分散,石坡、沟口、太阳沟一带,山大沟深,道路难走。南到昌灵山,北到海子滩,南北的距离几十华里,而且要翻山越岭,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要靠步行,用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每家每户。下乡工作很辛苦,下乡等于“下苦”。
夏秋季节,干部们更怕的是跟刘书记下乡估产。“估产”就是根据当年庄稼长势情况,提前对粮食作物产量进行估算,目的是向上汇报粮食产量,向下确定社员口粮分配,做到心中有数。庄稼生长的时候,夏天估一次,秋天估一次,庄稼收割上场后,根据落垛的大小,再估一次。一年之内要估产多次,每次都要到实地查看,深入调查研究是她一贯的工作作风与习惯。像太阳沟队的树湾子、刘家豁岘、申家湾、中川岘子;沟口队的破山头、南泥沟、曹儿水、沙岘子等地段,大多位于昌灵山山头,山路崎岖,山高坡陡,男同志们都望而生畏,可刘书记总是拿出红军的长征精神身体力行,带头攀登,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跃过一个深沟又一个深沟,仔细查看每个地块的庄稼长势,产量多少。累了,就在山坡上休息一会儿,渴了,喝一口山泉水。太阳晒红了她的脸庞,汗水淋湿了她的头发,她不叫一声苦,不说一声累。
估产一两个生产队的情况如此辛苦,全大队有六个生产队,要跑遍无计其数的田间地头,不知要走多少路程,花费多少时间,她从来都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年轻干部做出榜样。
她这样做,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社员群众负责。一般人这样说话,意味着得罪领导,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往往显得底气十足理直气壮。在生活困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她深深知道,群众的温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她肩上最大的责任。
让刘书记威名远扬的是她组织带领社员群众兴修水利和铺压砂田。修水解决了吃水困难,压砂造田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这两件大事办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其影响之大,意义深广,改写了石坡几十年无水可吃的历史,也谱写了石坡人民改天换地解决温饱的新篇章,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勇敢担当,老红军战士的远见卓识,为民谋福址的情怀。
今天,我们不想说石坡兴修水利的事,因为知道石坡修水的人比较多,宣传报道也很多。现在,我们只说石坡大队铺压砂田提高产量的事,因为时间久远了,有些事情知道的人屈指可数。
铺压砂田,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家乡人在“十年九旱”的严酷生存条件下,为改变干旱面貌,提高生活水平,与自己穷苦命运奋力抗争的一场伟大壮举。
石坡大队位于昌灵山脚下,七沟八梁,沟壑交叉。砂沟多,砂石多,贫薄土地多,天气十年九旱,土地广种薄收。铺砂压田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她想,不能守着黄土受贫穷,要想方设法改变社员群众的贫困面貌。也许是她用心思考,也许是她集思广益,也许是她见多识广。她曾上永登开会,路过新堡一带,看到当地砂地庄稼长得特别好,受到启发。于是,一个大胆想法在她心中产生,通过铺压砂田,提高粮食产量,改变贫困状态。在她的号召下,干部社员统一了思想认识,立即行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铺压砂田的“造田运动”。
当时,压砂的主要方式是人背、驴驮、架子车拉。
人背时,就是一人背一个芨芨背斗,背砂时把背斗放在挖好的砂台上,装好砂,倒砂时一手抓住背斗底,一手抓住背斗绳,肩膀一斜,斗口朝下,把砂倒掉。在机械设备极缺的年代里,背斗背砂出入砂坑方便,大小砂坑都适宜,更适合单独劳动,因地制宜发挥了良好作用。
驴驮时,是在驴背上备好鞍子,鞍子两边搭两个漏斗形担筐,口面大,底面小,底部做成活的,拴上开合的扣子,装砂时合上,倒沙时取开。用畜力代替人力,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当年,人们形象地把牲畜当作人们的“翅膀”,它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把它当作家庭的成员,当作自己的“亲人”。回到家,人不吃不喝可以,首先得把牲口喂上。因为在干旱的土地上,牲畜成为人们的“翅膀”和好助手,也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架子车拉砂,一般适用于地势平坦距离远的地方。两人一组,在架子车轴上拴一根套绳,一个人连背带拉,一个人连推带搡。较之人背畜驮,架子车拉得多,跑得快,能大大加快压砂速度,提高压砂效率。一个生产队如果拥有几辆架子车,那真能算得上先进的工具,如虎添翼。而家庭有架子车的更是凤毛麟角。当时,有一辆架子车,相当于现在家庭的小骄车。
背砂特别辛苦,也特别费衣服。当时计划经济年代,布料紧张,凭票供应,为了减少衣服磨损,生产队派专人到宁夏中卫购买背砂的马夹,大小形状颜色相当于现在志愿者穿的红马夹,它结实厚沉,久经耐用,是背砂的极好工具,在背砂的战场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压砂过程中,干部群众自发创造了“包干到户”“定量计酬”的办法。我觉得,这是后来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是她在那个年代的一次成功运用,它极大地激发了劳动热情,调动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为了多压砂,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大小都背砂,力所能及,能背一斗地背一斗,能背五升的背五升。背砂数量按衡量粮食标准的“斗”和“升”来算,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dan)。)一石是五分工,两石是十分工。背砂的时候,要把砂石倒成大小均匀的砂堆,这样便于估算验收。为了多背砂,多挣工分,人们自发地开展劳动竞赛。头天傍晚刨好砂,第二天五更时候就背砂,背砂不亚于山上背煤的活,踏黑夜,顶星天,起五更,睡半夜。背砂背的肩膀红肿、手心磨得脱皮。汗水抖落了星辰,脚步惊醒了黎明。满地的砂堆就像劳动的音符,背砂的小路就像生活的源流,初升的太阳就像心中的希望……



刘万寿出席县人代会、党代会与参会代表合影
各生产队涌现出一批批背砂的“拼命三郎”:像西水沟队的:杨玉堂、桑长生、刘生红;马家梁队的:王曰禄,张明智、马玉普;沟口队的:赵有前、张兆仁、马成彪;石坡队的:李能弟、郑希禹、方万功;太阳沟的:王保国、李全基、赵同文;新井队的:刘禄德、党兆得、石生彦……等,他们是背砂战线上的肯干分子,也是勤劳刻苦的突出代表,更是献身集体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
太阳沟、沟口两个队在远离村庄十多里地的五个墩子压砂,吃住在地窝铺里,冬天没有新鲜疏菜吃,只有黄米稠饭加酸菜,住宿环境艰陋,生活条件艰苦,一干就是几个月……
为了压砂,有人险些付出生命代价:西水沟队社员王忠信挖砂时,丈几高的砂崖突然塌落,窜起冲天尘雾,人们听到“轰隆”声响,一起扑向出事地点,只见整个身子全被压在沙堆下面,只有头部露在外面,由于抢救及时幸免于难,造成大腿骨折,留下了终身残疾。
在压砂的日日夜夜里,刘书记食不甘味,夜不成眠,惦记着全大队的压砂进度,牵挂着各队的压砂安全,天不亮就出门,脚不停点地奔波在各个压砂工地上,察看砂层的薄厚,验收砂石的大小。她公而忘私的精神,一心为民的情怀,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刻在人们的口碑里!
在她的带领下,发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艰苦创业精神,每年利用冬春两季农闲时间,干群同心,愚公移山,坚持不懈,压砂不止,一块块青砂地不断延伸,一片片稳产田不断出现。经过几年的连续奋战,石坡大队压砂面积达到2000亩左右,每亩产量原来300斤提高到500斤。这些骄人的成绩,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并给予奖励,将若干辆架子车底盘奖给石坡大队。《甘肃日报》报道了刘书记铺压砂田的先进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干部群众的士气和信心。
春华秋实,寒来暑往。辛勤的劳动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从此,青砂地,旱麦子,成了石坡人的骄傲。“秃头麦子”这个代表家乡地理标志的农特产品,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以极具抗旱的品质,靠天生长,靠青砂独特的保护和充足的阳光成长,不施任何农药和化肥,成为家乡闻名远近的无公害绿色产品。行面拉条,寸寸面条,旱地馍馍,旱地面粉,成为家乡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美食品牌。
自从有了砂地,石坡人民结束了无瓜菜的历史。蓝天下,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成为久旱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花皮的西瓜,麻皮的甜瓜,绿皮的香瓜,黑皮的葫芦(冬瓜),红色的辣椒,紫色的茄子……每当收获的季节,堆得像小山似的,遍布在石坡的芨芨梁上,遍布在新井的五个墩子,遍布在西水沟的林家砂河,遍布在马家梁的刘家坝里……阳光照射下,发出诱人的亮光。
说到石坡砂地的西瓜,我不得不说一段真实而耐人寻味的历史佳话:
据说“文化大革命”中,县委书记朱炳麟用架子车拉着铺盖卷到全县各地轮流接受批斗,路过石坡大队太阳沟生产及五个墩子西瓜地时,高温酷暑,干渴难忍,看瓜老农拿出甘甜的砂地西瓜“款待”当权派,使受批斗干部深受感动,牢记于心。七十年代,打井抗旱,机井配套指标异常紧张,大队干部前去申请,听说来人是石坡大队的,平反昭雪的朱书记感念石坡人民的厚道善良,一次性批给石坡大队机井配套设备六套(六个队),为打井抗旱,平田整地,尽快改变贫困面貌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石坡人民欢欣鼓舞,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和憧憬……
在干旱山区的几十年时间里,青砂地,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贡献了一年又一年公购粮,为人民群众解决温饱发挥了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对它怀着深深的眷恋。刘万寿书记是铺砂压田的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参与者、实践者,我们对老红军战士刘万寿书记怀着深深的敬意。她是永远活在石坡大队人民心中的共产党员。昌灵山青松向她鞠躬,南泥沟绿水向她致谢!今天的美好生活如她初心所愿,今天的盛世华夏如她理想所盼。但愿刘万寿老人家在天堂能够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含笑九泉永远为之欣慰。
回望历史的天空,有的景象已经模糊,有些却历历在目。青砂地,旱麦子,这个曾经温饱了石坡人民的历史名词,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它。它凝聚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凝聚着一位老红军战士的高尚情怀;它曾像一束明亮的灯光,点燃人们生活的希望,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它更像一缕飘香的瓜果,带给人们一种久久回味,源远流长,弥醇弥香……老红军刘万寿书记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讲述人:赵多鸿,男,初中文化,现年73岁,共产党员,甘肃省劳动模范,古浪县人大代表。现为古浪县海子滩镇马场滩村十组村民。历任生产队长、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石坡大队副书记、副大队长、民兵连长,公社民兵营副营长。

记录整理人:张万忠,男,甘肃古浪县直滩镇石坡村西水沟组人,退休教师,喜欢文学,热爱写作,偶尔有作品发表互联网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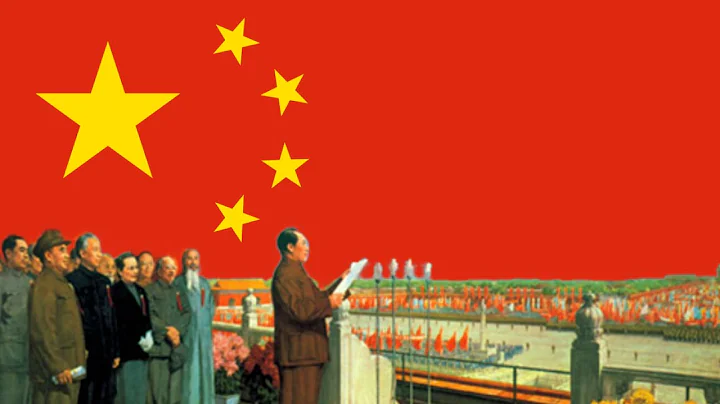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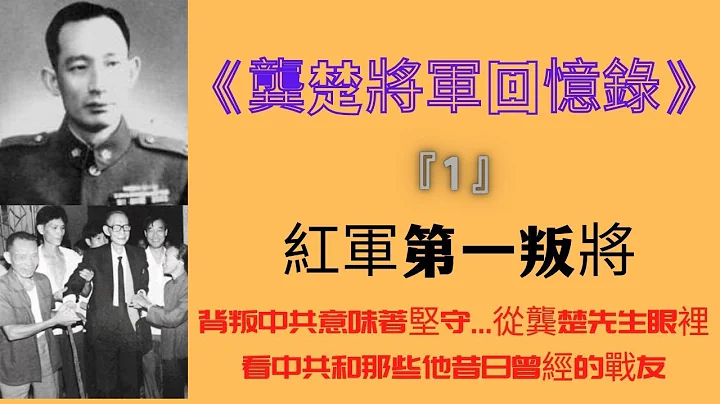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结】《我的女将军大人》女将军穿越意外嫁总裁,被心机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来了?总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宠#霸道总裁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