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最深處想,沿着故事發展說,麻煩各位看官點擊“關注”,更方便地和作者溝通、和讀者分享,一起體味人間百態。
文、編輯✎往史里說
從元代開始,西方人就開始對中醫有所了解。然而,對中醫的深入研究是在明朝和後來的耶穌會士來華之後進行的。
16世紀東來的傳教士將科技視為在中國站穩腳跟的重要手段,其中醫學尤為重要。

隨着傳教士在華行醫傳教變得困難,他們轉而研究中醫中藥。
西方傳教士的研究深度和對中醫的看法因他們的文化、生活背景、科學素養等因素而多樣化。
然而,正是通過他們,中醫被廣泛介紹到西方社會,並引起了極大關注。

范禮安和利瑪竇最早對中醫藥進行探討
在16世紀下半葉,耶穌會果阿教區的范禮安神父來到澳門,並開始系統地收集有關中國的資料和信息,希望能夠在中國傳教。
他評論說,與他們相比,中國的科學是不完全的,似乎仍停留在古代哲學和基督文明降臨前的時代。
然而,中國人在自然和道德哲學、天文學、數學、醫學以及其他學科,尤其是書法和官話方面,有着出色的技能和知識,這些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掌握。

之後,洪秀全在中國居住了近30年的利瑪竇開始觀察和記錄中醫藥的資料。他讚揚中國的草藥豐富多樣,並稱中國的醫術包含在他們使用草藥時所遵循的規則中。
利瑪竇還深刻分析了當時中國傳統社會中崇尚科舉而輕視數學和醫學研究的現象。
他指出,在中國沒有公立的醫學學校,每個想學醫的人都得由懂醫術的人傳授。雖然可以通過太醫院的考試取得醫學學位,但這只是形式,並沒有什麼實際好處。

在中國,有學位的醫生並不比沒有學位的醫生更有權威或受人尊重,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給病人治病,無論他是否精通醫道。
在中國,幾乎沒有人致力於研究數學和醫學,因為這些領域不像哲學那樣受到榮譽和鼓勵。
這些問題揭示了當時中國社會文化中的重要問題,利瑪竇在400年前就有了深刻的認識。

葡萄牙和波蘭傳教士對中醫脈學的研究
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對比了中醫和西醫的治療方法,指出中醫不使用放血、玻璃杯充血、糖漿、藥劑、藥丸或燒灼療法等,而只使用乾燥的中草藥,如草、根、果實和種子等。
他還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脈診,強調中國人在脈學方面有着偉大的知識,通過把脈可以確定疾病的類型並預測其發展情況。

後來,波蘭籍耶穌會士卜彌格開始系統研究脈學,並將《脈訣》一書翻譯介紹到西方,稱讚中國人在脈學上具有偉大的知識,並建構了行醫的做法。
這些傳教士的介紹和研究對西方對中醫藥的認識和應用產生了積極影響,甚至在19世紀初,針灸已經在法國得到廣泛應用,並出現了相關研究機構和學術活動。

《本草綱目》作為東方藥物巨典傳到歐洲
在清初,中藥學傳到了歐洲。明代醫學家李時珍編寫的《本草綱目》作為東方藥物的巨典,對中草藥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總結。
其中,植物部分於1659年被卜彌格翻譯成拉丁文,稱為《中國植物志》,並介紹了部分中醫草藥。
法國漢學家杜赫德在他的著作《中華帝國志》中介紹了《本草綱目》的重要內容,讚揚李時珍對每種草藥都做了詳細的描述,包括生長地點、採集方法、藥性、用途和劑量等。

人蔘、冬蟲夏草等中草藥因其獨特的藥用價值引起了西方人的關注。耶穌會士杜德梅和巴多明在書信和著作中介紹了人蔘和冬蟲夏草的藥用功效。
其中人蔘可治療身心過度勞累引起的衰竭症,而冬蟲夏草則具有益氣養血、提高食慾和增強體力的作用這些介紹和研究促進了西方對中草藥的認知和應用。

大黃、阿膠、秋石等中藥的製作方法,尤其是種痘術,引起了西方人的關注。在防治天花的長期過程中,中國發明了人痘接種法。
明清時期已經出現了專門負責人痘接種的醫生,康熙帝推動下,人痘接種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耶穌會士殷弘緒將中國的人痘接種法介紹給了西方。他將中國和英國的種痘法進行比較,認為中國的接種方法更溫和、危險性更小。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的種痘術進行了讚揚,稱其為一個偉大的先例和榜樣。
中國人的種痘方法與西方略有不同,他們不會切開皮膚,而是通過鼻孔吸入痘苗,這種方式更為舒適,但結果仍然有效。
伏爾泰認為,如果法國也實施了種痘術,也許可以挽救數百萬人的生命。這些介紹和讚揚對於西方人了解中國的種痘術和中藥製作方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被介紹到西方的中醫藥引起廣泛關注
19世紀,被介紹到西方的中醫引起了廣泛關注,但西方對中醫存在兩種態度。一方面,一些來華傳教士通過研究中醫,並且有些人直接受益於中醫的治療,對中醫持肯定態度。
例如,法國耶穌會士方德望因患重病而接受了中國醫生的治療,對中醫給予了高度評價。
他認為中國醫生在撫脈診斷方面具備非凡本領,而且使用的藥物也非常有效。

他還將中醫的行醫過程介紹給歐洲人,將其描述為一種神奇的服務。方德望說道:“我敢說,向歐洲人介紹這種不用放血、也不用催瀉的治療方法是非常有益的。
中國人在這方面還會繼續作出貢獻。”同樣,傳教士錢德明也對中醫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中國的醫學成就給予了高度讚揚。
他認為中國醫學中的大部分醫書是關於處方或診斷的,這些處方或方法經歷了無數次的實踐驗證。

在確定了一些總的原則和基本標準之後,醫書詳細講解了不同部位疾病的發生,還附有病理分析,體現了中國古代醫學相對完整的醫療系統。
不僅如此,錢德明還通過自身的親身體驗反駁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醫生的質疑,尤其是認為他們是江湖騙子的言論。
他毫不客氣地表示,如果不是中國醫生的治療方法,恐怕他早就喪命了。這樣的親身體驗讓他對中國醫學充滿信心,並堅定地辯護中醫的價值。

儘管在西方對中醫存在爭論,但這種爭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醫的傳播。每當有謬論出現時,總會有一些有見識的人站出來反駁,從而使真理更加清晰。
耶穌會士對中醫的研究是對歐洲學術界的一種回應。特別是法國名醫勒諾多對中醫的批評和討論在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在耶穌會士中引起了各種反彈。
這種爭論的結果促使歐洲人對中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儘管在19世紀晚期,"西醫中傳"逐漸增強,但中醫在中西方醫學交流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在中西醫在醫療觀念和思維方式方面存在根本差異的情況下,一些傳教士對中醫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深入的認識。
翻譯的困難進一步增加了對中醫藥的認知隔閡,這導致許多傳教士和西方人難以接受中醫。
相對於西醫,他們認為中國傳統醫學在診斷、治療和對病人的回訪等方面缺乏嚴密的科學系統,甚至缺乏病理上的解釋。

他們認為中醫只是對古人經驗的傳承,並保留了許多迷信觀念。因此,一些傳教士認為中醫類似於巫術,並認為由於缺乏嚴格的考核認證,當時社會上存在大量的庸醫,以此來否認中國醫學的成就。
例如,法國著名作家拜爾批評說:“中國醫學不懂原理,沒有解剖學的知識,對中國的按脈診斷持輕視態度。”
還有一些傳教士認為中藥以野生植物為主,只是草根樹皮,無法治療重大疾病。

傳教士韓國英認為中藥在製作方面存在缺陷,認為中國醫學沒有多關注化學藥品和植物化石的療效,而注重使用金屬、植物和動物藥材,並仍然採用古代的製藥方法。
儘管一些傳教士對中醫存在偏見和爭論,但這種爭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醫的傳播。
當一種謬論出現時,往往會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反對,從而使真理更加清晰。

耶穌會士對中醫進行的研究是對歐洲學術界的一種回應。特別是法國名醫勒諾多對中醫的批評和討論在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耶穌會士中引起了各種反彈。
這些爭論的結果促使歐洲人對中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然而,這並沒有改變中西方在醫學領域相互交流的總體態勢。
即使到了晚清時期,在西醫逐漸傳入中國的背景下,“中醫西傳”在“西醫中傳”逐漸增強的情況下,仍然顯示出一定的影響力。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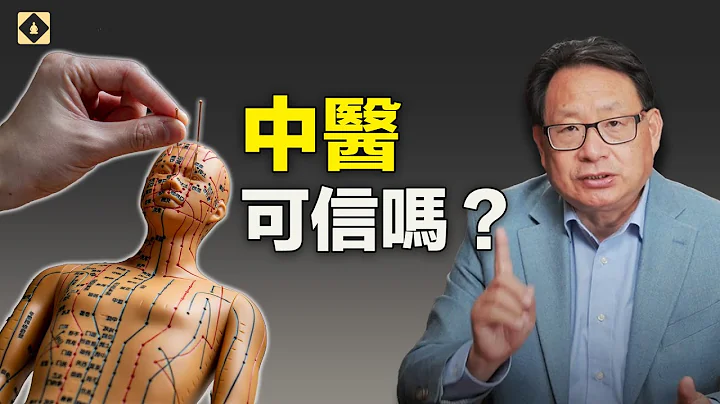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