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時代,因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因此,在中央集權越是集中的明清兩代,愚民就越成功。或者說,愚民政策,也只可能在相對封閉的時空中得以實現。
封閉,意味着圈養,意味着各種社會要素供給的內生性,因此,一旦確立了某種規則,就會因為供給的單一性,而形成極強的慣性。
清朝之所以繼續採用明一代的制度,其中,也是看到了這種制度對於統治的便利之處。
張居正的死後被清算,深入進去看,實際上也是這種“慣性”使然。
其一、張居正的革新圖強,打破了文官集團的內部平衡,既有利益的,更有話語權的。
其二、張居正的強勢,最終也打破了臣權與皇權的平衡。
而儒家道德,卻是以維繫社會平衡為主旨的。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謹和雷同被推崇,而一切突出的,就會被指斥為離經叛道,是異類。因為,一旦打破了平衡,就意味着利益被重新瓜分,話語權的制高點被更改。
這一切,在對張居正死後的清算運動中,全部赤裸裸的顯現。

01
以道德為實際的法律裁判依據,就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可能有多重的解釋空間。
明朝,始終以朱注“四書”規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依據,因此,許多的是非黑白,就都變得模糊不清,甚至可以顛倒是非。
這種缺乏法律手段的社會治理模式,使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缺乏了一種可以用作合理裁決的地帶。這也使得事實真相併沒有那麼重要,而人的道德品質有沒有瑕疵,卻成為了最重要的判斷依據。
而道德品質,實際上是最難判斷的。因此,才有了文官集團的陰與陽的集體特徵。就像李贄感慨說:“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另一方面,這種以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的治理模式,一旦知識分子出現放棄或者反抗儒家觀念的情況,那麼,王朝的安全就出現了問題。因為,自詡儒家正統的“四書”是維繫政府和文官集團緊密合作的唯一紐帶。
也正是這種因缺乏明確界限而約束力薄弱的道德依據,使得文官集團幾乎是集體走向了虛偽,也就是道貌岸然。這種治理模式,一定會形成無數的治理缺陷,以及可以在道德遮掩下形成的私慾的放縱。
這種社會治理模式,反應到對個人的定罪方面,就可以形成“莫須有”式的理直氣壯。
而張居正就正好陷進了這種道德判決之中。

02
張居正的權勢,幾乎可以與攝政王相匹敵。
歷朝歷代,要想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進行資源重新分配的革新,就必須獲得皇帝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必須強悍,不容置疑。
張居正比王安石幸運的是,支持他變革的皇帝是他從嬰孩時期就開始教導的萬曆皇帝。並且,直至張居正去世,萬曆皇帝都還只有18歲。再加上太后對張居正的信任,以及太監總管馮保的聯盟,也就是說,張居正實際上與這三個權力核心人物是一體的。而他是唯一可以出面鎮住場面的。
當然,也正是這種無以復加的權力,讓他打破了文官集團的平衡。他的革新,光全國土地丈量一件,就觸及了包括徐階在內的絕大部分權貴的利益。關於當時權貴對重新丈量土地的抵抗,有部劇《顯微鏡下的大明》,可見一斑。
這種平衡的打破,實際上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於是,倒張派就迅速潛伏下來了。
之所以是說潛伏,是因為只要張居正活着,只要沒有辦法動搖皇帝的支持,那麼,倒張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對張居正死後的清算,實際上的確鑿的違法亂紀的證據幾乎是沒有的,比如生活奢侈,那徐階奢侈多了,比如蓄養美女,比如任用私人,結黨營私等等,這些在基本的官員而言,其實都是常態。萬曆皇帝也並沒有多大的意外。
但是有一條,即謀反篡位,即與戚繼光的聯盟。戚繼光的軍政革新,而後有戚家軍,實際上是在張居正和譚綸等的先後支持下發展起來的。戚繼光的突出成就,當然也難免招致文官集團的嫉妒和忌諱。
那麼,文官之首的張居正和武將之首的戚繼光過從甚密,當然擁有了謀反的能力。
於是,張居正沒有謀反,但卻有謀反的能力,這一條便徹底讓萬曆皇帝推到了張居正。
這一條,其本質是臣子的威勢過大,就會威脅到君主的地位,那麼,儒家的君君臣臣的秩序就受到了威脅。於是,以此意識形態為統治手段的王朝,是堅決不會給這種破壞維繫社會平衡的異類存在的。哪怕他已經死了。

03
而這種清算的結果就是,另一班來督促皇帝要怎麼做皇帝的文官集團上來了。萬曆皇帝似乎也才明白,他們對張居正的義正言辭,不過是為了他們能夠取代張居正。
於是,後來的首輔申時行,借鑒了張居正的慘敗,於是充分做起了和事佬,以顧全大體的方式,保全政治的平衡。用儒家的道德規範,來平衡皇權與臣權,來平衡文官集團內部的利益。
這種平衡裡面,是沒有太多是非黑白的,有的只是一種表面的穩定和相安無事。
內里,仍然是官僚集團的“陽道德,陰富貴”,然後,大家誰也不戳穿,一起等待努爾哈赤的鐵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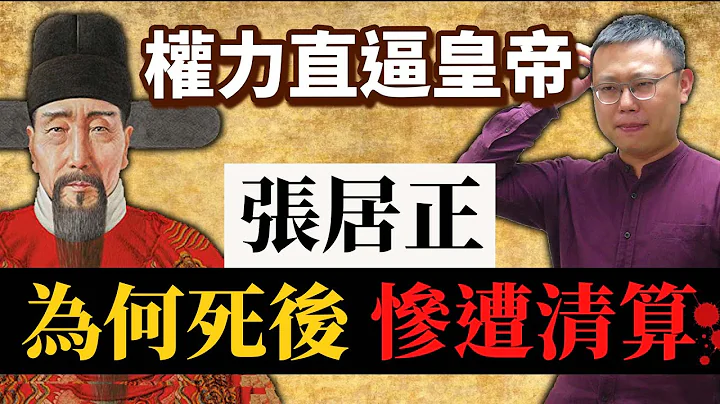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