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意思是人体好比小宇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整体通畅时,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一旦有痛的感觉,那就表示有些不通畅的部位需要调整。
人的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不通,可能会抑郁苦恼,人生灰暗无光。通了,就会豁然开朗,人生色彩斑斓。
那么,如何才能通呢?
01
必须依理而变才能求通
《易传》认为宇宙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迁流当中,正如《论语 · 子罕篇》所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的大历程,和孔子当时所看到的河流一般。
《系辞上传》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有象有形,大家张开开眼睛便能看见。
《系辞下传》又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宇宙唯有变化,才能够不穷而久。
因为变可以不穷而通,而通即能久而不停息。变化是宇宙的根本事实,只要万物生生不已,变化就能永不止息。
然而变是变,化是化,彼此并不相同。
“化”是变的过程,而“变”是化的结果。一切时时都在化,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能看出变的成果。
易学更进一步指出,变化是有条理的,变化必须依据不易的常则,才不致乱变而造成不通的恶果。
《系辞上传》云:“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一切动静都有不变的常则,也就是有常道可以依循。
刚柔的符号一旦定下来,便可以分辨清楚是不是符合常则。又云:“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天下事物变动不已,却不能乱七八糟而不合条理,因此,《系辞下传》直接指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这个“一”,便是永恒不易的常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生”——不是生命,而是创造。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一切都是电磁波的变形,宇宙的电磁波一直存在着光速的现象,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把原有的光速现象加以改变形态而已。
不论如何,有原则地应变才能通;缺乏原则或者违反常则的变,徒然制造一些紊乱的恶果,那就是不通。
02
持经达变才能真正变通
不易的常则,称为“经”;变易的因应方式,则为“权”。
“经”是不能变易的基本原则,应用的时候,必须因应当时的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做出因人、因事、因时、因地的合理应变。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权宜应变,也称为权宜措施。
“持经”的意思,是坚持既定的原则,维持一贯的理念,确立永远的目标。
“达变”的用意,应该是为了达成“持经”所做出的某些调整或改变。
所有的权宜应变,都应该有利于既定原则的实现,换句话说,一切的权宜措施,都不应该违反或偏离既定的原则。
长久以来,中华文化历经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内部不同意见的挑战,都能够顺利地加以整合。
便是古圣先贤立经,后代子孙持经,大家再怎样求新求变,都不敢离经叛道或做出离谱的改变所产生的功效。
中华文化得以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主要的原因,便是中华民族具有持经达变的素养和能力。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以来,我们这种能力正在快速地丧失中。面对外来文化,我们既不能持经,也不能做出合理的权宜应变。
最初学日本,然后学欧美,接着想学苏俄……不但不能持经,而且不知如何应变。
殊不知易学启示我们:唯有持经达变,才能真正变通;想要变而能通,非持经达变不可。
幸好历经动乱,我们已经迷途知返,思前想后,决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易学在二十一世纪必将发扬光大,和这种反思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如何持经达变,是学习易理的必修课题。及早把“经”找回来,才能做到真正的通达。
03
推己及人才能人我互通
就人与人的相通而言,我们把“知相通”称为“理解”;将“情相通”叫做“同情”;而以“意相通”当成“同感”。
无论理解、同情或同感,实际上都不是“实验”或“经验”所能够达成的,而是必须用心“体验”,才能获得真正的效果。
求学过程中,我们大多做过科学实验,却由于科学缺乏感觉,因此很难有所体验。
实际生活中,我们也都具有相当的经验,但若只有经历而缺乏磨炼,同样也不可能有什么体验。
体验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结果,目的在求人我相通。
《论语 · 先进篇》记载:有一天,子路、曾点(曾参的父亲)、冉有、公西华这几位弟子,陪孔子坐着。
孔子说:“你们可能因为我稍微年长,而不方便说出心中的话,现在不妨随兴些,谈谈自己的志愿吧!”
于是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侃侃而谈,各自说出自己的心愿。此三人皆胸怀大志,希望能做出一番大事。
唯有曾点在孔子的催促下,最后才说:
“我没有同学们那样有作为,只想在晚春时节,穿着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青年,六、七个少年,渡过沂水,在空旷的地方放声高歌,一路吟咏而返!”
孔子十分欣赏曾点的想法,毫不保留地说出:“吾与点也!”因为曾点所呈现的,是一种仁乐合一的圆融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充实之美。
人人倘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大家欢畅悦乐,应当是己安、人也安的人生艺术。
这种人我相通的境界,不必为了生活或居于理想的追求而紧张忙碌,才是“看似彼此不关心,实则人人都满足”的难得通达与真正安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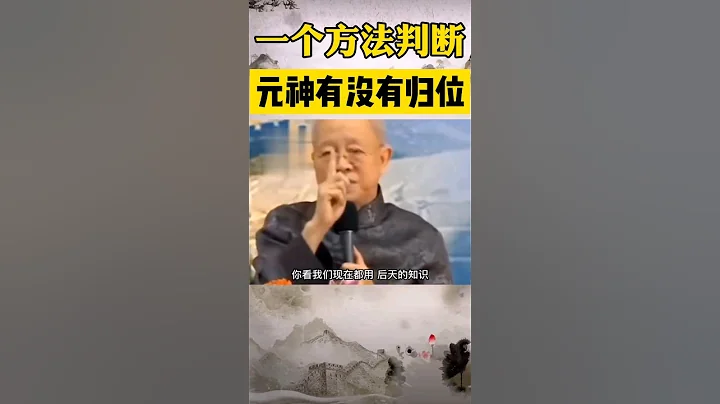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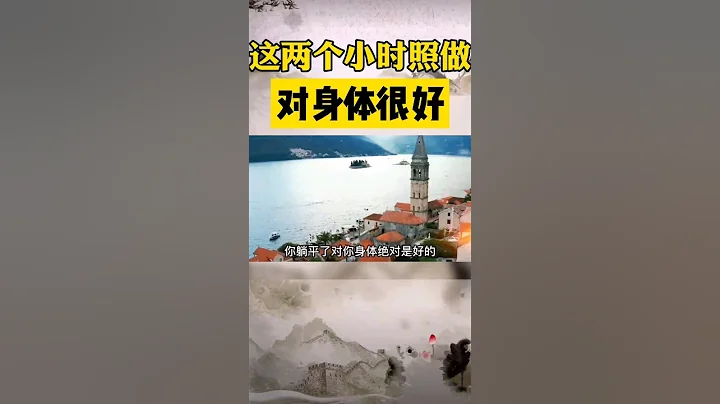




![[Chinese movie 2023]Poor girl helps disabled shareholder, changes fate!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2qSlT5aVHg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zmX0URNZaXthUulfqkBykMpzB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