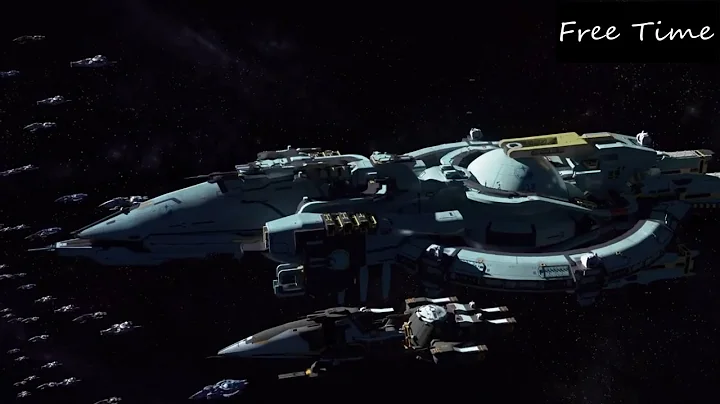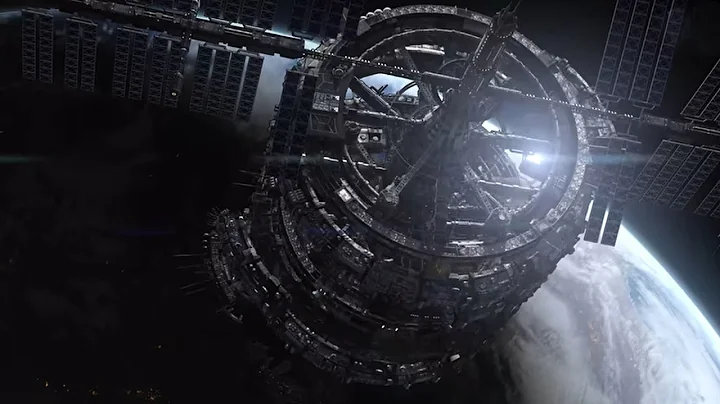不可一世的水滴

水滴學名「強互作用力宇宙探測器」,在《三體》中,它是一個無堅不摧的存在。末日之戰時,它用最原始的撞擊方式,在三十分鐘內摧毀了太陽系艦隊幾乎全部戰艦。
為了讓讀者理解水滴到底有多硬,大劉寫道:「水滴不像眼淚那樣脆弱,相反,它的強度比太陽系中最堅固的物質還要高百倍。這個世界中的所有物質在它面前都像紙片般脆弱,它可以像子彈穿透乳酪一樣穿過地球,表面不受絲毫損傷。」
除了堅硬,水滴還有一個特點——它的表面溫度是絕對零度。這說明組成它的分子沒有振動,它們牢牢地相互固結在一起,像被釘子釘死了一般。
能讓分子這麼聽話的力,只有強互作用力。
強互作用力是短程力,它本來只作用於核子之間。要想造出水滴,必須增加強力的力程,讓它能像電磁力一樣,作用在原子尺度上。
三體人是這樣做的——「他們在水滴的內部製造了一種力場,這種力場能夠抵消原子間的電磁力,使強互作用力溢出。」
所謂「溢出」,就是指在電磁力消失後,原子間的作用由強互作用力接管,它成了釘死原子的那根釘子。所以,水滴內部那個力場,才是關鍵中的關鍵。
強力由核子之間互相交換膠子產生。所以,三體人這種魔法般的科技可以這樣理解——有兩隻螞蟻,它們原本只能在乒乓球大小的空間里交換信息素;但在那個神秘力場的作用下,信息素的交換範圍擴大到了整個鳥巢!
「藍色空間」號通過四維空間碎片進入水滴內部,拆除了它的力場發生裝置。之後,水滴表面的強力消失,它立刻變成了一塊普通的金屬,光滑和堅硬都不復存在。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沒有四維空間,人類能夠摧毀水滴嗎?
這個問題我們暫時放一放,先來看看另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問題。
「魯伯特之淚」
有同學靈機一動:聽說有一種尾巴長長的玻璃球也很「頭鐵」,而且它的樣子和水滴幾乎如出一轍。大劉在寫水滴的時候,靈感是不是來自於它?
這位同學提到的這種玻璃球,有一個很浪漫的名字——「魯伯特之淚」。
「魯伯特之淚」最近有點兒火,這一方面是因為它神奇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個名字。實際上,它的英文名是Rupert's Drop,命名來自巴達維亞魯伯特王子。1660年,王子把五顆「魯伯特之淚」送給了英王查理二世,它們從此聞名世界。
「魯伯特之淚」的頭部非常堅硬。被子彈打中時,子彈被撞得粉碎它卻安然無恙;用液壓機去壓,要加到二十噸的壓力才能把它壓碎。
這一點,和水滴確實有點兒像。

但「魯伯特之淚」那個細細的尾巴卻無比脆弱,只需用手指輕輕一捏就會斷裂。不光如此,裂紋會以五倍音速在它的身上擴散,這個過程讓它看上去像是瞬間爆裂開來。
該同學繼續發散:那麼,我們破壞「魯伯特之淚」的方法,可不可以用來摧毀水滴?比如,如果嘗試攻擊水滴最脆弱的部分——那個同樣尖尖細細的尾巴——會不會更容易一些?
這就要從物質的結構上去分析了。
「魯伯特之淚」頭部的堅硬,和強互作用力沒有任何關係,起作用的仍然是玻璃分子之間的電磁力。
人們用交叉偏振光鏡觀察了「魯伯特之淚」形成的過程:熔化的玻璃滴進水裡之後,它最外面一層最先凝固,但此刻它的內部還是灼熱的液態。這些液態玻璃隨著冷卻體積開始變小,並拉著已經凝固的外殼收縮,此時外殼和內部受到方向相反的巨大應力。當整個液滴全部凝固後,這樣的應力存在於它的每一個分子之間。分子們看上去安安靜靜,卻都被身旁的夥伴死死地扯住,處在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中。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它的整個機體立刻就會被無處不在的應力釋放所裹挾,那也就是它灰飛煙滅的時刻。
而這個平衡是非常容易被打破的。因為「魯伯特之淚」纖細的尾部的確沒有多少強度,但它卻是整體應力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個命門就是它軀體內巨大能量的導火索。
假設玻璃的分子間電磁力是一根橡皮筋,那麼,「魯伯特之淚」的頭部由於特殊的冷卻過程,讓這根橡皮筋拉緊了。它的堅硬就來自這種拉緊,它爆開時的慘烈同樣是來自於這種拉緊——拉緊的橡皮筋比它鬆弛的時候,儲存了更多的能量。
但說一千道一萬,這根皮筋始終只是皮筋而已,它拉得再緊也不是鐵鏈。
電磁力和強互作用力對比起來,幾乎就是橡皮筋和鐵鏈的差距。所以,即使是它最堅硬的頭部,在水滴面前也完全不堪一擊。
三體人能夠製造出智子,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維度」的本質;三體人製造出了水滴,是因為他們掌握了「硬度」的本質。
那麼,所謂的「硬度」,到底是什麼?
硬度的本質

硬度,物理學專業術語,是指材料的局部抵抗硬物壓入其表面的能力。
簡言之,你能被我剪斷、劃傷、錘破、壓入——而我自己完好無損,就說明我比你硬。
事實上,目前絕大多數硬度測試,採用的仍然是「劃痕法」和「壓入法」。
硬度計把一個極堅硬的合金小圓球,或者一個金剛石錐體,以一定的力壓進材料表面,根據材料塑性變形的深度或寬度,來計算出材料的硬度。
敲黑板——「塑性變形」,是指材料被壓入後無法再恢復原狀的變形,換句話說,它是一種「破壞性變形」。任何被測試材料的硬度,必然要比小球或者金剛石更軟,從而它自己先被「破壞」。
那麼,用這個硬度計來測試水滴的硬度,會發生什麼?
很簡單,被破壞的不會是水滴,而是小球或者金剛石。因為,決定「破壞還是被破壞」的核心要素,是各自分子間作用力的大小。
而強互作用力的強度,是電磁力的100倍!大劉的那句「它的強度比太陽系中最堅固的物質還要高百倍」,真的不是隨便寫寫的。
地球上的任何材料都依靠電磁力保持其形態和硬度,面對用強互作用力製造的水滴,它們確實像是「乳酪碰到了子彈」。
有人說:我們有八萬噸的超級模鍛液壓機,八萬噸這麼大的力,總會讓水滴產生變形了吧?
對不起,八萬噸的豆腐腦,澆在一百千克的鐵鍋上,會不會讓鐵鍋損傷分毫?
那麼,如果我們攻擊水滴纖細的尾部,即使不能破壞它,那能不能「掰彎」它呢?也許「掰彎」了,就能讓它失去一部分功能?
抱歉,這同樣需要你的「硬度」是足夠的。你可以調動排山倒海的力,但「硬度」卻是這個「力」的落腳點。如果沒有硬度的加持,無論力有多大,最終仍然像無數的雞蛋遇到石頭,最先裂開的是你自己。
歸根結底,硬度才是讓對方發生破壞的根本。
而硬度的本質,就是雙方材料的分子間作用力的類型以及大小。
能夠摧毀水滴的「武器」
難道在三維空間中,人類對水滴就真的毫無辦法嗎?
別急,辦法肯定有,但是……
我們已經知道,水滴之所以無堅不摧,根源在於其分子被強力所統治。但強力系統並非不能被破壞,事實上,核裂變和核聚變就是核子之間發生的反應。這個過程會產生質量虧損和能量釋放,並由質能公式E=mc²所描述。釋放能量的大小,則與一個叫作「結合能」的物理量有關。
結合能是粒子間相互作用的能量測度。我們之前說過,如果普通物質分子是由橡皮筋連接,那麼連接核子的強力就相當於鐵鏈。破壞橡皮筋需要的能量叫作化學結合能,而破壞鐵鏈的能量就是原子核結合能。

現在,我們假設水滴是由鐵原子組成,鐵原子核一個個整齊排列在它的表面。我們合理推測:斬斷兩個鐵核之間的鐵鏈,會比直接把鐵核打碎更容易些,我們不妨就以後者為標準。
人類能夠製造出把鐵核打碎的能量源嗎?或者說,哪怕是在理論上,存在破壞鐵核材料的手段嗎(讓我們忽略二向箔因果律等武器)?
那麼,兵器譜翻翻看。
武器一:高能粒子加速器。
鐵原子核共有56個核子,總結和能為481.6MeV①。而在歐洲核子中心的對撞機中,人類已經能夠將質子加速到光速的0.999999991倍,對應能量是7000GeV②(1GeV=1000MeV)!可以想見,只要水滴乖乖待著不動,它會在一瞬間被人類加速器中的高能質子束轟成篩子(如果一個質子轟擊一個鐵原子核,那質子的能量只需要1/7000有效就夠了)。
武器二:高壓。
鐵原子核的平均結合能最高(平均結合能=總結和能/核子數),這意味著無論是聚變還是裂變它都要吸收能量,所以恆星中心一般會有一個穩定的鐵核存在,它是恆星聚變的最終產物。但恆星演化並不只有聚變階段,一旦發生超新星爆發,最終剩下的往往是中子星(或者黑洞)。這時候它的鐵核已經不復存在,每個電子都被引力壓進了質子之中。這種由巨大引力形成的高壓,當然能夠毫不費力地撕毀水滴的強力薄膜,可惜的是,這樣的高壓人類怕是無法創造出來。

武器三:微型黑洞。
在《三體3》中,人類利用環日加速器製造出一個微型黑洞,並在它蒸發前將其射入木衛十三,後者的物質被悉數吸入後,黑洞變成一個穩定的存在。如果人類有能力把微型黑洞發展成武器,就可以驅動它向水滴發起攻擊,或者將其隱蔽在水滴的必經路線上守株待兔。水滴在與微型黑洞接觸時必然會被吸入,退一步說,即使由於時間太短來不及吸入全部,也一定會破壞掉它被撞擊到的部位。之後那個部位的原子將會消失,強力控制下的水滴將會因為力量的失衡而坍塌。
武器四:反物質。

正常物質是帶正電的原子核與帶負電的電子組成,反物質正相反,它的核外電子是正電子,而原子核卻帶負電。正反物質碰到一起將會發生湮滅,此時它們所有的質量將全部轉化為能量。目前,人類已經具備在實驗室初步製造反物質的能力,一旦這些反物質被武器化(在《三體3》中,維德確實製造出了反物質武器),它們將是對水滴最有效的威脅。水滴再堅硬,也不過是由正物質組成,一旦躲閃不及,它就會在反物質的槍林彈雨下灰飛煙滅。
武器五:自相矛盾。
在《三體3》中,人類已經能夠在實驗室少量製造強互作用力材料(SIM):「只要再給他們十年時間,強互作用力材料就可以大批量生產。雖然水滴的推進系統還遠遠超出人類的技術能力,但可以用SIM製造常規導彈,藉助數量優勢,一旦擊中就有可能摧毀水滴;或者用SIM建造防禦屏障,即使水滴敢於攻擊這種屏障,它也變成了一枚一次性的炮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才是最直接的武器。
兵器譜或許還沒有翻完,但可以確定的是,要想摧毀水滴辦法確實是有,但,目前基本上都只存在於理論中。
既然只是理論,那麼我們這樣的頭腦風暴就不必怕三體人聽見了吧。即使他們真的聽到了,大概率也只會說一句:「 啊這……主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