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她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反應了西周初年至春秋時期約五百年的社會面貌。

詩經

最美不過《詩經》
其中的《風》,又稱《國風》,分別採集了周朝十五個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民間歌謠,稱為「十五國風」,《秦風》是其中一個,記錄的是秦國百姓的吟唱。
但《秦風》有別於其他「十四國風」,在其收錄的十首詩之中,除了《蒹葭》是愛情詩外,其他九篇都帶著濃厚的男兒熱血,或是妻子對從軍丈夫的無限思念和自豪,由此表現出了秦地百姓莊嚴沉重,尚武好鬥的社會風氣。
其中,以馬為切入點,就佔據了三首之多。
如:《車鄰》、《駟鐵》、《小戎》都離不開馬的身影,可見,秦人和馬的關係十分密切。
為此,汪郎以為:秦國就是一個建立在馬背上的諸侯國!
那麼,秦國和馬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聯繫呢?在秦國近七百餘年的發展史上,能立國,得益於馬!

馬
1、秦國能夠立國,離不開首任國君嬴非子的養馬才華。
嬴非子能夠獲得「秦」的封號,充滿了時代的機遇。
作為是犬丘封主趙氏嬴大駱的庶子,按照周朝的嫡長子繼承製,嬴非子是沒有資格繼承犬丘趙氏嬴姓的家主之位,但他有一項通天的本領,就是會養馬。
凡是經他養過的馬,匹匹膘滿體肥,雄駿健壯,非常適合用於戰場廝殺的戰馬。
這在周朝是相當吃香的生存技能。
因為此時的周天子不是別人,而是違背了嫡長子繼承製,趁自己的侄子周懿王姬堅駕崩之際,硬是從帝國的法定繼承人,太子姬燮的手中奪取王位的姬辟方。

春秋諸侯
他痛恨自己的侄子周懿王姬堅在面對犬戎等蠻族時手無足措的軟弱,在國都鎬京多次被蠻族的尖牙利爪所威脅時,不去積極整頓軍備,而是以遷都方式進行躲避。
「(懿王)七年,西戎侵鎬;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遷於槐里。」---《竹書紀年》
這樣有損大周王朝的威嚴!
故而坐上王位的姬辟方,第一件事就是兵伐犬戎。
「(孝王)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竹書紀年》
要興兵討伐就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而建立軍隊就需要大量的戰馬,這個時候,嬴非子的出現解決了姬辟方的難題。
「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史記.秦本紀》

周天子遷都
高超的養馬術,踏實的工作態度,讓嬴非子獲得了姬辟方的高度認可。
故而,不具備族長繼承權資格的嬴非子,讓奪權上位的周天子姬辟方產生了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這引發了申國侯對犬丘趙氏嬴姓一族族長繼承權的強烈干涉(申侯是嬴非子兄弟嬴成的外公,嬴成是嬴大駱嫡長子)。
人才是國家進步的重要保障,姬辟方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
為了鼓勵嬴非子能夠更用心地為王室養馬,他在無法改立嬴非子繼承犬丘趙氏嬴姓的族長之位時,大筆一揮,讓嬴非子在秦地(今甘肅天水)另立一宗,並賜予嬴非子「秦」的封號。

秦都八遷
「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史記.秦本紀》
當然,此時的「秦」還不能算是諸侯國,只是佔地五十里的周王室附庸,但不管如何,嬴非子從庶子一躍成為秦地趙氏嬴姓的始祖,完成了趙氏嬴姓新支派的開宗之路。
而這種身份上的改變,也就意味著嬴非子及其後人和犬丘嬴姓一族脫離了宗法上的尊卑束縛關係,從此海闊任魚躍、天高任鳥飛。

嬴非子
2、秦國從周王附庸,到西垂大夫,再到諸侯,其實就是一條血與火的馬背上淬鍊之路。
嬴非子開宗之後,秦嬴一族除了在封地秦邑繼續為周室養馬之外,又成為姬周抗擊犬戎入侵的第一戰線。
在和犬戎的長期戰鬥中,秦嬴一族目睹了犬丘趙氏嬴姓的覆滅,送走了戰爭中被西戎殺害的國君秦仲,保護周天子東遷雒邑,他們在馬背上得到淬鍊,在戰火中得到重生,每一步都意味著秦國的逐步壯大。
作為姬周西部最堅實的軍事屏障,秦國由王室附庸,晉陞為西垂大夫,再上升為諸侯,秦嬴一族及其統治下的百姓,都養成了尚武、彪悍的民風,最終成長為一支令東方諸侯恐懼的強大存在。

秦軍
在戰火中淬鍊的秦國,到底有多強大呢?
史載: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王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稱數也。」---《戰國策.韓策一》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馬,離不開一支強大的戰車部隊。
在西周及春秋時期,衡量一個諸侯是否強大,並不是以該諸侯佔有多少土地和人口作為標準,也不是以該諸侯統治區域內的物質產出和經濟實力為指標,而是以戰車的多寡為標準。
這就是先秦時期的文獻中,常常提到的「千乘之國」、「萬乘之國」的說法。

秦軍戰車
一乘就是一車。
每乘的標準配比:四匹馬拉的兵車一輛,車上戰士3人,車下步卒72人,後勤25人,共計100人。
到了戰國時代,因為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以及戰爭思想道德體系的轉型,奇謀詭詐的兵道之法大為盛行,戰車不再作為各國諸侯衡量自身強弱的標準了。
但即使如此,秦國依然維繫著一支千乘的戰車部隊。
馬是秦人立足西陲,並逐步成長為一方諸侯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同時也在秦國睥睨天下的氣勢中增添了濃厚的一筆。

戰車方陣
3、汪郎說:
因馬成國,由馬成軍,秦國的一路走來,始終無法掙脫和馬之間的關聯,事實上,馬已經滲入了秦人的方方面面。
如:《國風.秦風》中的《小戎》,詩中的主題雖然是秦婦對出征夫君寄予的深情思念,但從側面也可看出,秦人通過對戰馬、戰車的述說,散發出的對秦軍軍容、軍備強大的自豪,也向世人傳遞著秦軍尚武、不屈的精神。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①
詩既是詩人內心的折射,也是詩人對社會的寫實。
《秦風》是秦國百姓的吟唱,抒發的是也是秦國百姓內心深處對尚武精神的追求,以及對外敵無畏的悲壯氣息!
而我,通過《秦風》,也看到了一個敢於亮劍、有血有肉的百戰之秦!
註:
①《國風.秦風.小戎》節選
【我是江東汪郎,帶給你不一樣的歷史視覺!堅持原創,喜歡我就請關注我吧!】

《秦風.無衣》郵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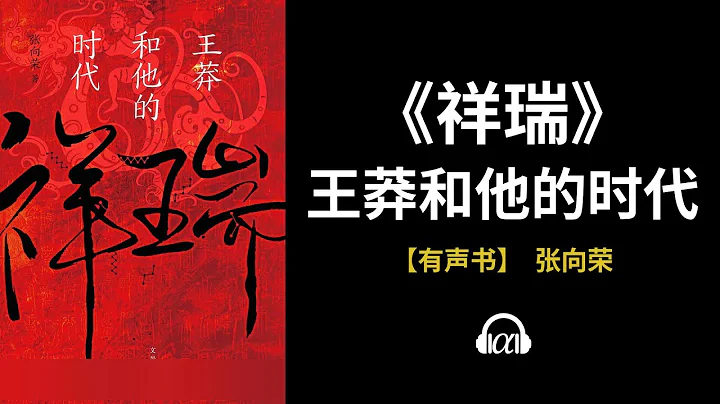



![[MAMA 2022] IVE, KEP1ER, NMIXX, LE SSERAFIM, NEWJEANS - 'Cheer Up' Lyrics (Color Coded Lyrics)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emQIKe2tGl8/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itWecJGXwnCsgIXjiSuzCmdM-1w)
![NewJeans在宣布獲大賞後全員毫無反應 「你們忘了嗎?我們是NewJeans啊」XD| [K-潮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VpJrVDAgBLs/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XE8uvu_gvrtmhqxrfNkwM21qLA)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 SSERAFIM&NewJeans - CHEER UP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d2heDnR3sjc/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AaAaOJ1FOuMVt8zl0aAdxxx1s2FQ)

![[2022 MAMA] IVE&Kep1er&NMIXX&LESSERAFIM&NewJeans-ELEVEN+WADADA+O.O+FEARLESS+Hypeboy | Mnet 221129 방송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IJks7TIDfnk/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Y-vECgvowNPEf_1BO1TlRrKZwj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