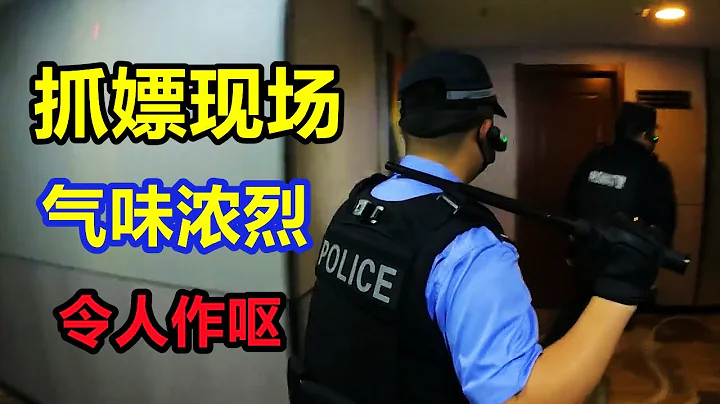今天是《黑神話:悟空》藝術展正式開展的第一天。
我預想過這次展覽的陣仗或許會很大,但當我走到舉辦場地時,還是被掛滿大半個校門的巨幅宣傳畫震撼到了。

作為《黑神話》的首次大規模線下展覽,這次的藝術展選在了西湖邊的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包括負一層在內的上下四層,全都用來盛放600多件展品。
在入場領取的導覽手冊上,寫著「本次展覽希望在《黑神話》和觀眾之間建立一種交流」,這也是我一天逛下來的最大感受。
這種「交流」一方面體現在身臨其境的觀展體驗上。展覽正式開始前,在展廳入口的正前方就能看到著一座1:1還原的土地廟存檔點,香爐里還插著一支未燃盡的線香;進入第一個展廳後,第一眼就能看到一座1.13:1(比遊戲尺寸更大)的天命人雕像。


這樣等比復刻的遊戲角色、道具和場景,在整場展覽中佔了相當重的比例。
比如最後決定的遊戲結局走向的金箍,就是用足斤足兩的純金打造;玩家一路收集的葫蘆,也都按照故事設定中的材質儘可能還原了出來;還有伴隨天命人一路打怪升級的棍子,也掛滿了整整一面牆。



其中最讓我震撼的,還是「風起黃昏」主題展廳。上百平米的場地,都被布置成了黃風嶺的地貌,一個1:1的無頭說書人坐在石頭上,旁邊還擺著個小音響不斷播放著「黃風嶺,八百里,曾是關外富饒地……」的陝北說書調子。

而在這一幕場景的正對面,則赫然陳列著一個巨型的靈吉菩薩頭顱。

也就是在這一刻,我才覺得這場展覽似乎真的想讓人覺得「這個故事真的發生過」。用大比例模型構造出的擬真感,讓玩家彷彿置身到遊戲的場景中,某種程度上的確是讓玩家走進了遊戲,也更近了一步。
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整場展覽的大部分展品都沒有使用玻璃罩保護。據遊戲科學的工作人員介紹,他們在策展時內部也為此爭論了很久,但最後為了更好的臨場感還是這麼做了。
特別是遊戲中小西天場景的懸塑展品上(藍田水陸庵的懸塑原型),他們還特意把原本高高掛在樑柱之間的塑像,拆分成小塊等比復原了出來,並放到了觀眾能看清的位置。讓遊戲中那些雕樑畫棟的場景,變成了字面意義上「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而不用再隔著一層電腦屏幕。

這種近距離的「交流」不止存在於遊戲與玩家間,也出現在了參觀者和《黑神話》的製作者之間。
現場除了出現在遊戲中的物品,也有大量未能實際出現在遊戲中的展品。
很多設定原畫的展品旁,都會像設計課的學生作業一樣,放上這張原畫的參考圖或設計過程。有的和最終實裝到遊戲中的相差無幾,有的則明顯經過了大幅修改。

鐵扇公主的設定圖

這一稿黃風嶺和我們玩到的版本就有很大出入
在現場密密麻麻擺滿了半個展廳的影神圖中,還出現了兩幅沒有名字的神秘圖畫。據遊戲科學的工作人員介紹,這兩張影神圖是最後沒有用到遊戲中的廢案。

另一側的原畫展品里,也有三幅最終沒能用到遊戲中的廢案,它們都是最後被遺憾砍掉的「獅駝城」。



一圈逛下來,整個遊戲的誕生過程立刻清晰了不少,就像也跟著製作組一起經過了從定稿到砍廢案的全過程。就連「夜生白露」章節(小西天)的定格動畫製作過程,也通過現場視頻和道具展示的方式,全部擺到了參觀者眼前。
這些《黑神話》台前幕後的創作者們,以這樣一種特別的方式完成了和玩家的交流。

這場藝術展本身無疑能達成一種「開發者與玩家」之間的無聲交流,而在現場,我也能感受到另一些不局限於「遊戲」命題的情緒流動。
在展覽的遊戲試玩區,有不少受邀觀眾帶著孩子在其中試玩遊戲。這些家長小孩的組合大都是孩子站著玩,家長站在後邊看,一邊問著在孩子看來是常識的問題,一邊指出路旁的一尊雕像是不是剛才在某個展廳看見過的。
最讓我感到驚訝的,還是在聽工作人員介紹展品時,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開始向工作人員提問,我探過頭去一看,一個寫著「1818」的話筒正擺在工作人員面前。以報道杭州本地家長里短聞名的節目「1818黃金眼」,突然出現在眼前問著些關於遊戲開發的問題,讓我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恍惚感。整個展廳里,除了遊戲玩家之外還有著大量或許不怎麼了解遊戲的觀眾。
據我的觀察,他們有的是社會新聞的記者,有的是杭州某個職能部門的員工,有的是畫家,但在這一刻卻都在《黑神話》的展廳里聽著這款遊戲的開發歷程。
在參觀完所有展品後,回到美術館大廳我才看到館長、馮驥、楊奇為展覽題寫的前言。其中楊奇說的最短:藝理恆真,因時頌之。遊戲藝術,登堂入室。

這裡的登堂入室當然可以包括那些高大上的殊榮,比如展廳一側《黑神話》滿牆的獎盃,當天到場的眾多杭州本地領導,以及前兩天遊戲科學剛剛以集體的形式入圍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的評選。
當這麼多形形色色的人因為遊戲齊聚一堂,都在把《黑神話》當做藝術討論,也因為遊戲產生了交集,也讓遊戲成為民生新聞也來報道的「家長里短」——這應該也是一種登堂入室吧。
藝理恆真,遊戲也一直沒變。但好在遊戲、開發者和玩家們身處的環境已經慢慢好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