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主席之于新中国的诞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打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处境,为了给中国人民创造一个新世界,毛主席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
在这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中,毛主席先后失去了六位亲人,是世界领袖人物中,牺牲最多,牺牲最大的领导人。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毛主席唯一活下来的儿子毛岸青,拥有了一段完整的人生。不仅过上了“平凡”的生活,更拥有美满的家庭。那么,他的晚年过得如何呢?又享受到了哪些待遇?

苦难童年与无尽的病痛
毛岸青是杨开慧和毛主席的次子。他1923年生于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4岁时,因母亲杨开慧被何键杀害,不得不跟着哥哥毛岸英、弟弟毛岸龙到外婆家生活。
然而,弟弟毛岸龙不久夭折,国民党的围剿又愈演愈烈,毛岸英俩兄弟只好被送往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所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生活。
那时,两兄弟还不知道,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人生挑战。

1932年3月,由于大同幼稚园保育员管荷英在外出期间失踪,负责管理幼稚园的特科员为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只好解散幼稚园,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寄养到地下党董健吾的家中。
当时董健吾的家是地下党的联络点,位置还跟法国捕房相隔不远,董健吾为了兄弟两人的安全着想,只好求助前妻黄慧光代为照顾孩子,每月还给他们送去30元钱的生活费。

黄慧光本就是家庭妇女,除了毛家兄弟外,他自己也有四个小孩要养。起初,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黄慧光虽然不事生产,但警觉性却很高。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她就立刻带着孩子搬家。在毛岸青的记忆中,那段时间,他们总共换过六个地方。
可后来,他们的日子就难过了。董健吾的失业直接影响了黄家的生活,黄慧光只能带着几个孩子做些手工灵活维持生计。偏偏,毛岸青还得了麻疹,毛岸英感染风寒。

缺吃少喝的情况下,黄慧光更是忙得焦头烂额,心浮气躁间便会打骂孩子。这对于少小离家的毛岸英冲击巨大。所以,趁着黄慧光不注意,他就带着弟弟离家出走了。
那是1935年的秋天,两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小孩子,就在茫茫大上海当起了流浪儿。
白天,他们就靠给别人拖地板、捡破烂换口饭吃,困了,就找个马路牙子睡觉。后来,毛岸英发现上海外白渡桥那里经常有黄包车拉不上去,帮忙推车,对方就会给几个小钱,他又带着岸青干起了这个活计。
可不幸的是,流浪期间,毛岸青遭遇了巡警的追打,对方专门往孩子的头部招呼。这番殴打,让年幼的毛岸青被打出了脑震荡,其后遗症就是让他患上了折磨终身的精神分裂症。

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中央特科人员得知毛主席的儿子出走后,急得团团转。他们发动了所有隐藏在上海的地下党,奔走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才在一间破庙里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
1936年4月,受毛主席委托,在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毛岸英和毛岸青跟随东北义勇军的李杜将军前往法国马赛,在那里,他被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接收,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苏生活。

婚姻与晚年
抵达莫斯科后,毛岸青跟着哥哥住进了国际第二儿童院,还拥有了个俄国名字亚历山大。
由于在上海时没能进入学校读书,毛岸青的中文读写能力较差,给爸爸毛主席写信用的都是俄文。搞得毛主席每次乐呵呵地读儿子的家书,旁边还要跟着师哲,这么个俄文翻译。
卫国战争期间,性格忠烈的毛岸英主动申请去前线参战,一直跟随哥哥的毛岸青便也跟上了战场,干些挖战壕、送伤员的后勤工作。

再回故土时,已是1947年,毛岸青已经从当年的半大小子长成了24岁的青年。尽管已经许久没见过爸爸的面,但是对于父亲的工作,毛岸青给予全力支持。在毛主席身边没待多久,毛岸青就跟着其他工作人员跑到气候寒冷的黑龙江齐齐哈尔搞土改工作去了。
奈何,精神疾病始终不肯放过这个有志向的年轻人。1949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做俄文翻译的毛岸青经常给毛主席写信。详细地告诉父亲,自己的脑子里始终有一个“小家伙”在跟他捣乱。
身为人父,毛主席心疼儿子、愧对儿子、同样也深爱着儿子。在听取其他医护的意见后,他只好忍痛,再次将毛岸青送到苏联去治疗。

然而,苦难并没有离开,反而对毛岸青百般刁难。当时,在苏联使用的是封闭治疗。因为过度使用激素的缘故,毛岸青浑身浮肿,病情不减反重。再加上当时中苏关系,毛主席便安排毛岸青到大连去疗养。
当时在中苏边境迎接毛岸青的是时任旅大市(大连市旧称)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的张世保。据他回忆,第一次见到毛岸青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30多岁的毛岸青神情憔悴,沉默寡言,整天都是病恹恹的样子,眼神忧郁得很难跟风华正茂的中年人联系到一起。因此,张世保决心要好好照顾他,为毛岸青提供最好的服务。
脱离封闭的空间,大连的海风和沙滩让毛岸青的心胸逐渐开阔了起来,话也越来越多。由于少年时期在苏联的成长经历,毛岸青的很多生活习惯跟欧洲人相似,没事就跟张世保打克朗棋,看俄国文学书。张世保还特意给他找了一本俄文版《西游记》,常常把毛岸青看得捧腹大笑。

毛岸青病情向好后,旅大市的很多人开始琢磨想给毛岸青介绍个女朋友谈谈。于是,几个热心肠的同志就给他找了一个女护士,让其在照顾毛岸青的时候,培养感情。
岂料,36岁的毛岸青从来没对哪个姑娘动过心,更没有恋爱经验。女护士照顾他两个多月,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是按照张世保给他安排的作息,出门散步,打克朗棋,闲暇看书。有时候,看书太专注忘了吃药,女护士还要再三催促。
大家一看这个情况,也就知道两人没戏,便不好再给他介绍女孩了。
不过,缘分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很玄妙。1960年1月,毛主席的亲家母张文秋带着自己的二女儿邵华也来到旅大疗养。张文秋此行的目的,是在毛主席的同意下,来给邵华和毛岸青“相亲”来的。
邵华是毛岸英妻子刘思齐的妹妹,从小就经常跟着姐姐、姐夫到毛主席家玩耍。长大后,她因酷爱文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有一天,她在跟毛主席谈论《简·爱》时,毛主席就想起了在旅大养病的毛岸青,说他三十好几的人,找对象谈恋爱不应该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儿子,应该介绍自己是中宣部的翻译。
毛主席还说,要毛岸青把择偶标准降低些,找工人或者农民。眼光高了,人家能力强,会被人看不起,生活自然不如意。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邵华虽没见过毛岸青,但是却对他产生了好奇心。正好,张文秋有意跟主席家再结连理,他们便安排放寒假的邵华到大连来探望毛岸青。

谁也没想到,两人一见面,毛岸青就对邵华一见钟情。这次相见虽然短暂,但是两人却经常往来书信,以信寄情。
此后,在交往一段时间后,毛岸青与邵华在196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在旅大宾馆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在旅大生活了一年时间。邵华酷爱摄影,经常拉着毛岸青去海边、公园拍照。毛岸青则喜静,常常捧着俄文书看个不停,间或翻译的俄文材料也总会被拿去刊登。
这么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相处起来,竟然非常和睦。学习好的邵华还跟着学会了不少俄语,常常跟毛岸青用俄语交流。

用邵华自己的话说,毛岸青跟当时很多的周边人不同,特别浪漫,还能歌善舞。不仅教会了她跳华尔兹,还喜欢一件大衣两个人披,挽着她在街上散步。这在当时的男性中,是很少有的浪漫举动,让邵华倍感甜蜜。
就在这种幸福中,他们迎来了自己的儿子。当时,消息传回中南海,毛主席笑得合不拢嘴,亲自给孩子取了名字。
此后,毛岸青和邵华一直居住在北京市郊,除了日常工作,就跟很多父母一样,忙着教育孩子。

毛主席过世后,毛岸青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当一个“平凡”人,不愿接受特殊的待遇,只有在医疗上破格享受到了副总理级别的照顾。
除了继续翻译俄文著作外,他经常带着妻子和儿子重走长征路,搜集革命时期的点点滴滴。并且,与邵华一起整理大型丛书《中国出了个毛主席》的文献资料。
唯一特别的是,每年的毛主席诞辰,他都会带着妻子儿女出现在毛主席纪念堂,回忆他与毛主席那短暂,难忘的父子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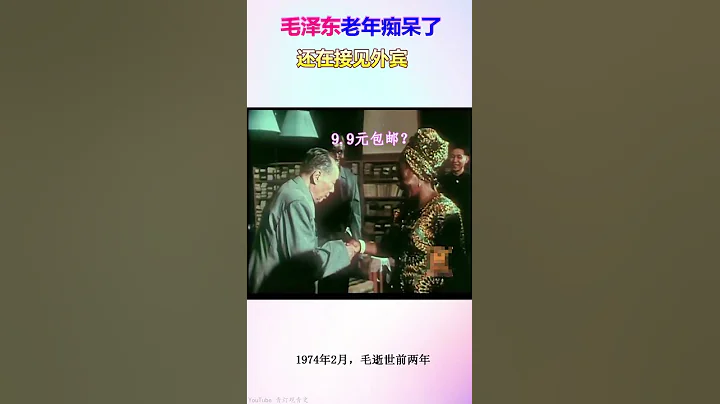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结】《我的女将军大人》女将军穿越意外嫁总裁,被心机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来了?总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宠#霸道总裁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