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平安是福
1969年8月中旬,15歲的我與軍科幾乎連鍋端的69屆初中畢業的大院孩子們一起,坐着綠皮火車咣當咣當地來到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18團七連,在包頭市的東南方向約20里處的位置。

我被分配到了第九班。從此,開啟了我初次踏入社會為期八個月的農墾生活。這段日子,在我的工作經歷中雖然很短暫,卻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01
九班副樹立起威信的艱苦歷程

在學校和在軍科大院孩子中從不顯山露水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剛到兵團領導就指定我為九班的副班長。至今都50年了我也沒弄明白原由,反正也沒地方問去,都不知道連長和指導員在哪裡,姓甚名誰。(噢,想起來了,我在文革複課時,當過短暫的初中某班班長。)
哎呀,這個小小的副班長頭銜可把我害苦了!全班除了胡陵秋外,我是第二個年齡小的,上面還有好幾個67屆68屆的大姐姐們,誰聽我的呀?
班長是個67屆的叫什麼鳳的人特別精明,凡是她不喜歡做的能推脫的事情都指派我去辦。像什麼開班會學習討論念報紙,打掃廁所衛生,代表班裡齣節目等等。
到時候開會了,該肅靜了,可是我喊了半天都沒人聽,還是各說各的嘰嘰喳喳。我的小臉憋得通紅,干著急不管用,直到班長發話才安靜下來。這種局面直到發生了幾件事情後才扭轉了,現在我只記住兩件事。
一次是冬天連里給我們班分配打掃廁所的任務。
班長安排我帶領幾個班裡比較鬧騰不服管的去。我們領了鐵鎬、鐵鍬、竹筐,到了廁所(那個時候都是露天的)門口,她們都站着不動,有人提議讓副班長先干。
呵,干就干,到了兵團誰還怕幹活呀!我拿着鐵鎬就去,那可是冬天,糞坑裡的屎和尿都結成了厚厚的冰。每刨一鎬頭,臭冰碴子就會濺到臉上和身上。
我不在乎,揮起鐵鎬一鎬一鎬賣力氣地刨。其他戰友們看到我一點也不嫌棄,都不好意思的陸陸續續加入進來。她們可都是自覺地加入勞動中的,我沒有招呼她們一句類似「別都站着,來幹活呀……」之類的話。因為我知道,越是叫她們幹活,就越是沒有人參與。這樣,我們終於一起把廁所打掃乾淨收工啦。
又一次是平整土地挑土。
我們班有一個從海淀區黑山扈生產隊來的農村女孩,從小就會幹農活,身子骨長得黑壯黑壯的,像個假小子。我們有拿鐵鍬的有挑竹筐的,三人一組分工合作。
給我分配的是挑竹筐,兩個戰友用鐵鍬把土裝滿兩個竹筐後,我負責把土從田地的東頭運送到西頭,有多遠我也說不清。
幹了一陣子,那個假小子就向我發起挑戰,要和我比試一下誰挑得擔數多。她嘴裏還一口一個副班長叫着,不應戰就是慫包。
儘管我從小沒幹過這些,連在家裡擦桌子掃地都逃避的嬌嬌女,如今要和比自己大兩歲的農村妞比體力,比干農活,那不是自找苦吃嘛!可我是軍人的孩子,能認慫嗎?絕對不能!
好,比就比,怕你不成,我也不是吃素的!結果,那天下午比到收工時,她挑了八擔土,我也挑了八擔土,打了個平手。最後,她把扁擔一扔,一屁股坐在地頭上邊喘氣邊說:副班長,我算服了你了。
我才不坐下歇着呢,挺直了腰桿,昂起頭擺出勝利的小樣,牛哇!她哪裡知道,我的右肩膀都磨出了血泡,又紅又腫。
晚上我鑽到李清菊的被窩裡痛哭了一場。清菊比我大一歲分配在十班,卻看見了我與假小子比賽的全過程。看着我肩膀傷的那模樣直心疼,不停地嘮叨我:你是什麼身子骨,能和她比嗎?以後別再干這樣的傻事兒啦!我咬着牙說:她們不服氣我還得這樣拚命,直到她們服了為止!
自此以後,她們都佩服得不行,從而,奠定了我這個九班副的領導地位。開會時,只要有人亂說話不安靜,不用我吭聲就有戰友大聲吆喝:靜一靜,別說話了,聽副班長的。
耶,小小的我好開心吶!
02
對人情世故,世態炎涼的初體驗
在接近1969年底的一天,陽光明媚,我和一個閨蜜行走在荒漠的羊腸小道上,一路聊得挺開心,我把她送出連隊已經很遠了才依依不捨地分手返回連隊。哪知道這次分別對我的打擊力度相當之大,以至於使我決心和她斷絕來往,不再做朋友,做閨蜜就更不可能啦!
她這次一走是徹底地離開兵團穿上軍裝當兵了。消息還是通過別人告訴我的,而不是她本人。當時我的心被狠狠地撕裂,臉上流着淚,心中流着血,有一種不被信任的羞辱感。那麼好的閨蜜,不說在兒時的玩耍,只說在兵團艱苦的生活中曾經同甘共苦,互相慰藉。可她在離開的時候連一個字都不跟我說,這還是閨蜜嗎?連起碼的信任都沒有,今後我還能相信誰?我那15歲青春期的小心臟要崩潰了!
當我陸續收到她從部隊寄來的信件和軍裝照後,慢慢的心情平靜下來,理解了,釋懷了。我想,要是我有這麼一個機會去當兵,當然也是選擇離開了。不過我不會和閨蜜們不辭而別的,因為我不想讓幼小的她們和我一樣受到刺激和傷害。
這事兒都過去50年了,早已經翻篇了,我們現在仍然是要好的閨蜜。
雖然我在花朵的年紀遭遇過信任危機,但在今後幾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都不會戴着有色眼鏡去看人,也不會聽別人說他好我就去喜歡,更不會聽別人說他壞就一定會疏遠。而是要自己接觸,自己了解,然後再做判斷。
至今我依然是以真誠待人,熱情助人。我覺得無論別人怎樣,我的那顆善良的心不能變。要學會原諒,而且還要感謝那些傷害過我的人,是他們激勵我奮進,使我變得成熟,使我更加堅強,使我能夠面對任何困難而永不退縮!
同樣是在1969年年底,在兵團里還有一件事情讓15歲的我深深的明白了今後的路要靠自己走,父母可能再也呵護不了我了。
那就是北京備戰備荒的大疏散。我們部隊大院的很多家庭,都隨着父輩們的工作變動而牽出了首都北京。為了安撫我們在內蒙兵團屯墾戍邊的七八十個孩子們,大院委派了三個軍隊幹部兩男一女來看望我們。那兩個叔叔是誰我記不得了,阿姨是專門來看女孩子的,叫什麼我也記不住,只知道是院里門診部的。
我們七連一幫女孩圍坐在炕上,阿姨在中間笑眯眯地跟這個女孩講:你爸爸到哪個軍區任職,她爸爸到哪個軍分區當什麼什麼官了。女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問阿姨自己家裡的變化,爸爸媽媽都去哪個省份哪個城市了?我也找空隙不停地問阿姨我爸爸去哪兒啦,心裏很着急,我間斷性地問了好幾次,阿姨只是看了看我不回答。
記得這個阿姨曾經來過我家幾次找我爸爸,在大院里碰到我時總是很和藹地和我說話,問長問短,所以我對阿姨很有好感。我想,阿姨被大家問得顧不上我吧,就等到她回答完所有同學的話再次問及我的爸爸。阿姨扭頭看着我,那張與別的女孩面帶笑容和藹可親的臉迅速耷拉下來,一臉陰霾並以溫怒的低沉的近乎於低吼的聲音說:你爸爸啥也不是了,退啦!
我去,這臉變得也太快了吧?!聽到我爸爸不再擔任職務的消息並沒有讓我驚訝,反倒是阿姨這張變幻多端的臉着實是嚇着我了。這個大白眼,使我立刻聯想到那些父母遭受迫害、挨整的孩子們、同學們,她們比我更慘,在比我的年齡更小的時候就遭受到比這更多更狠的白眼和辱罵。想想他們這個時候父母還在接受審查,我的爸爸不過是不再工作罷了,又沒有被圈起來進行勞動改造,已經是不錯啦。他們都挺過來了,我怕什麼?我有兩隻手,能夠生存,能夠養活自己,不求多富貴,能填飽肚子就行。想到這裡,調整好心情,第二天醒來,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和往常一樣開工去了……

我時常在想,自己遭遇過的挫折和受到過的負面衝擊,是人生中任何人都不可迴避的事情,這些經歷實際上是自己寶貴的精神財富。可以說日後除了當兵是托父親的關係走後門入伍外,什麼入黨、提干、上大學,晉陞職務,在朝為官也好,下海經商也好,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所以我時不時的感到自己很驕傲很自豪!
在政府部門工作時遇到的熱情接待,我明白是因為自己的工作身份所致,萬不可張揚跋扈,目中無人。在公司工作時遇到客戶的挑剔和刁難,也會盡自己所能去溝通去協調,直到實現既定目標為止。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自己只是渺小的一粒沙子,早已融入到沙漠或者大海中了。
03
醞釀逃跑
在軍科子女來兵團插隊的同學們,三三兩兩陸陸續續地成功逃跑回家的實例刺激下,我也蠢蠢欲動,開始策劃逃跑行動。
那時,爸爸媽媽帶着弟弟已經離京去了北京軍區駐臨汾的休養所。聽媽媽說這個地方還是受政治迫害仍然靠邊站的葉帥給爸爸找的落腳點,葉帥還悄悄跟爸爸說如果不喜歡再給他另外找地方。為此,媽媽專門去臨汾休養所看了一下,回來向老爸彙報覺得還不錯,就把家搬去了。自然是爸媽到了哪裡,孩子們就要投靠到哪裡。
北京沒有家了,去臨汾,就這麼決定了。
去臨汾的路線怎麼走呢?在一個休息日,我和同班的胡陵秋向連里請假外出被批准了。我們徒步走了15里地來到萬水泉火車站,向一個值班的大叔諮詢有沒有去臨汾的火車?大叔很耐心的告訴我們沒有直達的,只有到太原再換車去,並且告訴我們發車時間和全程的票價,兩段車程加起來要將近15元錢,而且去太原的車不是每天都有,好像是一周才一趟。

萬水泉車站
這個信息太重要太及時啦。可是摸摸自己的口袋,積蓄還不足兩元錢。沒關係,我努力積攢。當時,我們兵團戰士包吃包住,每個月有5元錢津貼(供我們購買牙膏、肥皂、衛生紙等日用品和解饞的糖果)。我嚴格控制自己的支出,省吃儉用,溜溜的攢了三個月,終於把火車票錢湊足了。
我逃跑之前告訴了好幾個閨蜜,印象最深的是李小俐那副走不了很無奈的模樣。是一個午後,小俐坐在她們班門口的小板凳上曬太陽,我走過去俯下身子悄悄地告訴她,明天天不亮我就逃跑了,特來道個別。小俐一聽都快哭了,仰頭看着我顫抖着聲音說:你們都走了,我怎麼辦呀?入團了哪也不敢去,早知道就不入了。
可喜的是我這些閨蜜們一個也沒有出賣我,都是值得信賴的好朋友。
算計好開往太原的火車日期,大概是1970年的4月4號凌晨,在沒有鬧鐘的情況下,極度緊張的大腦中樞神經喚醒了我,摸着黑從地鋪上爬起來穿好衣服,初春的季節怕春寒,把兵團發的棉大衣、棉帽帶上,提着自己認為存放貴重東西的旅行袋,朝着萬水泉火車站進發。
從連隊到火車站有15里地,天還黑漆漆的,我頭不回腿不停地一路向前。路過團部附近的一個村莊時,天空出現了一點點魚肚白,直視遠處堤壩上有個早起的老鄉,我沒有停下來,和他對視了一陣,誰也沒有說話,直到他的身影落在我的背後也沒有聽見任何響動。
天漸漸泛起早霞的紅光,火車站也出現在我的視野里。到了車站,售票窗口只有我一個人,問好值班員現在幾點?去太原的火車過去沒有?值班員的回答讓我興奮不已,時間趕上了。
當七點的火車進站時,站台上只有我一個乘客。登上列車找到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後,內心不能平靜,眼睛不停的看着車廂門口,深怕連隊派人來追我。要知道,我們一起來兵團的同學有好幾個逃跑的都被抓回去了,有的不止抓回過一次。我那顆懸着的心隨着一聲汽笛和火車輪子的慢慢啟動放下了。車廂里的喇叭開始播放那個年代的革命歌曲,都是我會唱的。伴隨着歌聲和車輪的提速,我的心中狂喜,哈哈,逃跑成功啦!真想放開歌喉與喇叭里的聲音一起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
當火車行進了一段時間後,有列車員和車長走過來問我會不會唱歌跳舞?那還用問,當然是小菜一碟了,我是兵團七連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呀!唱歌跳舞、獨幕話劇都演過。
可是,我斷然拒絕了,說我這些都不會。他們不相信,說一看我就會,別不好意思,為乘客們唱歌跳舞也是為人民服務。我堅持說不會,他們失望地走了。這個時候我是「逃兵」,哪能大張旗鼓地表現自己呢,招來橫禍怎麼辦?我可不想被抓回去。眼瞅着他們組建的臨時宣傳隊一個車廂一個車廂的表演節目,我為他們的付出和敬業鼓起了掌。
從內蒙萬水泉-太原-臨汾的兩段火車,我坐了一天半多,除了喝點熱水外,幾乎沒有吃飯。坐在對面的一個叔叔級的人看到我中飯和晚飯都不吃,直勸我吃點東西別餓着肚子。他哪裡知道,我買完火車票後沒有剩下多少錢,到爸爸媽媽家之前不知道還需要多少費用,我得節省着花呀!
我的逃跑決定完全是自作主張,從來沒有和家裡說過,給爸爸媽媽來了個措手不及。當我逃跑回到山西臨汾後,爸爸怕組織上說他破壞「上山下鄉運動」,就給連隊寫了一封信說要把我送回去,不過信中說我剛回家,讓我在家住幾天再回連隊。連長在晚點名時,給全連讀了我爸爸的信。連長以此為鑒奉勸大家不要逃跑了,跑回去也會被革命的英雄的父母們送回來。
要不是同班的胡陵秋寫信告訴我這些,我都不知道我爸要送我回去。陵秋囑咐我千萬別回去,如果回去就白跑了,以後就更不好回家了,還用了好幾個驚嘆號??為此,我一直很感激陵秋給我通風報信。我看了陵秋的信就去問我媽媽,是不是爸爸要把我送回內蒙?得到媽媽的確認後,我傻眼了。我不敢找爸爸說,就趴在媽媽後背上一邊搖她一邊求着:媽媽呀,別把我送回去啦……我媽當時坐在小板凳上摘菜,她那小個子哪裡經得住我的體重。媽媽快透不過氣來,讓我趕緊起來,並答應我去做爸爸的工作。後來媽媽告訴我說爸爸同意啦!歐耶?我又打了一個漂亮仗!
以後,爸爸沒有再提送我回兵團的事情,而且在生活上還特別關照我。由於媽媽回北京照顧我大姐和外孫,捎帶着找軍科院領導安排我當兵的事。家裡剩下我和爸爸、弟弟一起生活,弟弟上中學,家務活我全包了,爸爸也感到我在身邊的重要。記得當我生病時,爸爸會把一天三頓吃的葯一粒一粒給我拿出來放在桌子上,倒好一杯水催促我該吃藥啦,直到我病好為止。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爸爸如此對待哥哥姐姐和弟弟們,讓我感受到了爸爸的慈愛和親人相依為命的滋味。

我又要離開家當兵去了。上面的哥哥姐姐當兵時,爸爸都沒有把他們送出過家門口,唯獨我當兵時,爸爸拖着那條負過傷的腿,和弟弟一起從臨汾休養所走到火車站。因為是偷偷送我去當兵,爸爸不敢張揚,更不敢找休養所要車。而且,我們選擇晚上的火車,趁着天黑悄悄地走了。
自此,16歲的我又踏上了一個人的旅程,從臨汾到西安再轉車去往蘭州參軍。結束了我屯墾戍邊的兵團戰士身份,成為了一名真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從而實現了我 的人生轉折,實現了我小學時就立下的志向和夢想。

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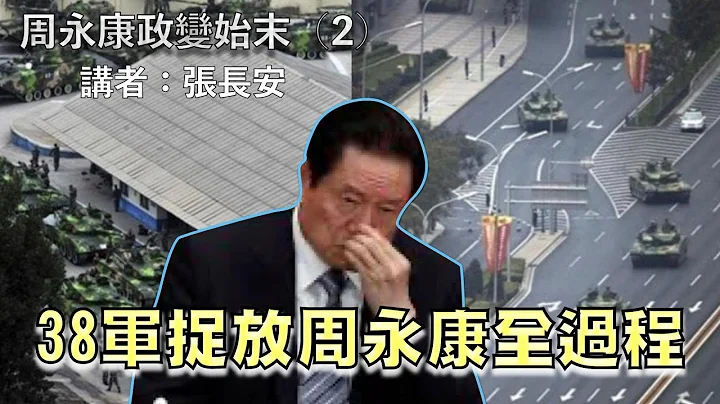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