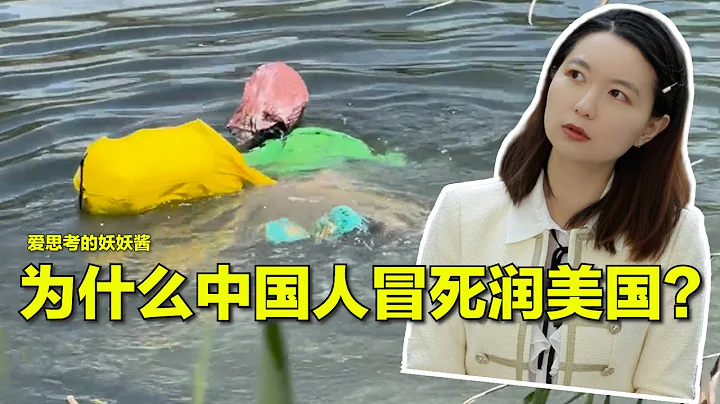38年前的今天,1984年11月2日,斯大林的女兒,在逃離蘇聯17年後,從美國返回蘇聯。

一、女兒
斯維特蘭娜,斯大林的唯一女兒,1926年出生後,父親給她起了這個名字。
其來源,是俄羅斯一首浪漫主義詩歌,「光影」之意。
她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十分受寵愛。
「她喜歡把我放膝頭,緊緊擁抱我。」

(斯維特蘭娜與父親)
「小麻雀」「小東西」「女主人」「第一號秘書」……都是父親對她的愛稱。
作為外人畏懼的領導人,在家中他甚至允許小「女主人」給自己發命令:
「我的第一秘書斯大林同志,命令你允許我和你一道去看電影或者看戲。女主人謝坦卡(斯維特蘭娜的昵稱)。」
「遵命,馬上就完成任務!」
親子遊戲,暖如常人。
斯維特蘭娜晚年回憶,她的童年是幸福的,「不論從哪方面來說,都可以說是住在天堂。」
6歲時,她人生中的第一個不幸來臨,她年輕的母親自殺身亡了。
童年的天堂,漸漸遠去。
10歲時,她穿了一件不到膝蓋的連衣裙,被父親凶吵了一頓。
在喬治亞的老年人看來,短裙子、短襪、短袖,都是不可接受的。
女兒年齡的增長,讓她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堅持。在父親看來,女兒越來越有主見了,也沒有兒時那般聽話、可愛了。
這令她與父親越來越遠。

16歲,她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時,與一個40歲的電影導演戀愛。
當父親的警衛發現了她與那個男人的不體面的事後,激怒的父親打了她一巴掌:
「現在戰爭都打成這樣,你卻干出這事……他身邊有那麼多的女人, 你是個糊塗蟲!」
父親不加掩飾的嚴厲,深深傷害了她的感情。從此,她不再留戀這份父愛。
2年後,她與一個同校大學生結婚,不過,令父親仍然不可接受的是,那男生是個猶太人。
翌年得子,父親也沒接受他們。甚至,始終沒有讓這個女婿進家門。
1947年,21歲的斯維特蘭娜與丈夫關係破裂。2年後,依父之見,與一個官員的兒子結婚,翌年生女。
1952年,26歲斯維特蘭娜再次離婚,父親給了她一棟別墅,她帶著子女單獨生活。
翌年,父親死後,斯維特蘭娜感覺沒有人再干涉自己的生活了,但好景不長,她生活並不如意,尤其在婚姻家庭方面。

二、出逃
1957年,斯維特蘭娜改隨母親姓氏,又過了幾年,她接受了東正教的洗禮,從此「不心懷上帝就不能生活」。
她開始寫書,《致友人的20封信》里,稱自己「渡過了37年愚蠢的、無意義的雙重生活」。
那一年,他在醫院偶遇了一個到莫斯科治病的印度人,叫辛格,兩人一見鍾情。
這是她的第4個男人。
她想與他結婚,但被有關部門阻止,說這個人比她大17歲,還一身病,即便她父親在,也不會允許她與一個外國人結婚。

(與第一任丈夫)
父親去世13年了,她還是不能實現自己的自由生活。斯維特蘭娜十分絕望,她開始消極避世,離開了工作單位,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史研究所。
與辛格同居一年多後,辛格去世,她再次寡居。
1966年,她向國家申請出國,稱要把辛格的骨灰送到印度去。
政府批准了,給了她兩周的簽證。
一到印度,她就想方設法不再回去。
先是給印度高官寫信,被拒後,又逃到美國駐印度大使館,請求移居蘇聯的敵對國,美國。
美國政府不敢輕易答應,以為她是頭腦發熱,先協調她去了瑞士。
一個半月後,美方有關負責人親自與她長談,斯維特蘭娜主意已決,決定「永不返回蘇聯」了。
1967年4月21日,她終於如願以償,坐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
此時,她的一兒一女仍在國內。
這個消息震驚國際。
蘇聯人指責她對不起死去的父親,更被判了祖國。

一到美國,斯維特蘭娜就是個名人:出書、接受媒體採訪,揭露克里姆林宮的內幕。
美國的目的很明顯,之所以熱心接收她,就是為了利用她,利用這個絕對稀有的內部人士,來批評、揭露、攻擊蘇聯制度。
她的書在美國暢銷,有人估算,光憑出書,她就有好幾百萬美元的收入。
還不說她被聘為俄國問題專家,要房有房,要車有車。
對斯維特蘭娜來說,真乃理想中的另一個「天堂」。
1969年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對她不再抱任何希望,決定剝奪她的公民權。
在美國,斯維特蘭娜與一個美國建築商認識3周後,閃電結婚。
44歲的她,再次組建家庭。
然而,在美國真正獲得無拘無束的生活後,斯維特蘭娜卻暴露了自己的缺點。

比如,她並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甚至無法經營好自己的婚姻家庭。
在與美國丈夫生下一個女兒的8個月後,她便帶女兒,離開了丈夫,開始獨自生活。
比如,她並不善於理財。
很快,她發現自己的錢並不夠。
出書賺的500萬美元,大部分被出版商、經紀人、律師、丈夫划走了,自己只得了100餘萬,還要替丈夫還債……
1978年,來美國12年後,斯維特蘭娜終於取得了美國國籍。
之後,她改名叫「蘭娜·彼得斯」,與自己的過去徹底割裂。
三、回國
斯維特蘭娜在美國生活十多年後,對美國也越來越失望,「過去,我從來沒意識到兩個超級大國是如此之相似,無論好的,還是壞的方面。」
她不想被媒體和出版商綁架,所以帶著女兒又移居到了英國。
只想在那裡安安靜靜地著書立說,「過個清凈的生活」。

一天,在劍橋,她突然接到在蘇聯的兒子打來的電話,這是她17年來,第一次聽到兒子的聲音。
電話里,兒子勸她「回來吧媽媽,我們需要你」。
感情的波瀾瞬時潰堤,感性再一次戰勝理性,她決意立馬回去。
1984年11月2日,斯維特蘭娜帶著13歲的小女兒,回到了闊別17年的蘇聯。
雖然她在美國大肆「揭秘」攻擊蘇聯,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仍然立即為她恢復了國籍。
此時的她,經歷了無數新聞媒體的追逐,十分厭倦在公共場合露面,只想平靜生活。
但這一次,她必須面對媒體。
她決定這是她最後一次接受採訪,所以說了許多真心話,然後告訴記者,以後請不要打擾我了。

■談及回國原因,她說,主要是十分想念留在國內的兒女。
她說,為了自己在美國的所謂的自由生活,自己做出了最大的犧牲,「失去了一雙兒女」。
17年來,他們不能通信、不能打電話,自己連10歲孫子的照片都沒有見過。
如果不回國,可能與他們「永世不得相見」。
■談到美國自由世界,她說令人感到失望。
起初,她把西方自由世界想得太美好,過於理想化,沉醉在興奮和自己的滿足之中。
但後來,她就明白現實是怎麼一回事了。「在許多方面都太令人失望了。」
她說,自己被局限在少數幾個蘇聯問題專家和俄國歷史學家的圈子裡,後來便不再受人歡迎,「處在一種虛情假意之中」。
「美國國務院在說謊方面,絕不比克里姆林宮遜色。」
而蘇聯也有好的方面,比如,「千百萬人在享受著免費的教育,人人有機會進入高等學府,大家都享受著公費醫療,你不能否認這對於人民來說是改善。」

■談及自己當年的「叛逃」,她用自己17年的海外經歷,給世人發出了一句振聾發聵的提醒:
「沒有一個變節者是完全自由的。」
「我今天要對所有潛伏的變節者說,不要忘記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類,他們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悶的、無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們所離棄的那些人。
「我十七年前所不懂的,就是兩個超級大國在好的和壞的方面竟是這樣相像。」

斯維特蘭娜的回歸,完全是情感需要,而絲毫與政治無關。
但是,不幸的是,她再一次夙願未成。
此時,經歷諸多政治風波的女兒,對她當年的離去,始終不可原諒。
即便她現在成了寡婦,帶著孩子艱難生活,也拒絕同回國的母親見面。
倔強的女兒,同母親一樣不輕易原諒雙親。
她寧願自己寫信給母親,也拒絕與她相見。
這對一個年近花甲、渴望彌補母愛的母親來說,是多麼大的打擊。

再說兒子。
斯維特蘭娜的兒子,由於酗酒,精神、身體都不好,年紀輕輕就未老先衰。
最頭疼的,是自己帶回來的13歲的小女兒。
她從小受西方教育,不會說俄語,不懂蘇聯歷史,信仰的是基督教,堅決不願意把脖子里的耶穌像摘下來。
而這,讓她無法在莫斯科接受教育。
生活上,自己與前夫所生的兩個孩子,和小女兒也互不融入。
斯維特蘭娜心力交瘁。
原來,家庭這場大戲,比政治更難。

堅持了1年後,斯維特蘭娜給戈爾巴喬夫寫信,失望地說,自己沒有實現當初回國的目的,「一家人無法團圓,沒有理由再待下去。」
1988年4月,蘇聯再次發出政令,同意斯維特蘭娜放棄蘇聯國籍。
她再次回到美國,隱居在威斯康辛州南部城市。
由於不善理財,晚年的她,生活相當窘迫。
2011年11月22日,85歲的她因大腸癌在威斯康辛州去世。

總結:
1️⃣ 「女兒是父母的小棉襖」,那是尋常倫理,政治人物的家庭,往往不尋常;
2️⃣ 父親的話,在許多時候都是對的,雖然他有時候不近情理,但對孩子,絕對目光如炬;
3️⃣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自由,理想永遠與現實有錯位,想靠潤學拯救自己的,請記住斯維特蘭娜17年悟出的真理:
「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類。」
(完)
參考資料:
●環球網,《斯維特蘭娜的悲慘結局:父親斯大林毀了我的一生》,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GDgr
●《克里姆林宮的兒女們》,(俄)B.C.克拉斯科娃著、徐昌漢譯,北方文藝出版社 , 1998.01
●《斯大林女兒的曲折人生》,王正泉,《百年潮》 2008-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