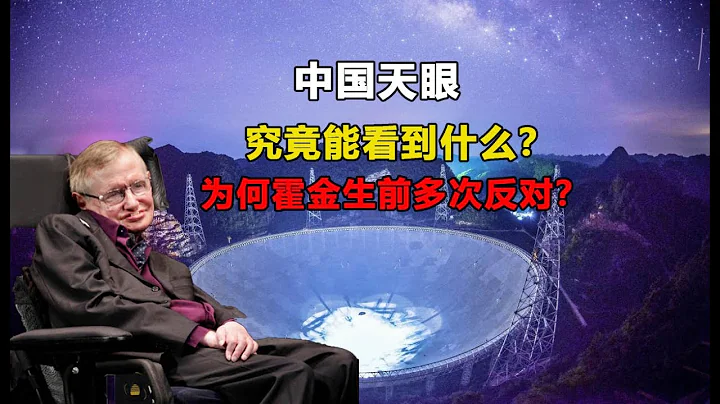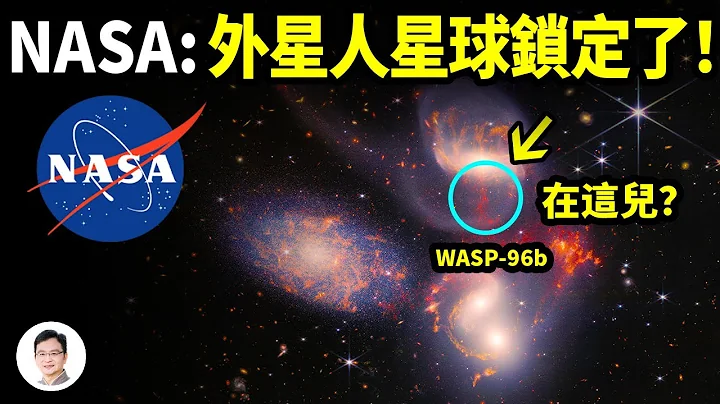歐洲望遠鏡是否在明代由利瑪竇傳入中國,在學術界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許多學者以1609年伽利略創製天文望遠鏡,來否認明人鄭仲夔「利瑪竇有千里鏡」之說,從而導致望遠鏡傳華認識上的種種誤區。然而,大量文獻證實,鄭仲夔所記是信史。其一,根據日本早期文獻《大內義隆記》《南蠻寺興廢記》《長崎實錄大成》《顯承述略》記載,望遠鏡在16世紀中葉的歐洲發明以後,傳教士很快就將其帶到了日本,那麼,對處在同一條航線上的澳門來說,萬曆九年(1581)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經澳門將望遠鏡帶進中國是完全可能的。其二,在漢文文獻中,鄭仲夔說利瑪竇帶望遠鏡入華並非一家之言,這可以從多種明末清初的文獻記載獲得旁證。例如,陸應揚的《廣輿記》、劉侗的《帝京景物略》、花村看行侍者的《談往》、單隆周的《希姓補》、王夫之的《思問錄》等等。其三,從利瑪竇的著述中,也可以證明他攜帶望遠鏡入華。例如,他撰寫的中文著作《理法器撮要》中,曾三次提到望遠鏡。尤其是在浙江省圖書館最新發現的署名為「太西利瑪竇傳,松江徐光啟校」的《開成紀要》抄本,詳細介紹瞭望遠鏡的製造方法和過程。從書中的文字和內容看,屬於初步完成的文稿,尚未經過考訂審核,所以是以未刊抄本的形式保存下來的。其四,利瑪竇不僅帶進望遠鏡,還能能製造望遠鏡,並且翻譯介紹過製造望遠鏡工藝方法的文章。這在明末時人孫承澤的《春明夢余錄》、毛奇齡的《西河集》、吳肅公的《明語林》、諸升的《〈鏡史〉小引》中都有記錄。所以,可以確定地說,在明代的中西科學文化技術交流史中,利瑪竇當是第一位將望遠鏡製造技術傳入中國的歐洲人。他與他同時代的歐洲傳教士不僅將望遠鏡帶進了中國,而且在耶穌會中國傳教團傳教政策的指引下,為了明朝宮廷修歷的需要,還製作了一批望遠鏡,而這些望遠鏡在明代社會已經得到廣泛傳播。

△利瑪竇(1552–1610)
關於歐洲望遠鏡製造技術在中國明清時期的傳播,已有不少論著發表,但因以往研究對中西文獻檔案的搜集有遺漏,導致研究者對望遠鏡傳華問題出現分歧。特別是大部分學者以1609年伽利略(G. Galilei,1564–1642)創製天文望遠鏡來否認明人鄭仲夔「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之說,進而成為利瑪竇研究乃至中國科技史上長期存在的誤區。本文擬在全面搜集中文文獻的基礎上,利用同時代的葡文、日文文獻,特別是最新發現的利瑪竇《開成紀要》等一批新資料,考證明代利瑪竇(M. Ricci,1552–1610)不僅帶望遠鏡入華,而且還能製造望遠鏡,希望在對中國科技史糾錯的同時,也能對利瑪竇研究有一個推動。
一 不能用伽利略發明天文望遠鏡來否認「利瑪竇有千里鏡」
在明代文獻中,明確記錄利瑪竇帶望遠鏡來華的是鄭仲夔。他在《玉麈新譚·耳新》稱: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視天上星體,皆極大;以視月,其大不可紀;以視天河,則眾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1942年,方豪在重慶《益世報》發表文章,否認了鄭仲夔這一記錄。其理由是:
然瑪竇卒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一年前,伽利略始在物尼斯製成第一架望遠鏡,瑪竇決不能及身而見也。蓋爾時國人極崇拜利瑪竇,故凡聞一異說,見一奇器,必以為瑪竇所創。《耳新》僅一例也。
1969年,《方豪六十自定稿》出版,收錄了《伽利略與科學傳入我國之關係》一文,再次重申了上述觀點。當然,在此之前,耶穌會士陽瑪諾(E. D. Junior,1574—1659)於1615年在中國出版《天問略》一書時,曾介紹了伽利略發明望遠鏡一事,並稱「待此器(望遠鏡)至中國之日,而後詳言其妙用也」,也認為在1615年之前,伽利略的天文望遠鏡還沒有進入中國。因此,餘三樂在他的關於望遠鏡的專著中也持與方豪相同的意見:
因為當1608年荷蘭眼鏡商人向政府申請專利的時候,利瑪竇已經在中國生活了26年,離開歐洲也已經30年了。雖然他即使在中國也有可能從通信中、從後來來華的同伴中得知他來華以後歐洲發生的事情,也可能間接地得到來自歐洲的書籍和自鳴鐘,但是,他卻不太可能知道望遠鏡,更不可能得到望遠鏡。因為這時離他1610年5月去世,僅僅只有一年多的時間了。
不能否認,方豪、餘三樂的說法具有他們的科學邏輯和道理,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鄭仲夔的《耳新》一書並沒有稱利瑪竇所攜帶的千里鏡是伽利略製造的天文望遠鏡,而望遠鏡的製造又並非自伽利略始。所以,上述批評不足以否定鄭仲夔的說法。
科學史家江曉原是支持利瑪竇攜帶望遠鏡進入中國之說的重要學者,認為儘管在當時的耶穌會中文著作中,不管是1615年陽瑪諾的《天問略》、1626年湯若望(J. A. S. v. Bell,1592–1666)的《遠鏡說》,還是1634年由湯若望等士人編纂的《崇禎曆書·五緯歷指》,都是將望遠鏡的發明權歸於伽利略,但在望遠鏡發明權中,學術界提到最早的望遠鏡發明者則是英國人迦斯空,如晚清學者王韜(1828–1897)與傳教士偉烈亞力(A. Wylie,1815–1887)合譯《西國天學源流》一書就談到16世紀的望遠鏡:
伽利略未生時,英國人迦斯空已用望遠鏡於象限儀。迦斯空死後二十餘年,無人知用者,而法蘭西有某者造之,誇為創事,且造分厘二器,亦無傳,而伽利略復為之,冠遠鏡諸器。
義大利人玻爾塔(G. B. D. Porta,1532–1602)1589年出版的《自然的魔術》書中稱:
用一塊凸透鏡,近旁的東西顯得特別大,卻更模糊。如果你知道如何將它們配置在一起,你既可以看到近旁的東西,又可以看到遠處的東西,並且在兩種情況下,看到的東西都是大而清楚的。我說的就是托勒密透鏡,或就叫眼鏡,利用這種透鏡,托勒密看到60英里外進犯的敵船。
英國人倫納德·迪格斯(L. Diggses,1515–1559)也是16世紀望遠鏡的發明者,他的兒子托馬斯·迪格斯(T. Diggses,1546–1595)留下了一份詳細的望遠鏡使用說明,並在1571年為其父的著作《經緯萬能測角儀》所作的序言中稱:「望遠鏡發明者的榮譽是屬於父親倫納德·迪格斯的。」《望遠鏡的歷史》一書中還寫到:
波爾塔在1586年致信樞機主教埃斯泰宣稱,他的《自然的魔術》中已經明確說明自己能製造「眼鏡(occhiali)」,通過它也可以看見數里之外的人。
研究中國科技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N.J.T.M. Needham,1900–1995)則稱:
可以肯定的是,在1550–1610年至少有六個人擺弄過雙透鏡的組合,使用了雙凸透鏡和雙凹透鏡,並獲得了令人驚訝的遠處物體放大的效果。某一種設想一傳播開來,就許多人幾乎同時付諸實踐,這種現象,如望遠鏡的發明,在現代以前幾乎是不可能的。
稍後,1612年11月2日,作為時常與中國耶穌會士通信的義大利耶穌會神父魯比諾(G. A. Rubino,1578–1643)曾在信中寫到:
一些人從義大利寫信告訴我,一種眼鏡被製造出來,可以看清楚15–20里外的東西。
貝克曼(I.Beckman,1588–1637)在1634年提到:
詹森(Z. Jansen,1585–1632)於1604年在荷蘭製造了第一架望遠鏡,他所依據的原型是1590年在義大利製成的。
以上多種西方文獻均可以說明,在16世紀後半葉及17世紀初葉,已有人發明了用雙透鏡組合的望遠工具,並運用到實踐中。這種望遠工具已經具有將遠處物體放大的效果,並且能看到六十英里外進犯的敵船。這種望遠工具就被稱為「望遠鏡」,中國人則稱之為「千里鏡」。也就是說,在伽利略發明創製天文望遠鏡之前,具有望遠功能的千里鏡早已在世間出現。
雖然按照教科書的說法,望遠鏡是在1608年,由荷蘭米德爾堡的眼鏡商利伯希(H. Lippershey,1570–1619)發明的,後由當時的著名學者開普勒(J. Kepler,1571–1630)加以改進,並設計了幾種新的望遠鏡,特別是用兩塊凸鏡片的天文望遠鏡。1609年,伽利略又製造了一架能放大九倍的望遠鏡,開始了對天空的觀察,創造了真正意義上的天文望遠鏡。《疇人傳四編》卷九稱:
伽利略,萬曆三十七年(1609)至威尼斯,適刻白爾論火星之書初出,偶與人談論,忽悟遠鏡之根,時聞荷蘭人造器能測遠,因思仿此作測天之器,遂以精思造成之。旣成,自言視物大一千倍,近三十餘倍。
伽利略也稱,他是聽到荷蘭人造望遠鏡之後才造的這架天文望遠鏡。但是,伽利略所發明製作的天文望遠鏡距望遠鏡的最早問世接近有半個世紀,在這一時間段里,望遠鏡已經被人們付諸各種實踐活動。然而,耶穌會傳教士為了其科學傳教的需要,在介紹望遠鏡發明和創製的時候,一般都祗提到伽利略,而不提及其他。所以,人們都是以伽利略發明天文望遠鏡的時間來界定望遠鏡始傳中國的時間,這就帶來了人們對望遠鏡傳華問題認識的誤差。
自16世紀中葉望遠鏡發明以後,望遠鏡就開始向東方傳播。據後奈良時代(1497–1557)的日本文獻《大內義隆記》稱:
都督在世之時,石見國太田郡發現銀山。外國聞日本發現寶山,便有無數唐土、天竺、高麗等國船隻渡來。天竺人所贈送的各種物品中,有晝夜長短分毫不差的司掌十二時之物,能發出鐘聲及未裝十三根琴弦卻能發出五調子十調子,能使老花眼看得清楚的鏡子及能清楚看清遠方的鏡子共有兩面獻上。
這裡所指的「天竺人」應指來自印度果阿的葡萄牙人或者是傳教士,「能清楚看清遠方的鏡子」即指望遠鏡。19世紀日本教會學者山本秀煌的《日本基督教史》稱:從印度來的外國人給山口的領主大內義隆獻上了「葡印總督的信函及洋琴、時鐘、遠眼鏡及裝裱美麗的書籍」。法國學者雅克•布洛斯稱,沙勿略(F.Xavier,1506–1552)於1549年抵達日本山口時,「向日本的大名奉送一座鐘,一些望遠鏡,一架斯頻耐琴」。明治時期日本文獻《增訂工藝志料》解釋望遠鏡傳日時亦稱:
後奈良天皇之治世,有天竺人來到周防國山口館,因向周防國主大內義隆獻上眼鏡及望遠鏡,而獲讚賞。由此,本邦之人始知眼鏡及望遠鏡之存在。
由上可以反映出,在後奈良時代,西班牙傳教士沙勿略抵達日本時,就將望遠鏡帶入了日本。又據《南蠻寺興廢記》載:
異國人到達江州安土城下後,令其至妙法寺休息三日。九月三日,召入城中,謁見信長。伴天連身穿神父之服,如毛氈般,裾短袖長,於左前扣合,與其體相甚,如蝙蝠展翅。賤聲如鴿鳴,所言不明。最有失體統之事,乃懷抱名香,於御殿熏之。對信長行禮,兩臑指尖向前伸出,再兩手交叉於胸前,仰頭。誠為不可思議之禮式。所獻之物七種:可遠觀七十五里的望遠鏡,可觀芥子如雞蛋的放大鏡,猛虎皮五十張,毛氈約五町四方,鐵炮伽羅百斤,八迭蚊帳,一寸八分的香筥,內裝四十二粒紫金制數珠。
此事又見於《長崎實錄大成》:
天正二年甲戌,大君織田信長命老臣菅谷九右衛門長賴,召伴天連烏而革莫。烏而革莫獻烏銃十、遠近鏡、盈縮帳各一,猩緋罽、藥物等種種珍玩。信長親問航海之由,烏而革莫曰:無他。天主之道,寰宇最上之教,願傳之貴邦。信長館之城外,餼稟至盛。
非常清楚,這裡的「遠近鏡」應該就是望遠鏡。這一次獻望遠鏡的時間是天正二年(1574)。又據日本明治時代學者萩原裕好問的《顯承述略》記載:
天正二年甲戌,參議織田信長命菅谷長賴,召拔的廉教會法長曰:拔的廉法徒曰維曼長賴,乃矯將軍教旨,致之京師龍造寺。隆信遣人護送,信長要諸途使至安土。被服奇偉,形若蝙蝠張翅,獻緋絨、火器、望遠鏡諸珍。
據此可知,天正二年時,歐洲傳教士給日本大名織田信長(1534–1582)進獻瞭望遠鏡。
根據上述多種日本早期文獻說明,16世紀中葉望遠鏡在歐洲發明以後,傳教士很快就將其傳到了日本。既然16世紀中葉望遠鏡發明後不久就傳到了日本,而澳門與日本處在同一條航線上,大多數傳教士是經澳門進入中國的,那麼,這一時期是否有望遠鏡傳進中國呢?我們根據下面的兩條材料也可以看出大約在望遠鏡傳進日本的同時,這一西洋奇器也傳進了中國內地。刊刻於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的范泓的《典籍便覽》一書中記載:
千里鏡:有估客貨一鏡,須千金。王文正公曰:鏡有何異?客曰:能照千里。公曰:吾面不臻樣子大,烏用照千里哉。遂卻之。
從這條材料可以看出,千里鏡在萬曆三十一年之前已經進入中國內地,並有商人出售,且售價千金。還有,清人沈季友編纂的《檇李詩系》收錄有趙世顯《題任氏貞節卷》詩:
自苦冰霜操,那知歲月深。塵埋千里鏡,腸斷五弦琴。亹亹丸熊意,凄凄化石心。共姜嗟已矣,攬卷一沾襟。
趙世顯,「字仁甫,福建人,萬曆初嘉善學訓」。這一條資料告訴我們,萬曆初年,在浙江嘉善縣擔任教諭的趙世顯在他悼念任氏的貞節情操時,提到了「千里鏡」,而且這個「千里鏡」在詩中與「五弦琴」相對應,可知此千里鏡即應是望遠鏡,亦可證在萬曆初年有望遠鏡已經傳入浙江地區。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條望遠鏡傳入中國內地時間與利瑪竇來華的時間大約都在同一時期,因此,萬曆九年(1581)來華的利瑪竇完全有可能將望遠鏡帶進中國。這裡有必要說明的是,上述所說的望遠鏡都是指普通望遠鏡,而不是指伽利略發明的天文望遠鏡。所以,以1609年伽利略發明天文望遠鏡為標準來判斷利瑪竇是否帶望遠鏡來華的觀點是完全不可取的。
二 鄭仲夔所記「利瑪竇有千里鏡」當為信史
否認「利瑪竇有千里鏡」的學者均將鄭仲夔的記錄當作坊間異說、民間傳奇,屬小說家類,不可徵信。因此,接下來就有必要介紹鄭仲夔其人及《玉麈新譚》其書。
鄭仲夔,字胄師,又字龍如,江西信州人,生卒年不詳,從他著作年份來看,應該是與利瑪竇同時代人。鄭仲夔雖然終身未仕,但學術名望很高,他的朋友楊觀吉稱他「胄師名如轟雷閃電,不可得而掩」。據《玉麈新譚·清言》之曹徵庸序,該序作於「萬曆丁巳」,即萬曆四十五年(1617)。《清言》一書在當時深受學界稱許,有「《清言》之核,期以示的於千古」之稱。而完成《清言》的時間是1617年,距利瑪竇去世的時間僅七年。而鄭仲夔又是江西人,在他生活的年代,有可能在江西見過利瑪竇,或者至少聽說過利瑪竇的傳聞。而《玉麈新譚·耳新》一書則完成於崇禎甲戌年(1634),是一部被鄭仲夔自譽為信史的史學著作。
據《耳新》鄭仲夔自序稱:
余少賤,躭奇南北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之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遯而湮沒也。隨聞而隨筆之,書成行世且久,而並取詳加訂焉,以是為可以質今而准後也。庶幾,竊比於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為孟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哉。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胄師父題
從鄭仲夔的自序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一)自序完成的時間是崇禎甲戌年,但寫序時此書已「書成行世且久」,說明《耳新》寫作的時間可能就在萬曆、天啟之間,不然,很難說「行世且久」。而且,他還明確說《耳新》中所記錄的事情是他年輕時候聽到的事情,所以,他所記錄的「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有可能是利瑪竇在世時或利瑪竇剛逝世時的記錄。
(二)該書所記錄的事實都是他親自「隨聞而隨筆之」,即他當時聽到的事情就在當時記錄下了;而且在書成之後「並取詳加訂焉」,說明他對其所記錄的事情極為認真,每一件事情都進行了考訂。
(三)鄭仲夔在序中自比漢朝劉歆(字子駿,前50–23),班固修《漢書》多取材於劉歆之書,故希望自己也成為班固(字孟堅,32–92)、王世貞(字元美,1526–1590)一樣的良史。他還稱,他撰修《耳新》一書,希望能成為傳世的信史,並「可以質今而准後也」。
鑒於以上三點,如果後人沒有足夠的證據,是不可以將這麼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中所記錄的歷史事實輕易加以否認的。
我們再對鄭仲夔《玉麈新譚·耳新》所記錄利瑪竇傳入望遠鏡之史文進行討論。其中,鄭氏所使用的「番僧」一詞需認真考辨:
「番僧」是華人對早期入華西方傳教士的一個普遍稱呼,因為他們本身就將自己稱之為「西僧」或「天竺僧」,中國人及傳教士都將西士視之為外國的和尚。雖然1594年年底,在范禮安(A. Valignano,1539–1606)的指令下開始易服改名,傳教士不再是僧人、和尚的形象,而是以讀書人或儒士的身份出現。據《利瑪竇信函》記錄:
我們已經考慮放棄中國人藐視的和尚(bonzos)的名稱,並採用巡查使神父允準的文人(letrados)的稱謂,我們留須並蓄髪至耳,穿上文人互相拜訪時所穿的特別服裝,而不再是過去的和尚打扮。
雖然利瑪竇離開韶州以後就已經改變了過去和尚、僧人的形象,且以儒士、文人相稱,但是,人們並沒有按照他們形象的改變而改變對他們的稱呼。《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稱:
至於稱呼問題,雖然我們自己家裡人和許多朋友都用我們的新稱謂來稱呼我們,可要在廣東全省推廣這種稱謂是極為困難的,因為中國人無論是世俗的,還是信教的,都以「僧」來稱呼所有離俗出家之人。同樣,他們也以此稱謂稱呼所有澳門的教士。
所以,當利瑪竇等人於1595年來到南昌以後,當地人仍稱他們為「番僧」。例如,在南昌曾與利瑪竇有所交往的江西鉛山人費元祿即稱:
番僧琍瑪竇,狀貌魁岸奇偉,自天主國航海入廣東韶州,歷居吳越、豫章,年可五十餘,後蓄髪,通中國語,所習經典法物及天主像極精緻。
又如,與利瑪竇有著深刻交往的江西著名學者章潢亦將利瑪竇稱為僧人:
前十餘載,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為九瓣。
遍檢明代中文資料,稱利瑪竇為「番僧」者祗有三人,一是章潢,二是費元祿,第三個就是鄭仲夔。有趣的是,此三人均為江西人。這反映出,利瑪竇到南昌以後,江西人普遍以「番僧」之名稱呼利瑪竇。而鄭仲夔不僅在《玉麈新譚·耳新》一書中稱利瑪竇為「番僧」,在他的另一本書中,《玉麈新譚·雋區》仍將利瑪竇稱之為「番僧」:
世人漫結交,遂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相知。試繹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以友為第二我,此深於相知之解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提到的「利瑪竇以友為第二我」指的就是利瑪竇的著作《交友論》,而《交友論》就是利瑪竇到南昌後於1595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番僧」一詞是南昌時期當地人對利瑪竇的習慣稱呼,而《交友論》也是於1595年在南昌出版的利瑪竇著作,以此推估,「番僧」應該是明萬曆時期江西南昌人對利瑪竇的一個普遍稱呼。故鄭仲夔所見或所聞「利瑪竇有千里鏡」之說仍採用了將萬曆時期江西南昌人對利瑪竇的稱呼為「番僧」,亦可證鄭仲夔所記錄「利瑪竇有千里鏡」之史文應是產生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中。
前引鄭仲夔《玉麈新譚·耳新》稱:「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這裡至少又有三個名詞需要進行考證:
(一)「其徒」。中文文獻多將在利瑪竇以後入華的傳教士稱之為「利瑪竇之徒」,如明人陳龍正稱利瑪竇:「未幾病卒。其徒眾,僅能傳習其器算,而穎慧莫之逮也。」談遷亦稱:「利瑪竇航西海二年達廣南,今其徒不絶,抑皆自歐邏巴而至者乎?」據此可以看出,所謂「其徒」,就是指繼利瑪竇以後入華的西方傳教士。
(二)「道人」。明代人對當時傳教士的一種稱呼。例如,馮時可即稱利瑪竇為「外國道人」,陳龍正亦稱利瑪竇為「利道人」。「其徒某道人」,意為繼利瑪竇入華以後的傳教士某人。據此可知,這個「道人」並非一般中文書上所指的中國的道士,而是指當時西方來華天主教傳教會的修道之人。
(三)「南州」。雖然南方地區廣義之稱為南州,甚至河南的南陽、福建的漳泉及蜀中之地也有「南州」之稱,但通常人們所說的南州均是指古豫章郡即南昌。東漢時期的名士徐稺,又稱徐孺子,為豫章郡人,曾屢次被朝廷及地方徵召,終未出仕,世稱「南州高士」,故後人多以豫章(南昌)為南州。例如,明人曹學佺《石倉詩稿·豫章稿》「故漢豫章守陳公蕃」一詩稱:「南州徐孺子,鄉里未知賢。一朝郡太守,下車請門前。」「蘇公圃」一詩稱:「西蜀蘇公圃,南州孺子祠。盈盈兩湖水,明月照相思。」南州為明代豫章郡的代指詞,在明代的文獻中間比比皆是,鄭仲夔乃江西人,所記事多為在江西所見所聞之事,故此處的「南州」,指的應該就是豫章郡即南昌。
那麼,1610年利瑪竇去世後,「挾(千里鏡)以游南州」的究竟是哪一位傳教士呢?據何大化《遠方亞洲》記載:
由於利瑪竇神父的離世,傳教團團長一職由龍華民神父接任。龍華民神父於韶州掌管整個中國境內第二大的留居點多年。之後收到要求,讓他出發前往京城,這裡需要龍華民神父的輔助。費奇觀(Gaspar Ferreira)神父成為韶州留居點的管理神父,由最近和林斐理(Felecianoda Silva)、金尼閣一同進入中國的陽瑪諾陪同。在兩人的陪同下,龍華民神父乘船來到南雄,並從這裡下船前往江西的省會南昌。龍華民神父在這裡停留了八日,依照自己的命令處理當地傳教點的事務。
龍華民(N. Longobardi,1559–1654)在1611年離開韶州赴北京時,曾在南昌停留了八天時間,而鄭仲夔在南昌見到的攜帶望遠鏡的「某道人」正是龍華民。在南昌,龍華民不僅向人們展示他所攜帶的望遠鏡,而且還將「利瑪竇有千里鏡」的信息告訴了鄭仲夔,所以鄭仲夔記下了「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之說。
在漢文文獻中,利瑪竇帶望遠鏡入華並非孤證,這可以從多種明末清初的文獻記載獲得旁證。陸應揚《廣輿記》卷一稱:
西洋利瑪竇航海九萬里入中國,神宗命給廩賜第,堂建第左。所制有簡平儀,本名范天圖,為測驗根本。沙漏用以候時候鍾,應時自擊。龍尾車,下水可用以上。千里鏡,可視小為大,視遠若近,皆極工巧。
陸應揚為明萬曆時人,與利瑪竇同時,在他的記錄中也認為利瑪竇攜帶有望遠鏡。劉侗《帝京景物略·西城內·天主堂》也稱:
遠鏡,狀如尺許竹筍,抽而出,出五尺許,節節玻璃,眼光過此,則視小大,視遠近。候鍾,應時自擊有節。
劉侗生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卒於崇禎十一年(1638),他在利瑪竇曾住過的北京天主堂看見過利瑪竇帶來的望遠鏡。還有,生於崇禎二年(1629)、死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日本江戶初期學者中村惕齋也稱:
吾聞利夷甚慧敏,且識文字,著作頗多,其所攜來天地球圖、測量諸器、遠鏡、自鳴鐘之類,皆今世所利用也。
連明末清初時的日本人也知道利瑪竇帶來望遠鏡。自稱「花村看行侍者」的明朝遺民所著《談往·西洋來賓》亦稱:
大西洋十字架教主,利馬竇也。萬曆三十年,由廣東東嶴率其徒龐迪峨、龍化民等五六人至五羊城,轉入八閩,遞上金陵。自言來自大西洋國,路遠十萬,泛海九年。海水崇卑,有上升於天、下及於淵之髙下,亦如地之低昂。初出千里鏡、自鳴鐘,舉重演算法諸事件,較大明國賢愚萬倍。
《談往》一書記錄的主要是明朝末年的事情,該書稱利瑪竇來中國時「初出千里鏡」,可證他的記錄並非抄自鄭仲夔,而自有所源。明末清初浙江蕭山人單隆周也有記錄:「利瑪竇,番僧,有千里鏡。」單隆周將「利瑪竇有千里鏡」之事載入了清初一本姓氏學的書籍,可見這一事實在民間流傳之廣。明末清初王夫之《思問錄·外篇》亦稱:
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為九萬里。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著名史學家,更提出利瑪竇利用望遠鏡觀察天文大地,與鄭氏「利瑪竇有千里鏡」之說相互印證。
綜上所述,關於利瑪竇攜望遠鏡進入中國的種種說法,印證鄭仲夔「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這一說法的真實性。故此可知,在歷史文獻和歷史證據中,「利瑪竇有千里鏡」之說並非一家之言,亦可證明鄭仲夔《耳新》一書所記錄「利瑪竇有千里鏡」當為信史。
三 從利瑪竇的著述也可證明他攜帶望遠鏡入華
在否認利瑪竇帶望遠鏡入中國的諸說中,宋黎明也曾進行過一番考證,其稱:
《明史》等官方著述則提到他攜帶到中國或者進貢給皇帝的「方物」,但望遠鏡無跡可尋。在信函以及晚年回憶錄中,利瑪竇對於自己攜帶到中國的物品如數家珍,但也從未提到望遠鏡。利瑪竇同時代的耶穌會士從來沒有讓利瑪竇與望遠鏡發生聯繫。相反,陽瑪諾在1615年出版的《天問略》中明確說:「待此器至中國之日,而後詳言妙用也。」這意味著1615年之前中國並不存在望遠鏡。
宋黎明所說的利瑪竇在用西文撰寫的「信函以及晚年回憶錄沒有提到望遠鏡」是事實,但是,在署名為「泰西利瑪竇」撰寫的中文著作《理法器撮要》中,卻三次提到望遠鏡。其文稱:
天體:天體渾圓,包乎地外,周旋無端。其形渾渾,元氣充塞,圍注地心,而地乃得懸空而不偏墜。西士航海,以遠鏡望之,則見天體稜層凹凸,堅而且輕……
七曜形體大小:日輪大於地球一百六十倍八之三。嘗以遠鏡測,見其出沒時,體不甚圓,形如卵,邊如鋸齒,其面有浮游黑點,大小不一……
火星大於地半倍。水星小於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此二星之形體,遠鏡中望之,亦祗此樣,別無所見。
這不僅說明利瑪竇有望遠鏡,而且可以證明利瑪竇曾用望遠鏡觀察天體。
《理法器撮要》凡三卷,是一部介紹歐洲宇宙論和天體測量方法的一部提要性著作,既未收入李之藻所編的《天學初函》,也未載入費賴之、徐宗澤、方豪、榮振華等中西學者所著錄的利瑪竇有關書目,目前僅見一抄本,題作「明泰西利瑪竇傳」,末附署名「求自樓主人」的一則短跋。考「求自樓主人」,當為清乾隆年間官刑部郎中的蔣楫。蔣楫,字濟川,號方槎,江蘇蘇州人,乾隆六年(1741)捐修長洲縣學,乾隆十四年(1749)捐建吳縣御道。乾隆時,蔣楫購得明朝大學士申時行(1535–1614)的舊宅建「環秀山莊」,並在庄內建「求自樓」,遂號「求自樓主人」。他在後跋中稱,乾隆「戊寅(1758)初夏,借得汲古閣毛氏抄本,因令胥抄錄一通」。「汲古閣毛氏抄本」應該指的是明末時期的抄本,因為毛氏藏書入清以後陸續散出。毛晉死後,其子毛扆言:「先君藏書,自經分析,二十年之內,散為雲煙。」可見,蔣楫所借的毛氏抄本應為明末抄本,但朱維錚教授在公開這一著作時,並沒有公布此抄本的來源。然而,根據抄本顯示的內容來看,此書應不是利瑪竇的原作。現今有學者稱此書為偽書,並稱《理法器撮要》卷二全部內容均抄自梅文鼎(1633–1721)的相關著作,故作為一個整體,此抄本明顯完成於梅文鼎之後。此二文都是採用科學史比對的辦法得出的結論,雖然很有說服力,但根據《理法器撮要》書後附有「求自樓主人自識」稱:
右書三卷,圖注精詳,詮詁明確,約而不泛,簡而能明,洵天文數學家不易得之寶也。戊寅初夏,借得汲古閣毛氏抄本,因令胥抄錄一通,雖字跡繪工遠遜毛本,然大意不失,尚可見廬山面目,爰書數語藏之篋衍。求自樓主人識。
蔣楫明確說他是「借得汲古閣毛氏抄本」而抄錄的,而且還比較了蔣楫抄本與毛氏抄本的不同,因此,這個抄本的作者是毛晉或者汲古閣內的文士;梅文鼎是康熙以後才從事天文學、數學研究的,卒於順治十六年(1659)的毛晉不可能抄錄梅文鼎之書。所以,此抄本應是明末時毛晉或者是毛晉僱用的學者根據利瑪竇和其他明末學者關於天文學和天體測量方法方面的著作要點彙編改寫而成,故稱之為「撮要」。特別是上文有三段文字提到「以遠鏡望之」「以遠鏡測」「遠鏡中望之」,遍查明末清初有關遠鏡的記錄,無任何著作載錄文字與上述三段文字相同或者近似,因此,這些文字應該就是來自於利瑪竇的著述,所以我贊同朱維錚對此書所作的判斷:「我們難以否認這部抄本中包含著利瑪竇的未刊稿。」書中有關遠鏡的三處記錄,很可能就來自於利瑪竇的未刊稿。而在明朝末年時,確實有人記錄利瑪竇使用望遠鏡觀星。生於天啟元年(1621)的明末貢生顧景星稱:
利瑪竇云:小星光聚所成,清秋晦朔,無雲氣。時以玻瓈望遠鏡覘之,見細星如沙,猶水之有泡易日中,見沫是也。
這裡明確記錄了利瑪竇使用玻璃望遠鏡觀察秋夜的星象,與《理法器撮要》記載利瑪竇用望遠鏡觀察星象之史實相互印證。
無獨有偶,除了《理法器撮要》一書中記錄了利瑪竇使用望遠鏡的資料外,最近又有寧波大學歷史系教授龔纓晏在浙江省圖書館發現《開成紀要》抄本,該書署名為「太西利瑪竇傳,松江徐光啟校」。該抄本以條目的形式,介紹了眾多技術及工藝,全書共有條目六十多條。在這部署名為「太西利瑪竇傳」的《開成紀要》一書中,有專門對望遠鏡的介紹,詳細介紹了其製造方法及過程,包括「材料」「體制」「造模」「造鏡」「造筒」等。這是一部極為重要的由利瑪竇和徐光啟合作完成的關於工藝方面專門的科學著作。從書中的文字和內容看,應該屬於初步完成的文稿,尚未經過考訂審核,所以一直是以未刊抄本的形式保存下來。下面轉錄有關望遠鏡製造工藝的全部文字如下:
遠鏡
一材料,須透明真玻璃厚及一分者,方可作前鏡,若薄,即不能大。為其體要凸出故也。玻璃照面大鏡破者可用用水晶則工力信,無能傷眼。
一體制,前鏡要凸出,則所視物,大於本體。遠則其大無盡,遠者前鏡去目稍遠也。故以後鏡收之,後鏡要窪下,其所視物形,小於本體,前後相合。又,二鏡相去如法,則遠體成近,小體成大矣。
一造模,銅板如窪鏡,徑七寸上下。其深中規,規之半徑,即遠鏡筒之長,為前後二鏡相去之度。先作半徑尺,取圓分作兩曲背尺,又作銅金與曲背尺相合,以旋模,令曲背尺相合,乃已。此曲背尺,留取常用試模。恐磨久模損,則不凖也。其窪鏡之模嘗凸起,則用薄鏡銅板窩作釜形,大不過一寸五分,亦如前作中規內向曲尺,將模窩訖,以曲尺范之,仍上旋床銼之,令與尺合。再用有凹砂石磨光,其二磨之比例,則大模之半徑,與小模之半徑,若二十與一也。
一造鏡,先作前鏡,將玻璃剪圓,以木長二三寸許,圓與鏡等,以餹膠膠定,手持木向銅盤磨之,磨用寶砂碾店有之用細者,和水磨之,候與鏡盤將次合式不必盡合,合則料太薄矣,即易寶砂漿即前寶砂磨下水飛出至細者也,或於碾店取水瓦出用,又磨至光滑無紋路,乃己。但光而不亮,次又用羊肝石,研極細飛極漿水磨之。候見亮光,乃己形如昏鏡。次用寶葯蘇州吳趙芳碾寶石沉家有賣,每兩三分五厘,托碾匠買之,將來水飛,取具極細者,再磨至極亮,乃己。寶葯須多磨,不宜用手,須用鏡帶木膠上旋軸,用牛皮,外面蘸寶葯少許不宜多用旋之,令照見絲髪、遠物一一極分明,乃己。其後鏡,將小模膠上旋軸,玻璃不必與前鏡等大。次將黃蠟傾化,粘玻璃一面,令著指以鏡抵模,用寶砂水旋之令深,不令玻璃穿為度,次如前用寶砂漿、羊肝石漿磨至微明,即取去模,將鏡膠上旋軸,亦用牛皮剪圓,用角蘸細寶藥水磨如前,極亮而止。後鏡只作一面窪,不宜作兩面。其前鏡若作二面凸,則比一面者,近三分之一。若用前鏡二作眼鏡,則凸之多少。以人年酌量之,年愈老,徑愈短。
凡眼鏡欲中高,則玻璃體薄者,不能如法,法作二面凸酌量為之,令合目乃已。若近視眼鏡,則作窪體,但與前鏡大小不同,須半徑稍長,窪稍淺,用水晶,乃可作二面,玻璃無此厚體,但可作一面耳。
一造筒,或用銅皮,或用鐵皮,以錫焊,或用布表,漿用白芨麺,內外用綾作面,以便抽拔,筒之數,或二或三以上,同前後鏡相去之度,酌量為之。
如此詳細記錄用玻璃製造望遠鏡的工藝流程和製造方法,是中國科學史著作首次出現。1615年出版陽瑪諾的《天問略》,雖然介紹了伽利略發明望遠鏡,但並沒有記錄望遠鏡製造的方法。湯若望《遠鏡說》雖然記錄瞭望遠鏡的製造,但利瑪竇《開成紀要》記錄的文字與湯若望完全不同。湯若望稱:
一鏡,造法曰:用玻璃制一似平非平之圓鏡,曰筒口鏡,即前所謂中高鏡,所謂前鏡也。制一小窪鏡,曰靠眼鏡,即前所謂中窪鏡,所謂後鏡也。須察二鏡之力若何相合,若何長短,若何比例,若何苟既知其力矣,知其合矣,長短宜而比例審矣,方能聚一物像,雖遠而小者,形形色色,不失本來也。一筒,鏡止於兩,筒不止於兩,筒筒相套,欲長欲短,可伸可縮。
比較《遠鏡說》與《開成紀要》兩書關於製造望遠鏡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知道《開成紀要》並非來自湯若望,這應該是利瑪竇從西方科學著作中又結合自己擁有望遠鏡的實體而寫出的關於望遠鏡製造方法和工藝流程的文字。因為其合作者是徐光啟,故亦可斷這應該是早於陽瑪諾和湯若望而成為中國科學史著作中首次對望遠鏡製造的介紹。
利瑪竇能製造望遠鏡,明末人孫承澤在他的《春明夢余錄·寺廟》中早已指出:
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冊,皆以白紅一面反覆印之,字皆傍行,其書裝法如宋板式,外以漆革䕶之,外用金銀屈戌鉤絡,所制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鍾、天琴之屬。
孫承澤生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春明夢余錄》是一部主要記錄明代北京地方歷史的著作。在這部書中,孫承澤明確稱利瑪竇「制望遠鏡」。這是明人第一個稱利瑪竇能製造望遠鏡的人,表明利瑪竇不僅將望遠鏡帶進中國,而且他還能製造望遠鏡。這還可以從生於明天啟三年(1623),卒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毛奇齡所著《西河集·西教入中國録》獲得證明:
利瑪竇於明萬曆間由廣東入中國,漸入留都,高論驚人,且出其制自鳴鐘、千里鏡諸品示人,則大驚,號為西儒,留都禮部遂咨送北京。
毛奇齡是明末清初著名史學家,所記錄的歷史事實大都經過認真考訂,在其著作中更進一步提出利瑪竇在南京時出示了自製的望遠鏡。也就是說,利瑪竇到南京時,就能製造望遠鏡了。還有生於天啟六年(1626),卒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吳肅公在《明語林·巧藝》中亦有相似記載:
西洋人利瑪竇,精曆象、推算、勾股、圭測之術。規玻璃為眼鏡燭遠者,見數百里外物。
這裡稱「規玻璃為眼鏡燭遠者,見數百里外物」,很明顯就是利瑪竇製造的望遠鏡。所以,在很多明末人的認識中,利瑪竇確確實實能製造望遠鏡。然而,從《開成紀要》記錄的望遠鏡細緻的工藝流程和製造方法來看,其製造方法都十分簡單,工藝流程也並不複雜,製作材料也沒有什麼特殊講究,主要是玻璃的磨製。所以,該書所記錄的製造「遠鏡」的工藝,絕不可能是伽利略1609年後伽利略所創製的天文望遠鏡,而只是用於航海或軍事上作為測遠工具的普通望遠鏡。從利瑪竇所著《開成紀要》的記錄可以得知,在利瑪竇身邊不僅擁有望遠鏡,而且利瑪竇極為熟悉如何製造望遠鏡。這與明代文獻中關於利瑪竇帶望遠鏡傳華的記錄完全吻合,也與鄭仲夔稱「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孫承澤則稱「所制有遠鏡」的記錄完全吻合。利瑪竇《開成紀要》中關於望遠鏡製造方法的記錄,進一步印證了明代文獻記錄利瑪竇不僅將望遠鏡帶入中國,而且還將製造望遠鏡的技術和方法傳入中國。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開成紀要》一書所記載的內容不一定全是利瑪竇所傳,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徐光啟自己所作,但其中關於望遠鏡的製造方法應來自利瑪竇。明末清初造鏡專家諸升《<鏡史>小引》稱孫雲球:
壬子(1672)春,得利瑪竇、湯道未《造鏡幾何心法》一書,來游武林,訪余鏡學。時余為筆墨酬應之煩,日不暇給。雨窗促膝,略一指示,孫生妙領神會,舉一貫諸,曾無疑義。越數載,余因崇沙劉提台之召,再過吳門,孫生出《鏡史》及所制示余,造法馴巧,並臻絕頂。中秋月夜,相對討論,亹亹不倦,予亦罄厥肘後以述。今制諸鏡,迨無出其右矣。且謙抑韜晦,本於性生,五車二酉,莫竟其藏。迄與人相接,如良賈深居,務匿瑤彩。即造鏡一藝,獨得利、湯幾何之秘,啟發則舉一知三,而加功又人一己百。然稍聞有擅此技者,必虛衷請教,一若其反勝己者。語云:盛德若虛,大智若愚。愈足征其謙抑韜晦之美,送養竭盡之誠矣。造鏡家,余亦閱曆數子,得其形似者十有六七,會其神理者十無二三,拈花微笑,惟孫生一人,即起利、湯而證之,恐不易吾言。錢塘諸升日如氏題於孫生安素齋之斗室。
諸升明確稱,孫雲球在康熙十一年(1672)時得到過利瑪竇的《造鏡幾何心法》一書,並兩次提到孫雲球的望遠鏡製造技術得之於利瑪竇與湯若望的「幾何之秘」。這可以說明,利瑪竇確實有關於如何製造望遠鏡的文章傳世,利瑪竇製造望遠鏡的名聲在明朝末年已經傳開。另外,康熙時人鄭相如亦稱:
至萬曆間,西人利瑪竇入京,有《西鏡錄》《同文算指》諸書流傳中國,純以筆用,但其寫法橫列如珠盤,位自左而右。
這裡提到的利瑪竇《西鏡錄》應該與利瑪竇的《造鏡幾何心法》是同一內容的書,而《開成紀要》中利瑪竇所記錄的製造望遠鏡的方法和內容與諸升、鄭相如的說法相互印證,反過來又可以證明《開成紀要》應該就是利瑪竇、徐光啟兩人合作完成的未刊稿。《開成紀要》的發現,應該引起從事利瑪竇研究的東西方學者深刻反思。利瑪竇在中國生活了近三十年,他到底留下了多少西文著作和中文著作,至今都無法予以準確估計,所以斷不可以為,利瑪竇本人沒有記錄下來的東西,就否定它們的存在。
關於利瑪竇能製造望遠鏡的史實,還可以從與他同時代傳教士望遠鏡製造得到證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曆法疏》稱:
邇年台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旣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敎,曉習華音。……觀其所制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
從上引奏章可以看出,李之藻在1613年就知道當時的龐迪我、龍華民等傳教士能夠製造「窺天窺日之器」。又,萬曆四十四年五月(1616年6月),南京禮部侍郎沈㴶給明廷上了一份著名的奏章——《參遠夷疏》,其中也提到:
說者又謂治歷,明時之法,久失其傳;台監推算,漸至差忒。而彼夷所制窺天窺日之器,頗稱精好。以故萬曆叄拾玖年曾經該部具題,欲將平素究心歷理之人與同彼夷開局翻譯。
這裡所謂「彼夷所制」,是指這些傳教士所制;所謂「窺天窺日之器」,指的應該就是望遠鏡。明人揭暄亦稱,湯道未、龐迪我造有「測日月食永儀、窺天遠鏡」;他甚至將望遠鏡直接稱為「窺天鏡」。徐光啟《新法算書·新法表異》亦稱:「所制遠鏡,更為窺天要具,用之能詳日食分秒,能觀太白有上下弦。」清人戴大昌亦云:「望遠鏡,亦名窺筩,蓋用以驗日食、月食之時刻分秒。」可知,當時能夠「窺天窺日」的科學器械應該指的就是望遠鏡。既然在1613年的李之藻、1616年的沈㴶奏章中都明確提到了西洋人製造的望遠鏡,而且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禮部已經提出讓這些傳教士參加修訂曆法,於是,為了進京修訂曆法,傳教士們加緊製造這些修歷的必備科學儀器——「窺天窺日」的望遠鏡。這也可以說明,在1611年之前,不僅望遠鏡已經被傳教士帶進了中國,而且為了參加明朝宮廷修歷的需要,以利瑪竇為首的來華歐洲傳教士都已經掌握了製造普通望遠鏡的技術而加緊趕製望遠鏡。這也應是當時耶穌會中國傳教團最重要的傳教策略之一。
綜上所述,明人鄭仲夔「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之說,記錄的就是歷史的真實。利瑪竇生前不僅將望遠鏡帶入中國,而且還向徐光啟傳授過製造望遠鏡的方法;他還翻譯介紹過製造望遠鏡工藝方法的文章,但未刊行。所以說,在明代的中西科學文化技術交流史中,利瑪竇當是第一位將望遠鏡製造技術傳入中國的歐洲人。他與他同時代的歐洲傳教士不僅將望遠鏡帶進了中國,而且在耶穌會中國傳教團傳教政策的指引下,為了明朝宮廷修歷的需要,還製作了一批望遠鏡,而這些望遠鏡在明代社會已經得到廣泛傳播。
湯開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客座教授、澳門口述史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明清史、澳門史、中外關係史、西夏史及中國邊疆民族史研究,出版學術著作《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明清士大夫與澳門》《党項西夏史探微》《宋金時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澳門編年史》(六卷,合著)《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等十五部。
來源:《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