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龍潭湖(本文配圖均選自蘇月斫的《光明樓——北京人家影像故事》)
當年在山東畫報出版社,我策划了一套「名人照相簿叢書」。這個名稱最早可以追溯到作家劉心武1986年在《收穫》雜誌上開的一個專欄,名稱是「私人照相簿」。我對這種以平民家庭照片為線索,有點民間書寫意味的著作方式很感興趣,於是冒昧與他聯繫,希望由他主編,約寫一套「私人照相簿叢書」。他忙於新的創作,沒同意,於是我就改了一個字,變成「名人照相簿叢書」,陸續出版了弘一大師、巴金、冰心、張愛玲、梁思成、啟功等二十多本。創辦《老照片》時,設立欄目,有個「名人一瞬」,與之相應,設了一個「私人相簿」。二十七八年下來,「私人相簿」成為來稿最多的欄目之一。
近些年,我有一個尚未實現的願望:做一套「一個人的照相史」叢書。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有句:「世上每個人都特別有意思」,高爾基則說:每個人都應寫一本傳記。同樣,每個人一生的照片就是一部有意思的圖像自傳。蘇月斫的《光明樓——北京人家影像故事》正是我想像中的那樣一本書:民間,鮮活,感人,美妙,充滿無意間的歷史感。我很喜歡這本書,為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這樣一本書感到欣喜。
劉心武曾解釋為什麼要寫「私人照相簿」這個專欄:「在我內心深處,常涌動著莫可名狀的情思。作為一個獨特的個體,我們出生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什麼家庭,處身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人文環境,我們承繼著什麼樣的遺傳基因、文化遺產,都是不由自主的……當人獨處一室,翻動著自己的私人照相簿時,或者可以鬆弛下來。人在這時可以意識到其實自己是可愛的,有道理的……」對此,我深有同感。

媽媽在永生小學院內(1979)
不過,每個人都寫一本傳記,說來容易,真做起來是很難的。首先你要有大量的、長年的積累和記錄。時光嚴酷,它會帶走一切,尤其那些生活細節,如果沒有當時的、有心的記錄,就會如海邊砂礫一般,被亘久不息的浪潮沖刷得乾乾淨淨,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其次,還要有一定的寫作能力,這是不言而喻的。所幸月斫的父母「文藝、師範」,而且年輕、漂亮,他們都曾是教師,爸爸蘇建華老師還是一名小有才氣的畫家,後來成為專職的美術工作者;媽媽閆靜平任過三十年音樂課老師,喜歡唱歌。當一般人還不懂得攝影重要,也沒有條件擁有相機時,蘇老師已經迷上攝影,大量拍照並自己洗印了。開初是借用別人的相機,後來省吃儉用購置了自己的。

爸爸媽媽在北京駒章衚衕33號(1985)
沒有孩子時,他們一個喜歡拍,一個喜歡照,拍和照都有文藝范兒,並非一般的家庭照。閆老師的美麗,是那個時代的美麗,是真正的美麗,不是如今修飾、妝扮的美麗。女兒降生後,這個溫馨的家庭自然又多了一根樂弦,大量的照片組成新的樂章(不知為什麼,我覺得這本書從頭至尾有音樂在背後)。女兒的出現並未造成對年輕媽媽的忽視,而爸爸的情感和寄託則通過拍照貫穿始終——這種飽滿的一個家庭幾十年完整的影像紀錄,比文字記錄更為豐厚和鮮活,其最大特點就是一目了然的細節:人物的表情、穿戴、動作,比如長辮子、花紗巾,家居的物件、樣式、新舊乃至雜物、門窗和窗帘,室外的樹木、水潭、山路乃至修二環、改造龍潭湖……這些細節,無處不在地展現了20世紀70至90年代北京一處街區一戶人家的日常,看上去親切、溫暖而又讓人惆悵。

我來了(廣渠門護城河東岸)
說實在的,一開始看到材料,我沒把握這本書該怎麼做,能否做成。有了豐富的影像紀錄(兩萬餘張照片),如何選擇、刪減、編排、展示、寫作、呈現給讀者,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我相信作為女兒的月斫,她的選擇既是最準確的,又是最難捨的;她的展示是最充分的,又是最收斂的。在這裡她有兩個角色,一是書的主角之一,一是書的編輯者;一個現身其間,一個置之其外。正像這本書的性質:既是私密的、個性的,又是社會的、普遍的。我不知道她編寫這本書用了多久,但那一定是一段深刻的情感之旅。

在北京動物園(1985)
月斫供職於《大眾攝影》雜誌,她也許學習了社會學、人類學的某些研究方法,受了攝影哲學和現代文學敘事方式的影響。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是爸爸媽媽的影像,第二章是女兒(即本書作者),第三章是一家三口,第四章「照片中沒有了我們三人的身影,但場景都取材於那些年我們生活中經常路過的、看到的地方。正是一張張看似散淡的、無關的、抒情的影像,承載了我整個童年的記憶場所,家在哪裡?就在這裡」。四章內容從小至大、從單純到複雜,各自獨立而又相互觀照。有意味的是,那些爸爸早年的水粉寫生風景畫,與照片融合、呼應,增添了日常的存在感,是別緻的一筆。
文字在書中並不鋪張,也不搶眼,是看了照片引起的回憶,簡明直白但又鮮活俏皮。敘述都是以第一人稱「我」或「我們」,但這個「我」,一會兒是媽媽,一會兒是爸爸,一會兒是女兒,有時又代表一家三口。雖然作者在文中有所交代,但讀的時候還是要根據照片和文意琢磨一番此刻是哪個「我」在講述?讀者因此有一種參與感、新鮮感。我想,這就是年輕一代的作者、編輯高明的地方,他們更有跨文化、跨領域的接受能力,更喜歡追求先鋒的表現方式。
除了整體結構的巧思和時空交叉的敘述方式,作為圖文書,圖片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置,圖片與文字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置?要使整本書流暢、錯落、好看,有空間,又不斷篇兒,也是相當有技巧的。不過,作為攝影雜誌的編輯,作為山東畫報出版社,這正是他們的長項——以書為證。
2024年元月北京十里堡
作者:汪家明
文:汪家明圖:月斫編輯:謝娟責任編輯:舒 明
轉載此文請註明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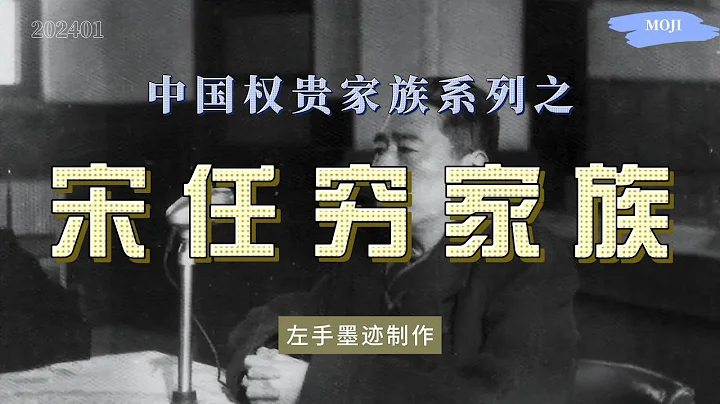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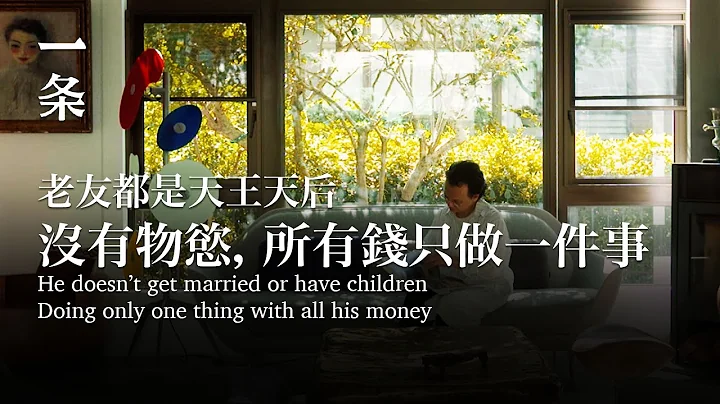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