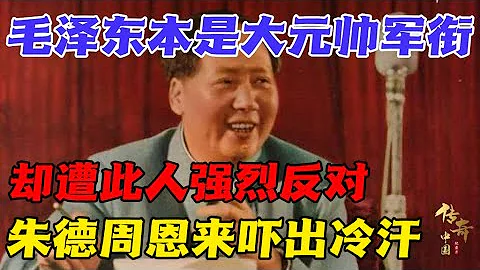基督教也許被人視為烏合之眾對這個世界的復仇。公元70年耶路撒冷所羅門聖殿的毀滅造成了「猶太人大流散」,他們所懷揣的猶太末世論種子在將來會蛻變為基督教。這些思想的種子起先在遠離羅馬的地方生根發芽,而我們此前已經在別的時代邂逅過這些地區,譬如小亞細亞、希臘、馬其頓、腓尼基和埃及的各大城市。基督教作為猶地亞地區一種隱蔽的猶太宗教逐漸發端。儘管後世的基督教作家極盡了天馬行空的誇張修飾之法,但事實上我們依然不清楚早期基督教的模樣,因為當時不管是猶太人還是羅馬人似乎均沒有對這門宗教產生特別濃厚的興趣。尼祿將基督徒順手拿來當作替罪羊,為公元64年那一場焚毀大部分羅馬城的大火背黑鍋。而尼祿之所以這麼做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他覺得基督徒無關緊要,根本沒什麼人會在意他們。事實上,羅馬民眾的確對基督徒深表惋惜,但這更多的是出於他們恐怖的死亡方式,而非任何由衷的同情憐憫之心或對教徒的信仰真的有什麼認知。那些基督徒被當作人體火炬燃燒,還披上獸皮被野狗撕成碎片。
似乎明了的是,耶穌作為一位來自加利利的猶太人雖未受過教育卻擁有超凡的個人魅力,他於羅馬皇帝提比略統治期間(公元14年至公元37年)在猶太同胞當中聚攏起了相當規模的追隨者。耶穌的活動最終引起了耶路撒冷猶太精英的注意,他們對耶穌的人氣感到警惕,並遊說行政長官本丟·彼拉多將耶穌推上審判席,耶穌被當作一名30多歲的普通罪犯用釘十字架的方式處死。耶穌的故事肯定不是公元1世紀猶太地區絕無僅有的孤立事件,其他來自加利利的先知型宗教人物也同樣吸引了大量擁躉而最終釀成了與羅馬當局或代理國王的衝突,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數施洗者約翰了。真正令基督宗教脫穎而出的是,耶穌的彌賽亞主張並未隨他的死去而消失。最關鍵的是,基督教的重心逐漸聚焦到勸說異邦人信主一事上,這意味著基督教不僅僅是又一門猶太宗教而已。塔蘇斯的保羅是擴大教派影響的重要人物。他不僅從小就被以猶太精英成員的身份培養,而且其羅馬公民的地位也使他成了轉信基督教的一位不同尋常的信者。保羅著手將這個初出茅廬的宗教團體引向雄心勃勃的全新方向,他開始在敘利亞、小亞細亞和希臘地區廣泛開展傳教工作,並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效果。待保羅年過花甲去世之時,這門宗教雖然仍很弱小,但在那些地區的許多大城市裡都已經健康良好地建立了起來。新創的基督社群之中有大部分成員都是異邦人,以手工匠為主。也許正是基督徒所面臨的來自各方的敵意——先是猶太精英而後來自羅馬當局——才使得教徒們自我組織得井井有條。他們擁有一套清晰的層級制度以及來自主教和教士的強有力領導。教徒社群具有一種慈善精神,因而在羅馬城市社會的貧賤階層當中特別具有吸引力。窮人們總是對那些賞賜食物、幫助埋葬死者的善心人抱有好感。

帝國全境內的許多宗教均相當和諧地共存著,而基督教在發展認同上另有其他方面與眾不同。首先,基督教的社群感十分強烈,它由一套複雜信仰團結起來,彌賽亞及追隨他的精選領袖團體已參悟了無可辯駁的真理。不過真正將基督教推上那條頂撞羅馬之路的是基督教對異教活動的敵意。這種姿態頗具煽動性,因為那些異教活動是幫助帝國團結凝聚的黏合劑。但至高無上的天主是唯一的,基督徒反對其他人的神靈,不願意玩羅馬人的遊戲。以德爾圖良為例,此人是公元2世紀晚期至公元3世紀早期居於迦太基的一名基督徒。(迦太基在公元前1世紀40年代由尤利烏斯·愷撒重建,成為羅馬轄下主要的非洲城市和基督教早期的重要中心。)德爾圖良被世人看作第一位用拉丁文著書的基督聖徒。他力勸教友們停止觀賞競技比賽,不要去劇院看戲,因為那裡所表演的一幕幕盡皆邪惡,而且還與異教神靈及宗教儀式存在瓜葛。德爾圖良命令女教徒們戴上面紗並迴避黃金首飾,他讚美貞潔,稱其為基督徒最受祝福的生活狀態。對於德爾圖良而言,原罪幾乎在羅馬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潛伏著。儘管後世的基督徒認為他有些瘋狂,但德爾圖良的觀點比慣常的標籤更具代表性。倘若他人的觀點對自己合適,那麼羅馬人便會容忍他們,但早期基督教徒搞出了一種讓人忍無可忍的生活方式,他們以自我的謙卑和犧牲而倍感自豪。
於是迫害行動很快降臨,不過通常並非來自帝國當局,而是由當地人發起的。當局常常很不情願地被牽扯其中。從德爾圖良的論著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迫害的效果只是令基督徒對羅馬帝國的態度愈發堅定不屈。他諷刺挖苦的旁白文字可謂火藥味十足。
假如台伯河水位之高淹沒了城牆,而尼羅河之低灌溉不了良田;假如世界山崩地裂,天空烏雲蔽日;假如饑荒遍野,瘟疫肆虐……此時呼喊聲會即刻響起:「基督徒們起來反抗『猛獅』!」什麼?所有基督徒?對付一頭「獅子」?

基督徒明顯感到無論什麼事情都會怪到他們頭上。對德爾圖良而言,羅馬就是「復活之書」中預言的「巴比倫啟示錄」,它沉醉在基督殉道者的鮮血里忘乎所以。德爾圖良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羅馬公民,他是一名律師,同時又是軍官之子,這個國家長期仰賴於像他這樣的個體,然而德爾圖良的文字顯露出對國家的一種別樣的疏離感。至於他為了堅決反對帝王崇拜所運用的其他一些觀點則來源於《新約》,來自耶穌對繳納帝國稅金這一棘手難題的機智回答,即「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羅馬帝國的官員會在未來的數世紀里時常聽到此回應。
其實跟當地行省的精英相比,帝國當局在迫害基督徒一事上長期以來始終相當冷淡。小普林尼無休止地寫信給圖拉真,其中一封請求圖拉真指示如何處理在他的行省比提尼亞境內的基督徒問題。皇帝勸告小普林尼,表示對基督徒不應當趕盡殺絕,而要儘可能多給一些迷途知返的機會。面對日益強大的基督宗教,羅馬人疲於應付,因為在傳統上只要別人尊重帝國的話,羅馬人就不會計較他們信仰哪些神靈,可是這老一套的行事方法根本糊弄不了這些狂熱分子。同此時此刻的待遇相比,基督徒們對死後世界更感興趣。
公元203年,最可怕的基督徒殉難大屠殺在迦太基的圓形競技場爆發了。這座競技場的規模在帝國之內數一數二,能夠容納3萬名觀眾。當時的皇帝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掀起了一場針對基督徒的迫害行動,並頒布法令禁止帝國臣民成為基督徒。有一位名叫波佩圖阿的女子信了基督教,她出身於富裕的異教徒家庭,像這樣的社會地位入教是不太尋常的,也許這種對階級的侵犯感正是令此則故事臭名昭著的原因之一。該女子年僅22歲,正在給小寶寶哺乳之時,忽然間就同其他基督徒一道被捕,其中還包括了她懷有身孕的僕人費莉西塔斯。波佩圖阿反抗來自家庭和當局的強大壓力,拒絕放棄信仰,在圓形競技場被判處死刑,波佩圖阿在獄中的時候跟許多殉道者一樣,都產生了許多「幻覺」。其中有些人宣稱波佩圖阿眼前的殉道不僅會幫助癒合其家庭的傷痛,還能彌合廣大基督社群內部的分歧。不過另一些人則明確表示波佩圖阿在競技場上將要面對的不是同野獸進行搏鬥,而是與魔鬼本人的真正交鋒。然而與此同時,費莉西塔斯愈發焦急起來,她的孩子即將出生,這會耽誤自己的殉道。不過在競技開始的前兩天,寶貝女兒呱呱墜地,這意味著費莉西塔斯的殉道願望並沒有落空,那名嬰孩後來被一名女基督徒收養。競技舉行當天波佩圖阿和費莉西塔斯均赤裸著身子被帶入競技場。群眾對此抗議,因為費莉西塔斯正在分泌的雙乳還在滲出乳汁。於是女子被帶出了競技場,遮蓋完畢之後又被重新領了出來。待一陣鞭打過後,兩位女子被一頭野牛踩踏。她們傷勢嚴重,痛苦非常,但仍然活著,隨後被一名劍士完結了生命。角鬥士的手顫顫發抖,波佩圖阿不得不指引著他,以便對方最終能夠割開她的喉嚨。

儘管存在這些駭人聽聞的故事,但一直以來真正殉道的基督徒並不多,直到公元3世紀情勢才有了轉變。當時兩位最高效、最具改革頭腦的皇帝德基烏斯及後來的戴克里先逐漸關注這門宗教的傳播,基督教似乎要破壞帝國賴以構建的許多根本原則和政策。教徒們拒絕帝王崇拜的獻祭活動,而這兩位皇帝均利用了這種反對態度,將頑固不化的狂熱分子連根剷除。德基烏斯在公元249年發布了一條敕令,要求在帝國境內開展一場全國性的帝王崇拜獻祭活動,此舉讓他在基督徒中間迅速掙得了一個反基督代言人的名聲。國家指派當地官員去落實這項政令,並簽發文書來證明特定的人員已經實施過獻祭活動。許多比較富裕的基督徒為了搞到一張此類證書便運用行賄的手段,或者花錢僱人以自己的名義代為獻祭;而較為貧困的基督徒則面臨一個更為簡單明了的選擇,要麼掉腦袋要麼去獻祭。數以千計的人放棄了原則,只有真正寧死不屈者才最終反抗到底。
對於那些決意要負隅頑抗的人來說,殉道不是一種懲罰而是獎賞。在這些基督徒的殉難事迹里,對肉體施行的可怕暴力與殉道者振奮的精神狀態之間存在鮮明的對比。這樣的故事很自然地存在某種強烈的修正主義宣傳元素,但即便是當時的證據也表明人們普遍認為殉難行為伴有某種精神麻醉的心態。有些基督徒將自己視為運動員,要在競技場上擊敗撒旦,而光榮的殉道就是一種勝利形式。基督教會在全國各地散播這些可怕的殉道故事,並在基督徒的集會上大加傳頌。迫害行動非但沒有摧毀基督教會,反而令它愈發強大起來。
公元303年2月23日,戴克里先發動了一場所謂的「大迫害運動」,他下令搗毀基督教經文著作,查禁禮拜用書,拆除帝國境內各處的崇拜場所。基督徒同時還喪失了法律權利。信教的元老院議員、騎士階級以及其他精英團體均被褫奪了頭銜和職位,然而這種現象本身就表明當時的基督教已經在帝國貴族當中展開了內部侵蝕,事實上戴克里先自己的妻子普利斯卡就是一名基督徒。戴克里先意欲通過振興傳統宗教活動的方法來重塑羅馬美德,就恰如奧古斯都在三個世紀之前所做過的那樣。戴克里先和「四帝」當中的其餘幾位都將帝國的福祉安康與百姓對傳統諸神的持續敬拜緊密地掛鉤起來,也正是緣於此等原因,任何一種威脅帝國安危的宗教都是大逆不道的。在接下來的歲月里,戴克里先及其繼任者們運用各種政策手段來對付基督徒,並轉而引入一套更為嚴酷的法律體系,而後他們又用實行特赦的方法中斷,然而他們所做的一切均無法阻止基督教的崛起。
後來在公元312年10月28日,羅馬帝國漫長歷史里的一個重大事件爆發了。「四帝」之中兩位敵對皇帝的軍隊在羅馬的米爾維安橋展開廝殺。戰爭事後被證明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君士坦丁取得了戰鬥的勝利,而其對手馬克森提烏斯則掉入台伯河裡淹死了,他被自己沉重的鎧甲拖了下去。這場戰爭標誌著由戴克里先創立的「四帝共治」體系開始走向終結,而與此同時君士坦丁異軍突起,成為羅馬世界的唯一主宰。不過在這一切之中真正具有紀念意義的是,君士坦丁將會主導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宗教改革。米爾維安橋之戰將一改教會與帝國此前的對抗形勢,會被世人宣告為雙方力量天平傾斜的轉折點。

君士坦丁和將士們在取得戰爭決定性勝利之前望見天空中有十字架的圖案,之後君士坦丁宣稱自己已信了基督教。然而也有人說實際上他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日暈而已。但當時的基督徒們很自信地認為這就是上帝支持君士坦丁的跡象,而君士坦丁是第一位值得讓基督教世界「泄露天機」的皇帝。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下了一道赦免詔書,最終授予了全境的基督徒從事宗教活動的自由,並恢復了此前被沒收的財物和屬於教會的資產。公元325年,隨著持久內戰的結束,君士坦丁掌控了全國。皇帝慷慨地贈予土地和資金,投射大量的影響力,此時基督教會的命運似乎已經完成了極大的轉變。
在羅馬,一系列宏偉壯麗、美輪美奐的教堂紛紛拔地而起,這對基督教而言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相傳首位主教就是聖彼得。基督教的主教如今已被納入皇帝的核心幕僚圈了。他們的影響力可以從君士坦丁發起的大量道德和宗教改革之中窺見一斑。神職人員從繁重的公務中被解放了出來,而主教們則被賜予了司法特權。反對通姦和鼓勵婚姻的法條得到了強化。與此同時,基督教對其他信仰及活動的零容忍性也開始被人察覺,一部分受人尊崇的異教神廟均被關閉,基督徒長期以來一直指責其進行不道德的活動,特別是那些與愛神阿佛洛狄忒祭典有關的。此外,另有其他法律禁止了法術、占卜和某些殺生祭祀活動。
為什麼君士坦丁會突然投入基督教的懷抱,這裡有一個巨大的問號。但對於基督徒而言答案是清楚明了的:皇帝是一位真正的信徒。在政治上利用教徒人氣以作為權宜之計的想法當然是可以排除掉的,因為時至公元312年羅馬帝國人口當中基督徒只佔了不到10%,大多數人並不來自任何強大的宗教勢力階層。然而問題是君士坦丁一直等到臨終前才接受了洗禮,要說他迫切想成為真正教徒的說法恐怕是很難站住腳的。我們沒有決定性證據來表明君士坦丁到底是一個真心虔誠的人還是一位世故的權術家。考慮到君士坦丁個人對信仰的那份虔誠之心曾經在許多不同的神靈之間飛快地轉換過,那麼此人長期對基督教保持興趣倒是令人頗感驚訝,不過相比之下我們也許更容易回答這一問題。答案很簡單,君士坦丁摧毀了精心構築的「四帝共治」體系並用獨霸天下的統治模式取而代之,對於這樣一個人物來說,基督教的那種決不妥協的一神論觀點勢必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此後將會是一個皇帝、一位神靈的時代。在成為帝國全境唯一主宰之後,君士坦丁很快就發表了一場演說,將一神論與在天堂和凡間的多神論相比較,他如是坦陳其危害:
君主制絕對遠勝過其他任何類型的政治體制和政府形式,因為與其截然相反的民主平權事實上只不過是無政府的混亂狀態。這就是為什麼只有一個上帝,而不是兩個、三個或更多。

基督教會雖然之前曾尖銳抨擊世俗帝國,但他們顯然非常善於適應這大幅提升的全新環境。教會的領袖們十分樂意宣稱君士坦丁的統治是由神靈所授,就好像一種合作關係已經由上天促成,或至少說是受上天首肯的。
然而基督教會和羅馬國家新建立起來的這些聯繫立刻就面臨了壓力。人們很快就清楚地發現,基督教在君士坦丁身上的影響是有限的。皇帝願意向教會撒下大把金錢和資源,但任何可能鬆懈其權力掌控的做法則完全不在考慮範圍之內。這一點從帝王崇拜一事上就很能說明問題,君士坦丁似乎仍然認定這種傳統宗教是十分有用的,全然不顧異教信仰與基督教核心原則相悖這一事實。公元4世紀30年代中期,君士坦丁的統治期漸入尾聲,他批准了一項來自義大利城鎮西斯佩倫的公民訴求,允許百姓以他本人和皇族的名義建造一座神廟,但附加了重要的條件,即不允許在裡面進行殺生祭祀活動。這是典型的君士坦丁式胡鬧,一方面設法不過分疏遠任何人,另一方面推動一項將自身領導權最大化的事業。如此一來,當地人有了他們自己的宗教活動,而基督教會則獲得了在禁止祭祀方面的滿足。這是一項持久的妥協方案,當考古學家在晚期異教神廟和聖殿里開展工作時,他們經常會在朝拜對象周圍找到破碎的蛋殼,最後一批多神信仰者以此類獨創性的做法來為他們的神靈獻上一場沒有血腥的殺生祭祀。
基督教會內部持續的爭吵是君士坦丁與基督徒之間緊張關係的最大來源。不消多久君士坦丁就會意識到那些看似也許隱蔽模糊的神學觀點對於他的新盟友來說是何等的重要。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在廣大的基督教社群當中,就正統信仰的構成要素問題似乎完全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聖父、聖子和聖靈到底是同一個人還是有層級的分別個體,人們對此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君士坦丁將自己視為上帝在宗教和世俗事務方面的凡間代表,他決心要對這場喧鬧紛爭做一個了結,於是他命令各大主教務必找到一種妥協方案。公元325年,他召集舉行了尼西亞會議,大會達成一項決議,幾乎所有的主教都簽字承認了。但假如君士坦丁以為教義的暗鬥就此終結的話,那麼他就大錯特錯了。轉眼間,諸多派別沒有一個對處理結果感到滿意的,帝王的干預不僅開創了危險的先例,而且還極大地抬升了基督教教義爭論的價碼,辯論雙方都渴望借用帝國的法律條文及其通常嚴酷的懲罰來彼此攻訐。同樣嚴重的是,凡是在帝國法律體系內行將失敗的人均會逐漸心生怨恨,將其視為皇帝對宗教事務的非法入侵。

基督教會與羅馬國家之間的緊張態勢經由幾十年的激化最終於公元4世紀80年代達到了危機的爆發頂點。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竟然是發生在兩位最虔誠的基督徒皇帝,即格拉提安與狄奧多西的統治期間。而基督教陣營最主要的推手是米蘭主教安波羅修,他是一位非凡卓越的人,經歷了成功的議員和城市地方長官的事業生涯之後,於晚年加入到基督教會的層級體系中。此人精力充沛、博學睿智,而且毫不懼怕與帝王討價還價。畢竟,他曾經擔任過某位帝王的老師。安波羅修堅信基督教會才是上帝在凡間的高級代表,而非羅馬皇帝。假如皇帝在未經教會領袖明確允許的情況下擅自干預教會事務的話,那麼他就是在僭越自己的職權範圍。然而即便在管轄範圍之內,皇帝的行為也應當嚴格受限,僅能夠運用世俗法律來落實教會的決策。以往的帝王常常一時興起就干涉教會事務,而安波羅修的此等論調顯然會將自己與皇帝對立起來,主教與皇帝之間力量對決的公開舞台就在帝國的皇城米蘭。
第一回合:小皇帝瓦倫提尼安二世的母親賈斯蒂娜是一位阿里烏斯派信徒,屬於基督教一個支派的追隨者,該派別沒有贏得尼西亞會議的勝利,不過存續了下來並在這中間的幾十年里數度興盛。皇帝要求安波羅修將他手上的教堂拿出一座來讓予阿里烏斯派,但被對方直截了當地回絕了,於是瓦倫提尼安調動軍隊前來。安波羅修沒被嚇倒,他將自己和教眾都鎖在教堂里,形成了一場不同尋常的對峙局面。帝國的官員們紛紛趕到現場,試圖打破僵局,但安波羅修立場堅定,孤注一擲,他猛然抬高對戰的籌碼,奮力地打出那張基督徒慣用的牌: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宮殿屬於皇帝,而教堂則屬於主教。你被賦予的權威只能用在公共世俗建築方面,而不是宗教建築。
在這種明確直白的警告面前,瓦倫提尼安的立場顯然動搖了,其風險不僅是與教會一刀兩斷,而且還同上帝本人斷絕關係。瓦倫提尼安先是有所猶豫,而後便下令撤軍。今後在安波羅修主持的米蘭將不會有阿里烏斯派的教堂。
第二回合:安波羅修不僅意志堅定而且狡猾老練,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而瓦倫提尼安只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毛孩,鬆鬆垮垮地掌握著他的帝國王朝,永遠都不是安波羅修那種人的對手。而統治帝國東半部分的狄奧多西卻非等閑之輩。此人精明強幹,是極具天賦的管理者和軍人,同時又以虔誠的基督信仰而著稱。這兩個令人敬畏的角色之間的碰撞將會是基督教早期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對戰。公元390年,狄奧多西派駐在帖撒羅尼迦的指揮官被當地的一夥暴民以私刑處死,於是他下令對帖撒羅尼迦施行大屠殺,6000人被以觀看比賽的借口誘騙至競技場。他們一到那裡便即刻慘遭屠戮。雖然不可否認此舉的殘暴性,但流程公開合規,是針對公眾秩序的結案。其處理的嚴厲程度常常被後世皇帝們習慣性地用來控制不安分的臣民。然而令此事與眾不同的是,帖撒羅尼迦是一座基督徒占多數的城市,儘管該案完全不在安波羅修的職權範圍之內,但他還是感覺自己必須有所回應才是。安波羅修將皇帝本人從基督徒的隊伍當中開除了出去。這也許是羅馬皇帝和基督主教之間最駭人聽聞的對抗,安波羅修居然公開拒絕為狄奧多西操辦聖禮聖事,甚至還禁止他加入教堂會眾。
安波羅修是個聰明的內行老手,知道要給他的皇家主子開一道門,永久的分裂畢竟對誰都沒有好處。在一封寫給狄奧多西的信中,安波羅修溫和地建議說,嗔怒乃是一種心靈之症,唯有基督教的懺悔和苦修方能治癒。這一觀點被對方接受了,在之後數月里,米蘭的公民們將會目睹皇帝本人異常壯觀的一幕:羅馬世界最強大、最可怕的人居然脫下皇袍,公開懺悔自己的罪過。皇帝全心全意地悔過,心存感激之情,遂被教會重新接納。然而即便到了此等地步,安波羅修仍確保每個公民都明白當初君士坦丁那種皇帝為上帝代言的模式已經宣告結束:
他(狄奧多西)撕扯頭髮,猛敲腦袋,眼淚打濕了地面,祈禱懇求上帝的寬恕。當輪到他將供物帶上聖壇之時,狄奧多西一邊始終悲泣著,一邊站起身子走近那塊神聖的位置。然而強勢的安波羅修再一次叮囑他注意分辨場所,安波羅修說道:「閣下,聖殿之所僅供教士使用,對其餘人等皆不開放,請你移步,站到眾人所站的地方。紫袍能讓你做皇帝,但做不了神父。」

皇帝或許是凡間最有權勢的人,但在上帝的宗教場所里,他只不過是又一個普通的教眾罷了。安波羅修針對皇權的著名勝利將會被新一代的基督教知識分子添磚加瓦,他們欲急切地重新思考自身與羅馬國家乃至整個凡間世界的關係。在這些神學家當中有一位極具天賦的人物,他確實可算作早期基督教會裡最為睿智的大儒,而此人正是由安波羅修在米蘭親手洗禮的。
奧古斯丁出生在北非塔迦斯特鎮的一戶中等富裕家庭。他的人生道路承襲了之前歷代行省才俊的步伐:在首府迦太基接受良好教育,隨後到米蘭取得一個教授修辭學的好職位。奧古斯丁早年曾有一段時間對摩尼教感興趣,那是一種來自敘利亞的禁忌宗教。不過在米蘭的時候他拜倒於安波羅修的魅力之下,經過洗禮之後,奧古斯丁決定放棄前程似錦的職業生涯,返回北非投身於基督教會。這一決定將永遠改變他自身的生活及西方基督教世界。
受聖安東尼榜樣力量的啟發,奧古斯丁想在塔迦斯特的一個基督徒小社群里悄無聲息地過一種清貧的生活——充滿僧侶式的簡樸作風與冥想沉思。這是有意識的遁世之舉,即遠離這片塵世與曾經熱切追逐的社會舞台。然而此等狀況並不長久,奧古斯丁在返回非洲多年之後,造訪了希坡。那是一座擁有龐大基督教社群的繁忙港口城市。早期基督教會最吸引人的一個方面就是眾多領頭的神學家最終都會成為現實世界中某個小城鎮的主教,雖然希坡並非什麼窮鄉僻壤,但對於像奧古斯丁這類曾在迦太基和米蘭生活工作過的人而言,希坡仍然太過偏遠了。最初有人請他去當希坡主教時,奧古斯丁是相當不情願的。事實上他幾乎是被教眾們「挾持」過去的,他們覺得奧古斯丁是個值得緊緊抓牢的搶手貨。不久之後奧古斯丁即在教堂開展佈道,運用了曾經讓他在羅馬和米蘭聲名鵲起的全部技巧與手段。每個星期天,希坡的基督徒們都會一次站立兩個小時以上,他們均被這位演講巨星的話語所迷住。當老主教去世時,由誰來繼承他的位子當然是毫無疑問的。在奧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僅十年之後,他便被人神聖地奉為希坡的主教了。
這份工作並非在海邊沉睡小鎮的舒適閑職,希坡就如同北非大多數地方一樣,正處於奧古斯丁的天主教徒與多納圖派信徒之間的宗教戰爭之中。多納圖派是一個信仰嚴苛的基督教宗派,他們認為自己才是公元3世紀大迫害時期大量北非殉道者的真正後裔。雙方的爭鬥不僅局限於口誅筆伐,還有宗派間動真格的暴力威脅。每當奧古斯丁訪問遠在自己教區之外的地方時,他總是很害怕會被人施以私刑,對此他常常抱怨不已。雖說這樣的爭鬥足以讓奧古斯丁忙碌不暇,但前方即將來臨的挑戰才令他名垂青史。
公元410年夏末時節,令人震驚的消息傳至希坡,羅馬竟然陷落於阿拉里克國王及其西哥特軍隊之手。近些年來羅馬已經抵擋住了兩波圍城,但公元410年8月西哥特人第三次捲土重來,到了該月24日,奴隸們打開了城門,日耳曼軍隊遂如潮水般侵入,隨後便是整整三天的洗劫,羅馬許多最精美的建築都被搗毀了。偉大的奧古斯都的陵墓慘遭洗劫,埋葬起來的骨灰瓮被打翻,皇帝們的骨灰散落在大街上。接下來的數月里,希坡到處充斥著來自羅馬的難民,他們的心靈皆因城市陷落而深受創傷,許多人仰天長嘆:為什麼?為什麼這座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在歷經800年後居然最終落入蠻族軍隊之手?難民當中有不少人是基督徒,然而甚至在他們中間也有某些人開始猜測,20多年前皇帝狄奧多西褫奪異教的做法會不會跟今天這場駭人聽聞的事件存在某種聯繫。
這一說法在奧古斯丁看來簡直卑鄙可惡,教人怒不可遏。於是他積極展開行動,拿起筆一頭扎進論戰之中。奧古斯丁撰寫了一篇檄文,猛烈抨擊羅馬神話與傳奇,並編著了一部站在基督教角度、與傳說相對立的城市歷史,毫無禁忌地描繪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歲月,從當初善良的建城者到奧古斯丁時代那些頹廢、自私、金錢至上的公民。奧古斯丁堅稱,假如羅馬崩潰,那也是它命該如此。他向羅馬獻上了致命的最後一擊,詆毀羅馬熱切追求的根本理念,而實際上那也是古代世界所有偉大文明都渴望的理想。「俗世之城」均註定風雨飄搖並最終崩塌,因為它們都出自墮落的人類之手。

奧古斯丁耗費了13年的光陰才完成了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他認為文明的構築十分脆弱,其評價之消極可謂無出其右者。對奧古斯丁而言,在世俗之城裡根本找不到什麼目的和意義,只有上帝之城才會為人類提供這些精神要素,而它們只有在人死後才能觸及得到。在榮耀的解脫之前,正直的信徒在墮落的人類世界裡應如「朝聖者」般行為處事,充分利用文明所給予的和平與安寧,但切記不要錯誤地以為這是什麼堅不可摧或經久不衰的實質性事物。善男信女們只是人世間的匆匆過客,文明所創造的科技、文化和政治成就只不過是通向上帝之城的踏腳石,引領人們走向更偉大的榮光。
然而在奧古斯丁毫不妥協的文字背後隱藏著一個不容迴避的真相,那就是羅馬帝國仍舊十分重要,甚至對那些雄辯的詆毀者而言亦是如此。他們之所以能戰勝多納圖派信徒及其他基督教對手,其原因不僅僅是奧古斯丁寫的那些信件、佈道辭和論述所形成的「密集攻擊」,同時也是帝國法律體系的實施結果——國家依法關閉了那些宗派的教堂,封殺了他們的神職人員並對其教眾進行了罰款。其實奧古斯丁和他的非洲主教同僚們都在幕後大花力氣,他們遊說帝國官員,據說還賄賂過不少人。
像奧古斯丁這樣的傑出人物似乎不可能意識不到一個縈繞他著作的巨大悖論。他在《上帝之城》中所運用的雄辯術和推理術是如此威力強大,但它們並非研讀《聖經》的成果,而是源於當年那套極為昂貴的教育,而在那裡頭恰恰充斥著奧古斯丁竭力詆毀的經典文化。如此看來,這簡直是一幕大師級的「恩將仇報」。
當奧古斯丁憧憬天國時,他其實是以俗世之城為藍本來展開聯想的,這一事實可以有力地證明城市文明所具有的持久關聯性,而這種文明已統治了近東和地中海地區1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