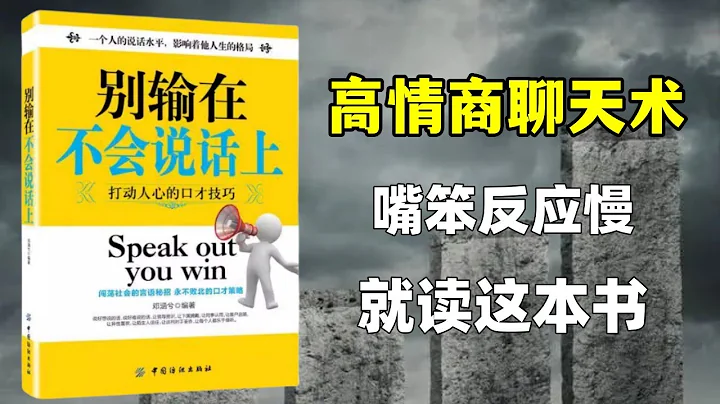自從哈爾濱這座充滿冰雪色彩的城市火了之後,全國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群蜂擁而至。當室內熱氣撲面與窗外風雪滿天的場景相映成輝之時,你是否想起過這樣一位來自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院士?
——他就是秦裕琨院士,他參與創立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鍋爐專業;他製造出我國第一台自然循環鍋爐至今依然被北方多地供暖使用。因為有他,才讓來自南方的「小土豆」們,來到哈爾濱這座冰雪之城,依然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滾滾熱浪。
耄耋之年,他依然活躍在講台上授課,他非凡的人生,向人們傳遞出我國第一代能源科技人才的無限魅力。

上海人在東北
秦裕琨是標準的上海男人,1933年5月出生於上海的法租界。在法租界內,他見識了身在中國的土地卻比外國人低一等的普世價值觀,他震驚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的貪腐猶如附骨之疽,蠶食著社會。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他正在讀高二,新中國的成立也讓他對祖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
1950年參加高考時,秦裕琨報考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製造系,當時他對這個專業完全不了解,之所以選擇這個專業,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說實話,當時我並不知道機械具體是做什麼的,只想著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要發展建設,需要強大的工業,而工業的基礎是機械。因為飛機大炮坦克是機械,汽車輪船火車也是機械,國家迫切需要機械方面的人才。」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大學生,秦裕琨提前一年畢業,當時本來他可以留在上海,留在父母和親人身邊。但他卻沒有這麼做,因為在他看來,與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相比,我國的東北、西北、華北等地更需要他這樣的人才。
於是在分配志願上,他鄭重其事地寫下了東北、西北和華北三個地方。因為當時中國和前蘇聯關係友好,前蘇聯支援中國建設很多工業項目,其中一大部分項目在東北。正因如此,當地急需像秦裕琨這樣的工業人才。於是他被選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做師資研究生。也就是要培養秦裕琨這樣的高材生做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教師,為新中國培養工業類人才。
或許南方「小土豆」們之所以喜歡去哈爾濱,是因為新奇,但要讓他們長久生活在這裡,恐怕大部分南方人都會「打退堂鼓」。秦裕琨卻從沒有打過「退堂鼓」。儘管他從小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環境里,沒經歷過哈爾濱零下四十度的冬天,也沒吃過棒子麵的窩頭,但他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裡卻看到了新中國工業崛起的希望。
每天都是新的,他們這批研究生其實做的每一項工作都是在創造歷史。
成為鍋爐專業的「小老師」
彼時的哈爾濱工業大學遠沒有今天這樣大的名氣,當時為了可以和前蘇聯的技術專家交流溝通,秦裕琨這批學生首先學習的科目只有俄語一門課。因為專業學科不完善,哈爾濱工業大學決定新設鍋爐專業,秦裕琨被選中成為跟著前蘇聯專家學習鍋爐專業。
雖然與秦裕琨之前學的機械專業截然不同,但他堅信,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這段過往,坦然地說:「我沒有專業,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專業。」
本來以為跨專業學習已經是一件非常有難度的事情了,但沒想到的是他不僅要跨專業學習,還要跨專業授課。而且其傳授的課程甚至是連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都沒有的鍋爐專業。
不到22歲的秦裕琨稀里糊塗地成為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小老師」。他講授的課程是「鍋爐與鍋爐房」。對於如何教好學生們,他煞費苦心。因為沒有教材,他只能跟著前蘇聯的專家提供的資料編寫俄文版教案,再讓專家審核確認後,自己翻譯成中文,將鍋爐方面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們。

秦裕琨開始現學現賣,就像孔夫子所講「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他每天除了要學習自己的課程,還要籌備給學生們的授課內容,還要為鍋爐學科的創建設計方案。在那個沒有電視、沒有手機的年代,秦裕琨幾乎很少在12點之前入睡,因為他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他需要為鍋爐學專業編寫教材。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他不知熬過多少個不眠之夜所創作的鍋爐專業的教材《蒸汽鍋爐的燃料、燃燒理論及設備》在1959年通過油印方式出版。在20世紀60年代初,這本內部教材由中國工業出版社正式出版,成為新中國鍋爐專業課程的第一本國家統編教材。
「秦總統」開啟工業鍋爐製造新篇章
秦裕琨有著年輕人的朝氣和不服輸的精神,他膽子大,又極具鑽研精神,時不時地將自己的奇思妙想「捅咕」出來,人們戲稱他為「秦總統」。
在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供熱鍋爐普遍採用蒸汽採暖,採用的是「強制循環」技術,需要用水泵不斷把水抽到鍋爐里,當水加熱後變成蒸汽再進入暖氣循環系統,以此方式為室內供暖,但這種方式的缺點明顯,就是熱得快,涼得更快,而且有一個致命隱患就是如果水泵因為停電無法工作,鍋爐就會因為承載不了過多的蒸汽而發生爆炸。而當時的中國停電幾乎是家常便飯一樣常見,給鍋爐的安全性問題帶來極大隱患。
所以,必須要對這種強制循環熱水鍋爐進行改造,因為要避開取暖季,鍋爐改造的時間也必須限制在4-10月之間。當時沒有人願意接下這個棘手的難題,沒想到「秦總統」卻欣然同意接下這個鍋爐改造的難題。

人們問他為什麼要接下這個難題時,秦裕琨笑著說:「要干就干別人幹不了的,要啃就啃別人啃不動的。鍋爐改造的難題沒人接,我才要接。」
接下這個難題,秦裕琨每天都在思考應該如何對鍋爐進行改造。他查閱多方資料,根據不同的鍋爐進行深入分析,一個初步的方案在腦海中成型——將蒸汽供熱轉化成熱水採暖。
有了思路後,秦裕琨便馬不停蹄地繪製改造圖紙,為了節省時間,他甚至直接搬到了鍋爐房吃住。經過兩個月左右時間的攻關,自然循環熱水鍋爐的圖紙草案終於出爐。緊接著,他帶領著學生和工人投入更加艱難的製造過程。最終他帶領著一群「工農兵大學生」團隊製造出了我國第一台自然循環鍋爐,由此掀開了我國工業鍋爐製造史上嶄新的一頁。直到今天,這種鍋爐依然是國內北方地區很多城市採暖的必備設備。
讓電煤清潔利用新技術領跑世界
隨著時代的變遷,1990年開始教育體制改革,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教研室開始劃分成若干課題組。有同事選擇了與秦裕琨相似的研究方向,為了豐富學科研究領域的多樣性,秦裕琨再次轉換跑到,轉向煤炭清潔利用領域。
當時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技術層出不窮,反觀煤炭領域似乎已經沒有可供研究的新課題。但秦裕琨卻並不這樣認為,因為他深知中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清潔能源的比重在當年只有不到30%,如果煤炭清潔利用技術沒有進展,對於全國的空氣污染治理都是不利的。

如何利用好國內大量的煤炭資源,如何能更清潔地利用這些煤炭資源成為已經到了花甲之年的秦裕琨面前的一道難題。
秦裕琨坦言:「能源與環境將是困擾我們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難題,中國的能源科技工作者就要研究中國的能源問題,我們要關注國際趨勢和熱點,但更重要的是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總跟在別人後面跑絕對不行!」
國際能源網獲悉,當時我國電力工業每年消耗煤炭近3億噸,但在電煤高效燃燒、低污染、低負荷穩燃和防結渣等技術科研方面一直未能取得重大進展。秦裕琨於是將研究領域聚焦在火電廠的煤粉燃燒技術上。
課題組剛成立的時候只有4個人,給他們的科研經費也極其微薄。這些困難秦裕琨和他的團隊並沒有放在眼裡,他們用了不到3年的時間成功在實驗室里實現了煤粉燃燒技術的應用。
但此後的秦裕琨卻面臨著沒有電廠願意採用這種僅在實驗室取得過成功的技術的又一道關口。對此,秦裕琨非常著急,因為他深知,如果這項技術僅僅存在於試驗室,對於國家的煤電產業的發展是沒有絲毫幫助的。
大煤電廠不敢用這種技術試驗,小煤電廠也紛紛表示拒絕,當很多人已經決定要放棄的時候,農星紅興隆管理局的一家電廠終於同意在一台幾乎要報廢的機組上應用這項技術。令人感到驚喜的是,通過應用這項新技術,一台舊得幾乎報廢的機組的熱效率甚至超過了新機。

他綜合「風包粉」和「濃淡燃燒」的設計理念,針對不同燃燒方式和煤種,開發出一系列濃淡煤粉燃燒技術,這些科研成果提高了鍋爐低負荷穩燃燒能力,降低了氮氧化物的排放,防止了結焦及高溫腐蝕,並保持了相當高的燃燒效率。這項技術的應用範圍也不斷擴大,幾乎遍布從東北到中原地區的絕大部分煤電廠。
經初步測算,僅在新技術推廣初期的2001年前後,秦裕琨團隊每年為社會創造的直接經濟效益就達1.3億元以上。
89歲高齡依然堅守三尺講台
如果說秦裕琨院士是一位「發明家」,不如說他是一位「教育家」更貼切。在哈爾濱工業大學,他執教的時間有68年。89歲高齡時,他依然堅守著三尺講台,給學生們傳道受業解惑。

他在擔任哈爾濱工業大學副校長期間,積極推動了學校的人才培養和教學改革工作,他率先提出實行學分制、因材施教等先進的教育理念,讓一批思想活躍、熱心改革的教師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自2019年12月起,秦裕琨院士還向哈工大教育發展基金會累計捐贈人民幣150萬元。同時,設立「秦裕琨基金」支持學科教育發展。
「『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校訓精神,一直深深影響著我……」秦裕琨院士回憶在哈工大學習生活數十年的經歷時,這樣表達了助力學校新百年發展的心聲。
90歲高齡之時秦裕琨院士依然沒有徹底賦閑在家,他依然會去學校參與研究生論文答辯、做學術報告等活動。
2023年11月13日7時35分,秦裕琨院士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逝世,享年90歲。
他濃縮了新中國第一代科研人的青春熱血,他就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走到哪裡,就在哪裡發光發熱,他的滾燙人生,值得人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