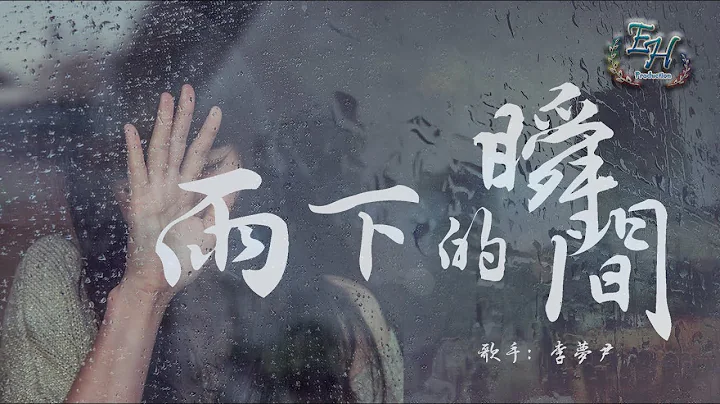文 | 習木方
編輯 | 楊旭然
相對於以前「大型企業走出去」的國家戰略,或者一些大量現金買買買的方式,這一輪新興企業的出海,是從產品、到技術、到品牌、到供應鏈生態全方位的出海。
比亞迪、拼多多、TikTok、SHEIN、雪王、海底撈等等明星品牌,都在海外干出了一片天地。
這背後離不開在國內高強度競爭中卷出來的內功,就好比能在中國全運會乒乓球、跳水等項目中里拔得頭籌的選手,到了世界大賽就是冠軍。
這輪出海熱潮有四個深刻的時代背景:
1.中國企業自身的資源整合能力提升
2.中國社會更加深刻的融入了國際化
3.後疫情時代通脹肆虐後的消費降級
4.中美貿易摩擦大環境下國際化退潮
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在完成自我整合之後,利用其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承接了西方進入創新經濟時代後轉出的製造業,而中國市場在經歷消化吸收外包生產的20年後,在全球市場考驗下,終於將彈性和效率統一。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國內統一市場,以及全球最完備、分工最細的供應鏈體系。其規模化、集約化和靈活性程度都是獨步天下。
而今,利用這套體系培養起來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成為了必然。正如內卷的字面含義,封閉空間已經無法承載中國的這套打法與能力,只有積極走出國門,才能獲得更大的市場、更高的利潤,同時也可以完成中國企業的自我升級。
把資源整合、打通全供應鏈的能力複製到海外市場,結合中國獨有高效大規模與靈活性,是中國企業出海最大的機會所在。SHEIN就可以用優衣庫、ZARA的打法與珠三角的大量「作坊式工廠」相結合,通過數字化整合就可以做到兼顧規模性和靈活性。拼多多出海的背後,則是依託於國內大量的白牌工廠,在前端整合供應鏈,在後端做好跨境電商平台的相關服務,最終形成槓桿效應。
風電、光伏、儲能類,也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依託中國製造,達到其產品的快速迭代和快速量產,提高了資金的周轉速度,最終在利潤微薄的情況下,硬是卷出了上萬億的海外市場。
01 雙向奔赴
出海空間雖大,但也並不容易。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折戟沉沙的故事了。
企業需要做大量的市場調研工作,目標市場的法律法規、人力資源整合、財務構架搭建、稅務籌劃等等方面,都是需要全面了解的地方。這個過程中還要完成組織的升級、文化的融入以及物流供應鏈的搭建,出海後還要將不同資源平台與公司自身供應鏈匹配......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後,才可能形成出海作戰的能力。
此前的出海潮流中,基本都是由海外巨頭搭橋拉線,完成最後的資源整合,這個過程中有非常成功的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收購幫助吉利完成了從內到外的升級,當然也有其他花費重金最終買回個「破爛」的慘痛經歷。

吉利收購沃爾沃是中企出海早期成功案例
而這一輪出海浪潮中,我們看到大量的相關服務公司都是華人背景。ToB的企業服務業務在這一輪出海浪潮中尤為亮眼,這些「工具業務」依託於早年積累和大量具有海外背景的華人人力資源,形成了一整套的出海服務生態。
自2000年後,中國對外交往的人員和生活在海外的華人華僑越來越多。同時,華人華僑在各國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在墨爾本、東京、多倫多、紐約等地,任一個有點規模的海外城市,都有當地的華人商圈,會計、法律、稅籌、物流等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優秀靠譜的華人來幫助國內企業對接,線上平台更是將溝通成本基本拉平到國內相同。
當人人都能看到遍地黃金時,賣鏟子自然就成了門好生意。
龐大的海外華人社區,不僅僅提供出海企業供給端的支持,更是在消費端熱烈捧場。每每有新的國內品牌出海開店,第一波消費都是在地的華人以及留學生群體,要知道這個龐大群體的消費能力在海外消費市場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可以很好幫助出海企業站住第一步。同時,大量的中國企業恰逢其時的出海,也給了部分華人以更多工作機會——典型的雙向奔赴。
02 徹底改變
全球疫情雖然告一段落,但其影響還遠未結束,並且深深改變了海外的市場。簡單來說就是海外消費者的兩部分改變:第一,接受電子商務,第二,需求更徹底的變化。
如同中國大陸市場在03年非典之後完成的對電子商務的全民認知,海外市場還是慢了好幾個節拍,但隨着疫情期間的封禁等情況,越來越多的海外大眾消費者開始接觸電子商務,包括美國市場在內,僅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過去十幾年才能達到的電商滲透率積累。

疫情封閉加速全球電商業成熟
另外疫情導致的居家辦公,讓大量的海外企業將採購、經銷等環節也都轉移到了線上進行,進而導致大量的海外零售商、批發商、經銷商、品牌商都開始通過線上重新搭建自己的供應鏈體系。這是一個極大的契機:市場大了,機會就多了,中國電商出海的優勢就更強了。
另一個改變就是海外消費者的需求變化。
這兩年海外生活最重要的體驗就是通脹,金融圈最熱的詞是加息。相對於08年次貸危機救市的不同,這輪全球救市大放水,不僅僅落實在貨幣政策中更是直接採取財政政策放水,說的直接點,就是政府直接把錢發給老百姓手中,幾萬億的資金以現金補貼的形式發放給「低收入人群」和小企業。這就造成了一個奇觀——疫情期間,西方世界的普通民眾的收入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
消費需求大漲的同時,而社會供給卻因為疫情等因素無法及時更上,通脹水平自然也是水漲船高。旺盛的需求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全球性通脹就這麼洶湧澎湃的擴散開來。
直到2022年3月,西方發達經濟體發現通脹已經接近7%-8%的高點,才開啟加息。澳洲也是在大選之後匆忙開啟極速加息的旅程。(18個月將利率從0.1%極速提升至4.35%)如此誇張的幅度,在同期別的發達經濟體中竟然屬於保守狀態。

近年來澳大利亞利率變化
後疫情時代的暴力加息與縮表,和疫情期間的降息與發錢之間形成了巨大的政策鴻溝,埋葬了巨大的流動性和低廉的生活成本。物價指數直線飆升,收入漲幅被通脹水平遠遠甩開,在房貸、車貸利息上的開支直接翻倍,政府社會福利開支大幅縮減……一句話「地主家也沒餘糧了」。
如今,大量的中產家庭開始追求低價高質的產品。而中國產品一直都是低價高質的代名詞,大量的平替產品生逢其時,絕對是中國企業出海的好時機。
03 搶灘登陸
自18年起的中美貿易摩擦,大大改變了世界貿易格局。美國不僅僅在高科技領域採取「小院高牆」策略,也在實體經濟端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在一眾鐵杆盟友中構建起一道道包括關稅壁壘在內的貿易保護之牆。
在供應鏈管理中,美國提出「中國+1」的策略。而這些措施迫使中國的許多企業被迫出海來規避政策風險。東南亞和墨西哥分別成為此類企業出海的橋頭堡。
套用孫正義的時光機理論,越南似乎就是20年前的中國,在資本管控等方面更是被大吹特吹。但現實是越南的土地價格與自己的發展程度完全不匹配,說是在泡沫化的邊緣也不為過。

快速發展導致越南經濟存在一定泡沫
另外相比中國,越南實在太過狹小,工業原材料大量依賴中國進口。企業出海越南主要是依託於中國供應鏈的溢出效應,和歐美市場對於中國原產地特別關稅。轉口貿易已經越來越不被越南政府認可,大量的加工製造企業出海越南,只是為了規避歐美市場針對中國原產地加征的特別關稅。
製造業方面,越南製造用上全套的中國設備和管理,性價比其實和國內生產並沒有太大差距,但越南沒有配套的原材料加工市場,規模完全和中國不在一個量級上。中國光伏企業在東南亞地區出海的過程中,這一點體現得非常充分。
從積極的一面看,總的來說東南亞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低,適合發展製造業,GDP增速快,消費群體處在消費升級的節點,本地市場潛力不小。以當地為跳板,可以將生意擴展到北美、歐盟地區。東南亞地區最成功的國家新加坡,更可以成為中國出海企業的高端人力資源庫,以及金融、科技、互聯網信息服務的中心。
在民間資本積極開拓東南亞市場的同時,國字號背景也在深耕當地市場。諸如雅萬高鐵等標誌性項目的落地,都會極大拓展中國製造與中國品牌的公信力,讓出海的中國企業更有信心去面對處理複雜的外部生態。
第二個橋頭堡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是中企進軍美洲的要地
出海墨西哥的初始階段,也是以零售貿易為主,但隨着中國工業實力的提升,順其自然的複製了當年日本企業為規避貿易壁壘轉戰墨西哥的基本操作,以享受《美墨加協議》下的關稅優惠。美國在2021年公布《美國供應鏈行政令》中更是鼓勵美國企業將業務外包給鄰近地區,馬斯克就曾不止一次的希望特斯拉在中國的配套公司去墨西哥建廠。
福耀玻璃這類運輸成本比重高的公司更是將工廠直接建在美國,利用能源、土地、運輸等優勢來抵充人力資源上的成本,發展越來越好,目前在北美地區的市場佔有率已經超過25%,其產品一直處在供不應求的狀態。
04 步步險灘
如今東南亞、南美、非洲等新興市場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日趨走向完善,而且移動終端也基本完成了普及,當地移動互聯網市場蓬勃發展,時光機理論又可以在這些市場重現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井噴、產品下沉的一幕。
而中國創新企業產品更新速度快,注重用戶體驗與社群建設的打法,必然開拓出一個巨大且確定性高的藍海市場。米哈游、IGG、三七互娛等一眾互聯網公司快速佔領市場就是最好的例證。

中國手游出海已經繁榮多年
在大量企業出海成功的同時,更要看到出海並非一帆風順,尤其是在地緣政治影響越來越嚴重的當下,更可以說是步步險灘。沿用國內成功經驗的同時,也將一些客觀存在的問題帶了出去,如流量亂象、加班文化、忽視創新與品牌建設,不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等等。
這些雷有的已經爆了——如亞馬遜大規模封號事件造成超千億的損失,印尼封殺直播帶貨,歐盟對於中國出口電動車的補貼政策進行調查等等,而有些則會在未來幾十年內長期挑戰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另外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是,這幾年國內輿論太過重視越南,又太過輕視印度。一提印度大家往往想到就是三件套「沒有秦始皇、沒有土地改革、沒有工業化」,甚至有人說印度社會還處在前現代化狀態。
但實際情況是,印度在過去幾年因為地緣政治紅利備受全球資本追捧。目前在鋼鐵、水泥等傳統支柱行業產能中成為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的存在,汽車產能世界第三,智能手機產量世界第二——果鏈轉移到印度的影響已經是門顯學了。

印度電子業已歷經多輪發展
僅次於中國製造的超大規模,疊加高附加價值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再加上在國際高端人力資源中的儲備,可以看出印度有潛力發育出中國一樣的全產業鏈。印度GDP將在9年內翻一番,預計在2030年左右,印度將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與此同時,其中產階級也預計將達到8億人,從而形成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
印度製造能力+本地消費優化+西方市場遠景,已初見端倪。
這輪印度的紅利期過程里,中國企業在印度市場異常艱難,「小米被搶」的故事時有發生,乃至引起公憤。一個不太友好但是國力迅速上升,並且將中國列為頭號競爭對手的印度,將會是從官方到商界未來幾十年始終要面臨的問題。
05 寫在最後
中國企業在這輪出海潮中,還有太多的優勢可以發掘,太多的短板可以填補。
中國企業、商品更多仍然依託於自身的資源稟賦,將品牌和資本力量集中在消費、互聯網領域,這其實是中國企業的傳統優勢。強如TEMU和SHEIN,也只是在強化中國製造的基本盤。
而那些大額、昂貴、更需要消費者信任的「大件商品」,仍然有不小的提升空間,就像剛剛開始的汽車出口浪潮,正在逐漸扭轉低端形象的家電、手機、電腦,未來可能會大規模向外輸出的芯片、面板等等。
這些高價商品背後有千千萬萬個供應鏈企業,這些或大或小的製造業單元,支撐着中國品牌、中國製造在全球的繁榮,這其中的財富機遇不計其數。
有人說內卷是一種不允許失敗,也不允許退出的競爭,但真實的出路其實已經被一波又一波的中國企業趟了出來——通過走出去完成更加徹底的自我進化,真正戰勝內卷。
像極了那句「除了勝利,我們已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