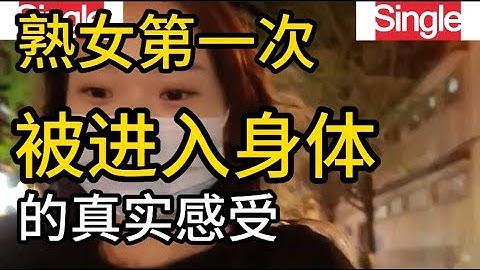2023年春季,八年級下的語文教材進行了調整,最突出的內容為,在「名著導讀」部分,將《傅雷家書》替換成朱自清的《經典常談》。
而這個消息也引發各方的關注,最顯眼的就是圖書市場。比如某出版社的《經典常談》首印雖只有5000冊,但目前加印到第8次,發行量近20萬冊,出版方表示,隨着該書被收入教材,近期還會計劃加印。
看來教科書依然有着很強的風向標作用。一入教科書,就彷彿身價倍增,人們趨之若鶩。這也展現了教科書的「力量」,它能快速形成一種導向,引領大眾的閱讀。
《傅雷家書》和《經典常談》我都讀過,也都堪稱經典。《傅雷家書》人們都很熟悉,這本親子之書影響了無數人,作為父親的深情、作為學者的思索,都在簡牘中的字裡行間,娓娓道來卻又動人心腸。就像傅聰說的:「翻翻家書,我就會淚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整天若有所思,很難再工作下去。」被打動的,又何止是傅聰呢?
《經典常談》其實是一本介紹經典的入門書,告訴當時「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該讀哪些經典,以及怎麼讀這些經典。語言簡單、平實,很適合作為一種入門讀物。但翻翻這本書的寫作時間——1942年,以及落款里「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聯想那個時代背景,不難想見作者的心曲:在一個風雨如晦的年代,讓人們讀國故經典,以增強人們堅定的信念。
毫無疑問,這兩本書都是好書,但教科書的篇幅終究是有限的,選了這篇就不可避免地會落下另一篇,這都很正常。人們非常關注教科書,多一篇少一篇都會引發很多關注。但其實,教科書又怎麼可能窮盡經典?換句話說,讀經典又何必局限於教科書呢?
我記得上高中的時候,語文老師在早讀課上都會在黑板上寫一首不在教材里的「課外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寫了一首宋代劉過的《唐多令》,最後幾句我到現在都能張口就來:「黃鶴斷磯頭,故人今在否?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
早讀課時間短,老師也沒時間細講,就當是個補充知識,重點是學生自己體會。我那時看着黑板上的這些詩,自己也讀得似懂非懂,但詩里的韻味卻在腦海中揮之不去。我到現在還記得,在那些本該打瞌睡的早晨,我興緻盎然地抄着這些課外詩。我也很感謝高中語文老師,是讓他讓我知道了課本之外還有那麼多美好的詩詞,也讓我養成在課本之外多看兩眼的習慣。
教材終究是管中窺豹的指引,被選入教材,是一種客觀上的「必讀」;但未被選入教材,也絕不意味着「不必讀」。把經典閱讀當成一種習慣,或許也就沒有必要那麼糾結了。就好像前不久有專家解釋,岳飛的《滿江紅》從來未選入過中學教材,但這絲毫不會影響《滿江紅》的流行。
當然,如果我們「多看兩眼」,岳飛其實還寫過一首《小重山》,風格完全不同。「欲將心事付瑤琴注。知音少,弦斷有誰聽。」這些婉轉雋永的句子,讓橫戈躍馬的岳將軍形象又豐滿了一些。
這些或許都不在教材里,但確實足夠經典。經典浩瀚,教材終究只能取一瓢飲。何況我們關注的教材,也多是中小學,而經典的閱讀時長,可以是人的一生。經典能給予我們的,其實遠遠超過課堂與考試。
工作以後,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他自己寫的關於《孔從子》的書。《孔從子》是記錄關於孔子及其後人事迹和思想的諸子著作,我之前都不知道原來還有這麼一部經典。
我翻着這本書,生澀的古文似懂非懂,但也禁不住想,經典何其淵深,我們又如何能夠窮盡?所能做的,也不過是「多讀一本是一本」,在足夠廣闊的時間裏,一點點接近知識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