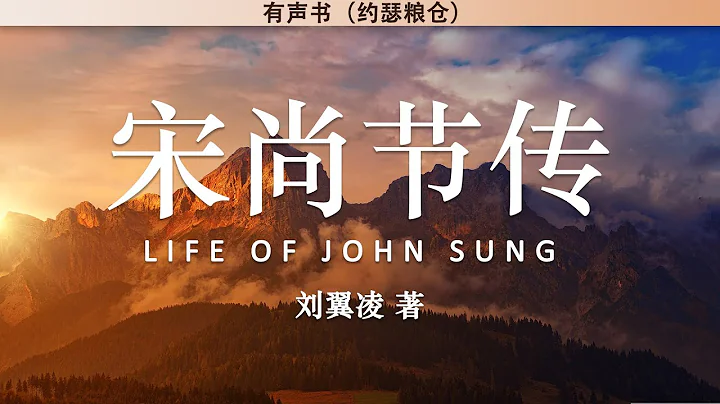理查德·菲利普斯·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1988),美籍猶太裔物理學家,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教授,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

費曼1939年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1942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旋即加入美國原子彈研究項目小組,參與秘密研製原子彈項目“曼哈頓計劃”,時年24歲。
費曼提出了費曼圖、費曼規則和重正化的計算方法,這是研究量子電動力學和粒子物理學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被認為是愛因斯坦之後最睿智的理論物理學家,也是第一位提出“納米”概念的人。

本文是費曼在美國科學院的一個演講, 深入淺出、客觀理性又激動人心。
本文譯者李沉簡,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譯者說:
這篇文稿翻譯於弗羅倫薩,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刻。
近二十年前,我和妻子徐楊充滿享受地翻譯費曼的書,而書的最後一篇就是這篇講演詞。那時我們還沒有手提電腦, 兩年中我們的背包里一直隨身帶着費曼的書和筆記本, 走到哪裡, 寫到哪裡。在我結束了一個在德國海德堡的合作之後, 遊歷意大利到了弗羅倫薩, 這個文藝復興的文化和歷史集萃之地。在弗羅倫薩城隔河的小山上, 米開朗基羅的第三個《大衛》帶着世紀的勇氣,靜靜地俯瞰全城。雕塑腳下有個咖啡館,於是我坐下來歇腳, 隨手拿出費曼的書,打算翻譯一些再繼續旅遊。可是當我寫下幾段之後, 就完全無法停止,費曼幾乎就在我的面前。整個下午, 我一氣呵成翻出了整個篇章。在結尾的時候天色已經黃昏;金色夕陽下的弗羅倫薩突然間全城暮鍾如潮。夕陽、弗羅倫薩、《大衛》、費曼,大概世間不會有太多更讓人激動/有幾近宗教神聖感的瞬間了。
二十年後重讀費曼, 依然擲地有聲。與諸君共享。
科學的價值
文 | 費曼
譯 | 李沉簡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認為科學會有利於每個人。科學顯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參與了原子彈的製造工作。科學的發展導致了原子彈的產生,這顯然是一個具有極其嚴肅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對人類的毀滅。戰後,我對原子彈憂心忡忡,既不知未來會怎樣,也更不敢肯定人類一定會延存。自然地,一個問題會這樣被提出:科學是不是包含着邪惡的成分?這個問題也可以這樣來問:當我們看到科學也可以帶來災難時,那麼我如此熱愛,並且畢生孜孜為之的科學事業的價值究竟何在?這是我無法迴避的問題。這篇“科學的價值”,你們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這個問題時的所思所悟。——理查德·費曼
時常,人們對我提出,科學家應該多多關心社會問題,特別是要考慮科學對於社會的影響。人們似乎相當普遍地認為,只要科學家們對於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加以關注,而不是成天鑽在枝尾末節的科學研究之中,那麼巨大的成功就會自然到來。
我以為,我們科學家是很關注這些社會問題的,只不過我們不是把它們當作自己的全職而已。其原因是,對於這些比科學研究複雜千百倍的社會問題,我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絕無靈丹妙藥。
我認為當科學家思考非科學問題時,他和所有的人一樣無知;當他要對非科學問題發表見解時,他和所有的門外漢一樣幼稚。今天我的講演“科學的價值”所針對的並不是一個科學課題,而是價值評判;這樣看來,我下面將要講的大概也是粗淺不堪的了。
01
科學的價值的第一點是眾所周知的。科學知識使人們能製造許多產品、做許多事業。當然,當人們運用科學做了善事的時候,功勞不僅歸於科學本身,而且也歸於指導着我們的道德選擇。科學知識給予人們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惡,它本身可並沒有附帶着使用說明。這種能力顯然是有價值的,儘管好壞決定於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學會了一種方法來表達上述問題——一個佛堂的主持向遊客們談及佛學,最後他說他的臨別贈言將使遊客們永不忘卻(我是真的從未忘卻)。這贈言是佛經中的一句箴語:“每個人都掌握着一把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這把鑰匙也同樣能打開地獄之門。”
如此說來,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又有什麼價值呢?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分辨一扇門是通向天堂還是地獄,那麼手中的鑰匙可是個危險的玩藝兒。
可是這鑰匙又確實有它的價值——沒有它,我們無法開啟天堂之門;沒有它,我們即使明辨了天堂與地獄,也還是束手無策。這樣推論下來,儘管科學知識可能被誤用以導致災難,它的這種產生巨大影響的能力本身是一種價值。

02
科學的另一個價值是提供智慧與思辨的享受。這種享受一些人可以從閱讀、學習、思考中得到,而另一些人則要從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滿足。這種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們忽視,特別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導我們科學家要承擔社會責任的先生們。
我當然不是說個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學的全部價值所在。不過,如果我們社會進步的最終目標正是為了讓各種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麼科學家們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個不容低估的科學的價值是它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概念。由於科學的發展,我們今天可以想象無窮奇妙的東西,比詩人和夢想者的想象豐富離奇千萬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類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詩人想象巨大的海龜馱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學給了我們一幅圖畫——天宇中一個巨大的球在旋轉;在它的表面,人們被神奇的引力吸住,並附着它在旋轉。
我常常想這些奇妙的東西,這些從前人們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學知識使我們可以想象的東西。
曾經,我站在海邊的沙灘上,陷入了這樣的深思:
潮起潮落無法計數的分子各自孤獨地運行相距遙遠卻又息息相關泛起和諧的白浪曠代久遠在尚無生物的上古眼睛還未出現年復一年驚濤拍岸如今為了誰,為了什麼?在一個死寂的星球沒有為之欣悅的生命永無休止驕陽彌散着能量射向無垠的宇宙掀動着大海的波浪大洋深處分子重複不變忽然,萌生新的組合它們會複製自身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愈變愈大愈變愈複雜生物,DNA,蛋白質它們的舞蹈愈加神奇躍出海洋走向陸地站立着具有認知力的原子具有好奇心的物質憑海向洋一個好奇者在好奇我——一個原子的宇宙一個宇宙中的原子
這樣的激動、驚嘆和神秘,在我們研究問題時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知識的進步總是帶來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們去更深一層地探索。有時探索的結果令人失望,可這又有什麼關係?我們總是興緻勃勃而自信地深鑽下去,發現無法想象的奇妙和隨之而來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這難道不是最激動人心的探索么!
誠然,沒有過科學研究經歷的人大概不會有這種近似宗教的感受。詩人不會寫它,藝術家也無法描述這種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難道他們都不為我們所發現的宇宙所激動嗎?歌唱家現在還不會歌唱科學帶來的神奇美妙,科學對於人們來說還是在講課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詩與歌之中。這說明我們還沒有進入一個科學的時代。
這種沉默無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們必須懂得如何讀這種音樂的樂譜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學論文說,“鼠的腦中放射標記的磷在兩周中減了一半。”這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腦中(你、我的腦子也沒什麼差別)的磷有一半已經不是兩周前的原子了,它們已被替換了。那麼我要問:“究竟什麼是載有意識的分子呢?子虛烏有么?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載一年前在我腦中的記憶,可當時發生記憶的分子卻早已被置換了!這個發現就像是說我這個體僅僅是一個舞蹈的編排。分子們進入我的大腦,跳了一場舞就離開了;新的分子又進來,還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樣的舞蹈——它們能記住!”
有時我們會從報紙上念到這樣的話:“科學家認為這項發現對於治療腫瘤是十分重要的……”。看,這報道只注重那項發現有什麼可利用之處,而完全丟開了它本身的意義。而實際上它是多麼奇妙啊!偶爾,小孩子反倒會意識到那些意義;此時,一個科學家的苗子出現了。如果當他們上大學時我們才教他們這些,那就太晚了。我們必須從孩童教起。

03
現在,我來談談科學的第三個價值——它稍稍有些間接,不過並不牽強。科學家們成天經歷的就是無知、疑惑、不確定,這種經歷是極其重要的。當科學家不知道答案時,他是無知的;當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測時,他是不確定的;即便他滿有把握時,他也會永遠留下質疑的餘地。承認自己的無知,留下質疑的餘地,這兩者對於任何發展都必不可少。科學知識本身是一個具有不同層次可信度的集合體:有的根本不確定,有的比較確定,但沒有什麼是完全確定的。
科學家們對上述情形習以為常,他們自然地由於不確定而質疑,而且承認自己無知。但是我認為大多數人並不明白這一點。在歷史上科學與專制權威進行了反覆的鬥爭才漸漸贏得了我們質疑的自由。那是一場多麼艱辛、曠日持久的戰鬥啊!它終於使我們可以提問、可以質疑、可以不確定。我們絕不應該忘記歷史,以致丟失千辛萬苦爭來的自由。這,是我們科學家對社會的責任。
人類的潛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來未免神傷,總覺得人類可以更好。先人在惡魘中夢想未來;我們(正是他們的未來)則看到他們的夢想有些已經成真,大多卻仍然是夢想,一如往日。
有人說教育的不普及是人類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難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為伏爾泰嗎?壞的和好的是同樣可以被傳授的;教育同樣擁有趨善或趨惡的巨大能力。
另一個夢想是國與國之間的充分交流一定會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縱的。如此說來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實,也可以是謊言。交流也具有趨善和趨惡雙重可能。
應用科學可以解決人們的物資需求,醫藥可以控制疾病——看上去總算盡善盡美了吧?可偏偏有不少人在專心致志地製造可怖的毒物、細菌,為化學生物戰爭做準備。
幾乎誰都不喜歡戰爭,和平是人類的夢想——人們儘可能地發揮潛能。可沒準兒未來的人們發現和平也可好可壞。沒準兒和平時代的人因沒有挑戰而厭倦不堪,於是終日痛飲不止,而醉熏熏的人並不能發揮潛能、成就大業。
和平顯然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如同嚴謹、物資發展、交流,教育、誠實和先人的夢想。與先人相比,我們確實進步了,有更多的能力了。可與我們能夠成就的相比,所達到的就相形見絀。
原因何在?為什麼我們就無法戰勝自己?
因為我們發現,巨大的潛能和力量並沒有帶着如何使用它們的說明書。譬如,對物質世界認識愈多,人們就愈覺得世界真是毫無目的意義可言。科學並無法指導行善或行惡。

04
有史以來,人們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義。他們想:如果有某種意義和方向來指導,人的偉大潛能定會充分發揮。於是有了許多種對生命意義的闡述和教義。這些各自不同的教義有着自己的信徒,而某一種教義的信徒總是懷着恐懼的心情看待其餘教義的信徒。這種恐懼來自於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發點都匯入了一條死胡同。事實上,正是從這些歷史上錯誤信仰所製造的巨大謬誤中,哲學思考者們慢慢發現了人類美妙無限的能力。人們夢想能發現一條通途。
那麼,這些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如何來解開存在之謎呢?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們不知而我們今天所知的——那麼我認為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還是知之甚微。
不過,正當我們如此承認的時候,我們便開始找到了通途。
這並非一個新觀念,它是理性時代的觀念,也正是它指導着先賢們締造了我們今日享用的民主制度。正因為相信沒有一個人絕對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們才有這樣一個制度來保證新的想法可以產生髮展、被嘗試運用、並在必要的時候被拋棄;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輪迴運行。這是—種嘗試——糾偏的系統方法。這種系統方法的建立,正是因為在18世紀末,科學已經成功地證明了它的可行性。在那時,關注社會的人們已經意識到:對各種可能性持開明態度便帶來機會;質疑和討論是探索未知的關鍵,如果我們想解決以前未能解決的問題,那我們就必須這樣地把通向未知的門開啟。
人類還處在初始階段,因此我們遇上各種問題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來還有千千萬萬年。我們的責任是學所能學、為所可為、探索更好的辦法,並傳給下一代。我們的責任是給未來的人們一雙沒有束縛自由的雙手。在人類魯莽衝動的青年期,人們常會製造巨大的錯誤而導致長久的停滯。倘若我們自以為對眾多的問題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年輕而無知的我們一定會犯這樣的錯誤。如果我們壓制批評,不許討論,大聲宣稱“看哪,同胞們,這便是正確的答案,人類得救啦!”我們必然會把人類限制在權威的桎梏和現有想象力之中。這種錯誤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偉大的進展都源於承認無知,源於思想的自由。那麼這是我們的責任——宣揚思想自由的價值,教育人們不要懼怕質疑而應該歡迎它、討論它,而且毫不妥協地堅持擁有這種自由——這是我們對未來千秋萬代所負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