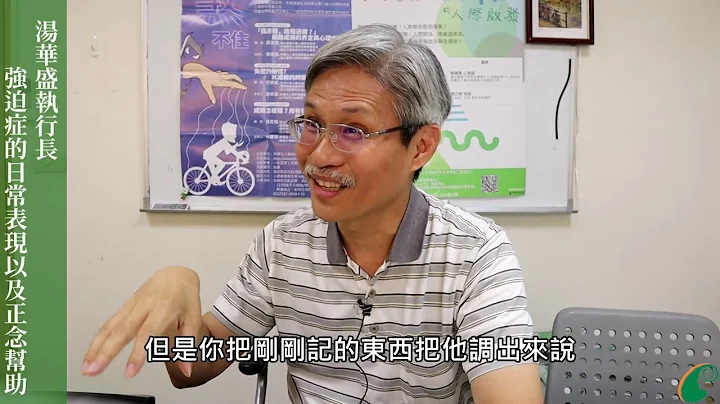自我定位
有這樣一部美國電影《機動殺人》,講的是一個連環殺手,專挑與自己體型相仿的人下手,然後偽造對方的齒痕,髮型,甚至是指紋,冒充受害人生活一段時間,膩了之後再隨機找到下一個地方重複作案。
片中的FBI在調查這個案件的時候給這個罪犯如此的心理分析:
大鬍子也可能只是他一個暫時的身份
換句話說,現在馬丁幾乎可能是任何人
像寄居蟹一樣不停地尋找可以寄居的殼
他只有冒充別人才能忘掉自己
殺人是為了獲得死者的身份,冒充他們繼續生活
這是個極端厭惡自我的人

他厭惡自己的原因是,他有一個雙胞胎哥哥,但媽媽卻一直喜歡哥哥而不喜歡他,而14歲那年哥哥因為意外溺水身亡,而媽媽就一直認為是小兒子的錯,所以就把他關進了一間密室或者說是牢房。從此小兒子性情大變,最後離家出走。
當然,影評可以說他殘忍,扭曲,變態,不值得同情一類。但試想一個不被愛的小孩如果不成為另一個人,那麼他如何面對一個被嫌棄的自己?
所有的神經症或犯罪心理幾乎都可以找到原生家庭的問題,而最主要的就是不被愛,沒有安全感。因為不能接納自己,所以就會在內心中構建一個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並認為現實中的自己是不該有的存在。一位患者寫到:因為從小被媽媽罵垃圾,廢物,不被接納,所以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自卑已經定型,而自信就是一種強迫性塑造的自欺欺人,自己覺得自己厲害。
因為父母剝奪了他作為一個人的權利,所以他必須要成為一個神,但當他沉浸在神的幻想之中的時候,那麼他就徹底和真實的自己決裂了。此時,他也許不敢看小時候的照片,覺得那個孩子很呆,很醜,很傻;他不想回憶自己的過去,覺得自己的過去充滿了黑歷史和屈辱,他也不會和別人提起,甚至會把過去的朋友刪掉,一方面他擔心別人瞧不起他,另一方面他不想回憶起那些不堪回首的過去。一旦有事情做不好,他就會罵自己是一個無能的廢物,別人對他友好他也會有一種自己不配的感覺。有時,他會認為不是自己無法接受自己,是別人無法接受自己,是身邊的人都憎恨自己,瞧不起自己,甚至認為別人咳嗽,都是在針對自己。
如果不打破理想化的自我的幻想,那麼一切自我接納都是自欺。
我是誰?是那個自認為的偉大的人,還是現實中那個渺小的人類;是人品端正的聖人,還是依然具有各種人性的黑暗面的普通人;到底是一個完美的神,還是有着各種缺點與不足的的凡人;到底是無所畏懼的強者,還是一個膽小的人;自己到底可以掌控一切,還是最終只能被命運所掌控?
而這一切的答案關乎一個人的人生走向,關乎一個人最根本的人生追求,也關乎他與自我,與他人及這個世界的關係。畢竟,當我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價值所在,邊界所在,那麼我們就不會妄自尊大,也不會妄自菲薄;不會因為別人的評價來決定自己的價值,也不會為了聖人般的道德來束縛自己的人性,此時我們可以面對現實,接納自己。
當一個人不能正確地看待他自己,無限地把自己美化,並把自己放在了他所不是的高度,並以此來衡量自己的價值,進而貶低別人,那麼他必然會在內心中產生各種衝突。但不明所以的人依然堅持自己沒有錯,錯的只是這個不如意的人生與不可控的現實。
神經症的癥狀的表現可能各有不同,但究其根本就是他不能擺正自己的位置,不能正確地看待自己,不敢成為他自己。只要你生活在孤芳自賞的世界裡,你就無法真實地看待你自己。夢幻與真實之間並無橋樑,通常他們的差異過大而不容有任何妥協,而且只要你無法真實待己,生活在想像的偉大“自我中心”中,我們就不再關心我們自己的真相。
治療是為了找回自我,但到底找回的是哪個自我呢?是他想象中的完美自我,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自我呢?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那麼在治療的路上必然會南轅北轍。
但對患者來說,這個被他創造出來的自我,甚至真實的他更為真實,他不能相信這一切是假的。實際上,對於食品加工,金融詐騙等以假亂真的手段我們可能會了解,但對於如何創造出一個虛假的自我卻知之甚少,下面就分析下這個虛假的自我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
1、 想象
一般而言,“我是誰”來自於的現實反饋,但對於“被嫌棄的小孩”來說,他無法依靠真實的自我來生存,所以他只能在想象中去創造一個自我,這個自我可以幫助他應對無力應付的環境。就如同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給自己創造了幻想的情景與人設。
想象是這一切的開始,此時他只是看了某部電影或一本書,他就可以把自己幻想成為其中的主角,而這種幻想給了他在現實中所沒有的力量感與掌控感,所以他更喜歡沉浸在幻想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現實里。但這樣的結果卻是他會慢慢的模糊了現實與幻想的距離。
雖然他並沒有完全脫離實際,但因為潛意識中對安全與價值強烈的渴求讓他忽視了客觀現實的檢驗與反饋,而錯誤地把這個幻想中的自己當成是客觀存在。而從此之後,一切都變得不同了,原本用來實現自我的精力,結果都用到了維繫這個虛假自我身上,他的精力被極大的浪費,他的生活也因此脫實入虛。
2、成功的經歷
虛假自我的創造並非是沒有任何現實依據,神經症患者依然和現實有着接觸,他的自我的評價依然有部分的現實依據。諸如,他小學的時候是班長,大隊長,第一名,好學生,別人家小孩,企業家,成功人士,好人形象,道德聖人,良好人際,好的口碑。
但這一切又並非全部來自於現實,畢竟人生就是一種敘事,你可以選擇性地看見什麼,或忽視什麼。一位患者在諮詢中就提醒我:你有沒有發現,我總是談起我成功和勝利的經歷,但實際上我也被別人打過,但我卻沒有和你說。
並且,某一方面的成功,也不意味着各方面都比別人強,但神經症患者卻容易因為一個點而放大成整個面。他會因為學習,掙錢,籃球,人際,唱歌,外貌等某方面的閃光點而認為自己整個人就是卓爾不群的。並且,某一時期的順境並不能代表這個人就會一直比別人強,畢竟這只是某個特定時期的產物,例如,小學初中學習數一數二,但到了高中或大學就不見得能保持優秀。但他卻不能隨着境遇的改變而調整自我的定位,他往往會把自己的順境定格,認為那時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認為之後的失敗是因為癥狀,或是因為自己沒有努力,他就是不願承認事實上他並沒有他認為的那樣出類拔萃。
有時,他的比較也缺乏公平,舉例來說,他往往會認為自己是唱歌裡面跳舞最好的,而跳舞裡面唱歌最好的;學習裡面籃球最好的,而籃球裡面學習最好的。例如,一位患者認為比他掙錢多的人沒有他有文化,而比他有文化的人沒有他掙錢多,所以他就是最厲害的。但這種比較沒有任何意義,他只是通過這種自欺的把戲把自己抬高到一個無以輪比的高度。
這一切帶有很強的主觀性,所以,一位女性患者告訴我,她想明白了一件事,雖然在這個單位,在這個部門她是最優秀的,但平心而論的話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畢竟她只是在市級單位,但如果是省級呢,如果是全國呢?實際上她可能都排不上號,此時她才意識到自己並沒有自己認為的那麼優秀。
所以,患者實際上不是活在過去,就是活在未來,而不是活在當下,他只是活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期,並把那時的優秀,當成了自己不凡的理由,但如果這個成立的話,是否我們也可以因為唐朝的輝煌而洋洋自得?顯然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就算他活在了當下,但他卻也放大了自己的成就,而沒有認識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這隻能說明某方面的優秀,但不意味着整個人的卓爾不群。
3、阿Q精神
“阿Q精神”是一種自我安慰的精神。簡言之,是使用精神勝利法進行自我安慰。
當一個人在“正路”無法維繫幻想中的自己,那麼就會走“小路”。比如,當他怎麼努力都無法達到他期望的優秀的話,那麼他可能就會把價值的支撐建立在打遊戲上;如果他無法通過主流的方式得到別人認可,那麼他可能會成為學校的校霸,通過打架來讓他顯得厲害;如果他不能在成就上超過別人,那麼他就會試圖通過外貌或身材來取勝;如果他不能通過自己來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那麼他可能就會依賴一個有能力的異性來減輕他的自卑;如果一個人不能通過天賦來獲得別人關注,那麼他可能選擇嘩眾取寵來博取眼球。
如果連這些都沒有,那麼他就全憑精神勝利法了。例如,一位高中生,每天都第一個跑下樓梯,如果他是最快的,那麼他就會洋洋自得,認為自己是學校體育最好的人。他還會在同學放學之後練習立定跳桌子,如果成功他就覺得自己比同學都厲害,因為沒有人跳的過去。我提醒他,也許這個根本就沒有人在乎,除了他自己;而另一個男孩是大專生,不過他卻認為作為本科生的女友沒有他有文化,當問他是如何判斷自己比女友更有文化的時候,他談到因為他看過豆瓣top250的電影,看過很多世界名著。我笑道:如果這意味着一個人有文化,那麼還考什麼大學。
當一個人故意欺騙自己,扭曲現實,那麼他能因為任何一點無足輕重的理由而自負,能因為他甚至不具有的美德來自我標榜。總之,當一個人試圖給自己臉上貼金的時候,就算貼上的是黃土,他都覺得自己是世上最美麗的人。這一切也像極了《阿Q正傳》的情節,阿q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什麼人都能欺負他,可他卻並不在乎,常常好像還很得意,因為他有一種獨特的精神勝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卻想:這是兒子打老子。
一個人的能力與地位要在與現實的交互中獲得,但對於神經症患者來說,通過精神勝利法他就獲得了一切,最終他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了一個笑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小丑。
4、模仿與表演
我們都知道電影中的演員只是在表演,那並非真實的他。但對神經症患者來說,他卻總是忘記了這一點,他把表演出來的形象當成了他自己,並因此自我標榜,輕視別人。
他會模仿那些成功的人,那些受人歡迎的人,也會模仿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好學生,好員工,好愛人,好朋友,好孩子,一個好人。他會表現的對人友善,對父母孝敬,對小動物充滿愛心,對事業充滿熱愛與負責的精神,也會表現的寬容,大度,不自私,悲天憫人。雖然這一切都是表演的,而非發自內心的,但他卻把這當成了真實的他自己。
但這樣就會出現很多後果,首先就是兩面性,他會在外面會樂善好施,但對待自己的家人卻尖酸刻薄;他在外在表現的乖巧聽話,但內心卻離經叛道;表面上他可能喜歡每一個人,但內心深處卻沒有愛。第二,矛盾性,他雖然可以表現的大度,寬容,為別人着想,但內心中卻壓抑了很多憤怒與不滿,畢竟他只是表演的很好,但不代表他真的不在乎,內心沒有情緒。
表演的與真實的畢竟不是一回事,對於真實自我來說,因為他是人性的表達,他可以依據自己當時的心情與需要做出自己認為對的選擇與判斷,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但對於模仿與表演的人來說,他只是為某種人設的需要而做出某種行為,而這並非來自於內心的情感,只是一種表演,所以必然會與他的人性發生衝突。
5.人生追求的偏差
人活着到底是為了什麼,到底是為了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愛自己所愛的人,還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強,維繫虛榮心和優越感?
對於不敢面對真實自我的人,他就容易追求一些很虛的東西,結果丟失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部分。他可能為了被別人看得起,而買一些昂貴但卻不實際的東西,比如名牌的手機,包包,汽車;他可能試圖維繫生活的品味與逼格,花費大量的金錢,但卻沒有多少儲蓄;他可能會試圖尋找更漂亮的,可以給他虛榮心滿足的異性,但卻錯過了真正適合他的人;他可能交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朋友,但卻沒有幾個真心朋友;他可能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美容,健身,考證上,這樣就會讓他看起來更完美,但實際上他並不喜歡這些事情;他可能會把金錢與地位看的過於重要,而忽視了自己內心真正所熱愛的東西。
一位患者總是到世界各地旅遊,而必須頭等艙,高檔酒店,然後喜歡看朋友圈別人對他的點贊。雖然他收入很高,但結果卻沒有存錢及為以後考慮,錢都被用在了這些和別人比較與炫耀的方面,而時間也都用在了融入那些更高級的群體之中。他用這些光鮮的東西來塗滿自己的全身,他還真的以為自己是上等人了。
就好像《非洲紳士》這部紀錄片,剛果有一個奇怪組織“時尚優雅人士協會”,他們這樣的人稱自己為薩普。片中一個穿着優雅裁剪西裝的男人,踩着油光嶄亮的鱷魚皮鞋,走在灰塵飛揚的街道上,每天走在破爛的街道上,形成剛果一道靚麗的的風景線。色彩鮮麗的西服和周圍灰暗簡陋的房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你以為他是一個富豪,其實他的月工資不超過人民幣800元。
剛果石油資源豐富,但水資源匱乏,糧食短缺,有一半以上都屬於貧困地區,人們只能把樹葉當成麵包,這裡常年被疾病戰亂籠罩。但薩普卻是一個例外,他們每個人都擁有時髦而昂貴的衣服,搭配圓頂禮帽,手掌,蝴蝶結,像是來自於西方的紳士。
每當片中的馬克穿着時髦華麗的西服,走到狹窄混亂的街道上時,就像進行一場個人的時裝秀,人們發出興奮的歡呼,簇擁着他和他握手,彷彿他是一個國際巨星。馬克也很享受這種感覺,他熟練且優雅的和每個人握手,猶如出身高貴的紳士。而他回到家,一切光環都不存在了,數十人擠在狹窄混亂的院子里,妻子是賣衣服的小販,收入並不高,他們還有兩個孩子需要照顧。馬克走進房間,牆面斑駁,家徒四壁,他從破爛的床腳,小心翼翼的取出一雙皮鞋,這是法國的奢侈品牌韋斯頓,一雙售價超過萬元,馬克攢了整整兩年的錢才擁有它。在貧困的剛果,這些錢足以買下一塊土地,供他們一家過上小康生活。在馬克眼裡,改變家境遠遠比不上薩普的尊嚴和體面。
試想,維繫虛榮何止是華麗的服飾,當一些人執着於成功和優秀,執着於好工作和掙錢多,執着於成長與進步,難道這不是一種進化版的薩博?

6、 強迫性努力
我們總是說要有平常心,但對神經症患者來說他恰恰缺乏平常心,他的眼中只有執念。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過於用力,但越是如此,他不僅沒有把事情做好,最後反倒把事情搞砸。
他為何會如此用力,過度認真,這裡的原因就在於他做事情根本就不是在做事情,他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維繫自負。當然有人會認為這是一種進步和成長,但這實際上只是被恐懼驅使,他怕這個怕虛假的自我形象被破壞。
但反過來這種人設又強化了他的自我逼迫——因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那麼他必須各方面比別人表現的更優秀;因為他是一個品德端正的人,所以他就不允許自己有任何不良嗜好;因為他是受人歡迎的人,所以他必須和每個人都處好關係。這兩者之間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當應該維繫了人設,那麼人設反過來又強化了應該,與此反覆,彼此加強。但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這不可能無限制擴張下去,遲早有一天會崩潰。
所以,別人可以偷懶,可以放鬆,但他不行。對他來說工作和學習都是消耗的,是恐懼的,在其中他很難找到樂趣。所以,拖延和逃避就成了一種必然的結果。
7.逃避與依賴
因為害怕幻想的破滅,他會不自覺地活在全面防禦之中,他害怕那些可以戳穿他自負的東西,比如,失敗、被否定。所以,他活在了“舒適區”之中——他會逃避未知,在熟悉的環境中才感到安全;他也不敢承擔起生活的責任,因為不努力會不會失去,更不會失敗;他不認真投入生活,那麼就可以給自己的不成功找到理由;不睜開眼睛看自己與這個世界,就可以繼續做夢。
所以,在神經症患者身上經常看到的現象就是休學,轉學,辭職,離婚,絕交,宅在家裡,不去承擔與面對他這個年紀應該去面對的生活。有時,他明明喜歡一個人卻不敢追求;他明明想要考研,卻突然放棄;他明明想要找更好的工作,但卻不敢爭取。
一位患者這樣寫道:任何有可能打破我腦海中的幻想的事情我都會全力去逃避,花費幾個小時完成別人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做好的事情讓我感到沮喪和憤怒,大腦里的我這麼厲害,為什麼現實里又這麼普通呢?需要進行比賽對抗的項目讓我感到恐懼和沒底氣,我不敢參加鋼琴比賽。我總是害怕出錯,出醜,害怕評委對我譏諷。我總是在恐懼,總是感到沒底氣。兒時的我,總是很擰巴,內心渴望和同學做朋友,大腦里又自傲地覺得他們太幼稚,不配和高貴的我相處。我模仿着成熟大人的模樣,像個小大人一般幫老師同學分憂解慮。此時,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我是被接納的。當一段關係破裂,我便會感到受傷恐懼,被拋棄的感覺又讓我去彌補這段關係,周而復始,最後徹底絕交。是我自我成長的方式出了問題,還是壓根我就不想“好”,寧願活在夢裡自欺不願承擔更多現實的痛苦呢?或許活在夢境里本不是錯,錯就錯在本已經意識到這只是泡影卻依舊在維繫?
實際上,只要一個人故意欺騙自己,那麼他可以找到成百上千種騙自己的方法,只要一個人不肯誠實地面對自己,那麼他就會想辦法催眠自己,就算現實擺在眼前,他也可以視而不見,就算這一切漏洞百出,他也可以裝糊塗。例如,一個女孩她不回答老師的問題,因為她怕回答錯誤;她不交朋友,因為她欣賞的人很少;她不接電話,因為她會緊張;她只對物理,客觀,沒有思想的東西感興趣,但對真實存在的人,卻沒有半點興趣。當然,不是沒有興趣,而是人會傷害她的驕傲,打破她的幻想。當她炫耀自己的成績與成功的時候,我提醒她如果有人比你更優秀,更美麗怎麼辦?她談到:不聽,不看,不接受。她始終相信自己就是那最好看的,最優秀的。
隨着治療的逐步深入,一些患者會意識到似乎自己是活在了一個虛假的自我與幻想的生活之中,他開始對之前所認為的自己產生了懷疑,他開始試着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試着重新自我定位。
一位女性患者寫到:有些迷茫,我好像慢慢發現了自己的位置,以前我認為自己和那些優秀的同學是一個階層的,可是現在慢慢發現,自己趕不上了,無論是單位,還是男朋友,人家的都比我高一階級——追她們的男生是7、8分等級,而只有3分的男生才對我感興趣。
我開始懷疑自己的位置,事實多了我不得不懷疑甚至承認自己不是以前的8分,8分的同學依舊是8,而我卻是5。現在我不僅要承認自己的不好,我還要接受以前和我一樣的人要高於我。我開始懷疑迷茫,以前的高人一等呢?就算不高至少也該屬於那個被仰視的階級。難道現在我真的就比他們要低一階級?也許是吧。
我知道5分不足以讓我選擇死亡,因為我知道我只是個普通人,那麼在我身上1-10分都是正常的,我的範圍不是只有8-10分。我該承認我做不到父母眼中的8或9分,我讓他們失望了。他們對我是9分的要求,而事實我只是5、6分,是我不夠好不夠優秀,是我無法匹配他們對我9的希望和要求。最可怕的是我竟然認為父母的高要求客觀上沒有錯,我爸只是希望我優秀,他的要求有什麼錯?我想,是我不夠優秀沒能匹配上他們的9分的期待,因為確實有人就是9分,客觀上,還是我不夠好吧。
寫到這我很難受,雖然我感覺到“我不夠好”有點問題,可是客觀上5大於3,但5也小於9,所以我不夠好客觀上也沒錯。
對自我價值的懷疑雖然是治療中重要的一個環節,但這個環節卻會讓一個人會變得更加自卑與恐懼。此時,他對於治療,對於分析也會產生抗拒的心理,治療也陷入了瓶頸。雖然他知道應該從夢中醒來,但他卻無法面對因此而來的巨大的衝突。
隨着一層一層向下分析,我們最終發現了核心的問題——他不敢成為自己,不敢面對真實的世界。原生家庭的傷痕,負面的能量彙集到一起形成了一個黑色的能量體,讓他無法直視,甚至無法靠近。當他瞥見真實自我的時候,就好像有一列火車開過來,或一個大浪向他打過來,他只能老老實實,只能偽裝討好,只能活在自負幻想之中,不然整個人就會魂飛湮滅。把這個虛假自我打碎之後他沒辦法生存,一種被生吞的感覺撲面而來
一位患者在寫到:往前走,似乎就進入了危險區,進入了戰爭區,我的它,不管你們稱它為心魔,還是人設,還是魔鬼什麼的,它就要面臨隨時可以被犧牲,被一炮打死的可能……我不想讓它死,我喪失了理智,我要拚命救它,因為後退是無盡的深淵。為什麼害怕它死呢,因為它是我的全部,我的價值,我的人生,我的快樂,我的全部,都是它給的。它為啥不能死,如果你現在問我,我會說,它肩負着父母對我的愛和我的價值,是我人生的全部。
也許,越接近真相就越痛苦,但不痛苦怎能看清真相?患者往往希望治療師可以溫柔一些,但這這不切實際,畢竟成長就意味着痛苦,不痛苦也就沒有成長。幻想給了他虛假的安全的同時,實際上也阻礙了他的成長,他依然被卡在了童年,他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成熟,並沒有發現實際上成為你自己才是真正的救贖。
治療進行到這個階段,很容易進入一個無限循環狀態,他會一直繞圈,不敢碰觸核心的問題。他寧願沉浸在對解決癥狀方法的執着當中,也不願意直面他內心深處的恐懼——成為他自己。
有這樣一部叫《永無止境》的美國電影,講的是一個廢材,女友也離他而去,他走在街頭別人都離他遠遠的,他就好像是一個流浪漢。有一天他得到了一種葯,吃了之後大腦開發到百分之百,整個人直接開掛,走上人生巔峰。不過這種藥物只能維持幾天。但一直服用這種藥物卻會對身體與大腦造成嚴重的不可逆的傷害,最終死掉。他明知道是這個結果,但他卻不敢停葯,因為他怕回到之前的廢材,害怕失去當下所擁有的一切。
一面是得救的希望,一面是無盡的深淵,治療進行到這裡就進入到了深水區與危險區,患者一腳在現實,而另一腳在幻想之中,他理智上能認識到這一切,但身體上卻本能地抗拒。所以在這個“我是誰”這個核心問題上,神經症患者總是一會清醒,一會糊塗。雖然理智上他知道我說的是對的,這個方向是對的,但因為真實的自我太弱,並且他也不認為這個自己是可以被社會所接受的,所以他寧願繼續做夢,寧願活在一個虛假的自我裡面,畢竟這樣還可以活下去,雖然他知道這也是慢性自殺,但如果打破虛假的自我的結果對他來說就是宣布死刑,立即執行。
一位患者寫到:
你把我的黑歷史全部都全都挖出來了;
我逃避的是小時候;
虛假的自體遮掩自卑的自己;
你太壞了,把我挖的太深了;
你是壞人,我又喝酒了;
又一次變成餃子餡;
張愛玲說: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卻爬滿了蚤子;
你是第一個看到滿身虱子的我,也許大多人都看到了,卻沒有這樣告訴我
我用曾經虛幻的我遮蓋虱子
可笑又可悲。

《楚門的世界》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幾近和諧與和平世界——桃源,在這個世界裡楚門不會受到不法分子的迫害,不會經歷人生中巨大的挫折,不會因為生活的苦而感到煩惱,於是我們把這個名為The best place的世界譯為桃源。這一切是多麼的完美,或許有很多人會沉醉於其中,盡情的享受的一切。但是楚門卻並不如此,最後他幡然醒悟,毅然放棄這完美的一切,走出那扇門去尋找真正屬於他自己的生活!因為他知道只有在那扇門的外面才是真正屬於他的世界,無論多麼危險,他要回歸現實,去尋找真正的自我。
影片中的製片人克里斯托夫說:“他如果有野心,隨時都能走;他如果決心查出真相,誰也阻止不了他。”當人生成為一場戲,當所有的真實都成為欺騙,當發現自己所有的生活都是表演,那麼,只有義無反顧的追求真正的生活,才是讓所有的謊言有個完美的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