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有些東西“談之色變”是有原因的。對“供銷社”來說,是有深刻的歷史記憶的。且這種記憶並不美好。
“供銷社”在年紀稍長的人的記憶里,就是那個生活局促、物資短缺、人性壓抑的時代的象徵,是計劃經濟背景下的社會經濟供銷體系。其背景是,新中國內外交困現實背景下的社會經濟造就的現實。其本質是,學師西方代替傳統路徑後還未能產生各個層面的協調融合而發生排斥產生的混亂。其現實是,我們自身意識層面沒有思想創新而無法駕馭調和這種新路徑產生的具體問題而出現的經濟、社會秩序混亂,最終成為拿來的意識路徑的附庸而淪為計劃標準的標的而失去人性中的自我意識,所以導致整體社會都不會獨立思考、沒有創新意識,很多層面一直延續到今天。
所以,人們反應有點“不安”,是可以理解的。

而今非昔比。今天極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即以城市文明為標誌的西方商業文明體系形態。雖然說,供銷體系伴隨着國人並不美好的一段回憶,但任何存在都有其必然,問題只是出現在,這些形式方式用到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怎麼用的問題上。那個時代秩序性的混亂致使要素混亂,並不代表今天秩序相對穩定的狀態下也不能用。
顧名思義,供銷體系本身就具有公共屬性,在過去是因為物資匱乏的統銷統購。而今天物質文明大發展,市場經濟配置功能強大,可為什麼還要恢復供銷體系呢?
其實,我們恢復的不過是個名稱而已,並非要恢復過去的計劃經濟體系。
因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是資本,資本逐利的本性只會嚮往資源、人力密集和生產效率高效的工商業集中的城市領域。所以導致諸如中國三農領域無資問津,而淪為經濟價值、社會治理、生態平衡的窪地。
而現實中國需要振興“三農”來平衡以城市文明為載體的商業文明。所以,祭出“供銷社”這種具有公共屬性的社會、經濟於一體的服務組織來幫助“三農要素”形態穩態,來和城市文明形成互動以平衡中國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問題甚或是危機。

具體什麼情況?
從“三農”的角度來講,農村治理主要體現在黨建層面的組織關係,而在事物層面是分散的。可現實經濟體系中,三農要素在權責價值等層面上界定並不清晰徹底,且過於分散,加之農民對接市場能力及認知差異的現實,導致要素流通受阻,使農民資產無法通過自身能力整合而阻礙價值變現。
所以,設立專門為三農與基層服務的供銷社,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信息平台、協調平台、資源平台來實現資源整合,促進要素流通來幫助資本不願涉及的領域的價值變現及公共治理與服務保障。
從“應對可能到來的危機的社會保障”的角度來講。
首先,中國漸入老齡化的現實。中國人口結構相對畸形,青壯年普遍無或少兄弟姐妹,但上有老下有小,還要工作養家,所以普遍風險承擔能力不足。若遇危機,極易造成社會問題。新型的供銷體系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類似於社會保險似的“公共養老”。
其次,現實中國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國際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變化。而我們自身的經濟結構是深度參與全球化造就的,所以勢必會受到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由於我們身處西方創造的產業經濟的中低端而必定會承受高端玩家的成本轉嫁,且高玩貪婪導致的自身危機漸自反噬,遂有圖窮匕見之勢。

這種外部的覬覦極有可能在接下通過製造我們的地緣危機來誘發我們自身體系的危機。所以,此時恢復具有公共保障性質的“供銷社”,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預而備之。
所以,不必過度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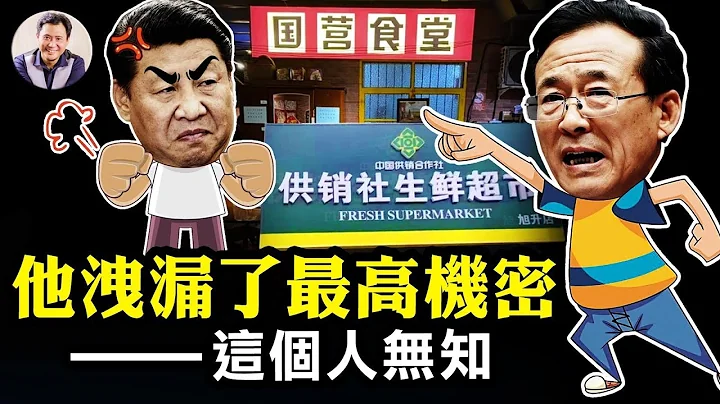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