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平安是福
1969年8月中旬,15岁的我与军科几乎连锅端的69届初中毕业的大院孩子们一起,坐着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来到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8团七连,在包头市的东南方向约20里处的位置。

我被分配到了第九班。从此,开启了我初次踏入社会为期八个月的农垦生活。这段日子,在我的工作经历中虽然很短暂,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01
九班副树立起威信的艰苦历程

在学校和在军科大院孩子中从不显山露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到兵团领导就指定我为九班的副班长。至今都50年了我也没弄明白原由,反正也没地方问去,都不知道连长和指导员在哪里,姓甚名谁。(噢,想起来了,我在文革复课时,当过短暂的初中某班班长。)
哎呀,这个小小的副班长头衔可把我害苦了!全班除了胡陵秋外,我是第二个年龄小的,上面还有好几个67届68届的大姐姐们,谁听我的呀?
班长是个67届的叫什么凤的人特别精明,凡是她不喜欢做的能推脱的事情都指派我去办。像什么开班会学习讨论念报纸,打扫厕所卫生,代表班里出节目等等。
到时候开会了,该肃静了,可是我喊了半天都没人听,还是各说各的叽叽喳喳。我的小脸憋得通红,干着急不管用,直到班长发话才安静下来。这种局面直到发生了几件事情后才扭转了,现在我只记住两件事。
一次是冬天连里给我们班分配打扫厕所的任务。
班长安排我带领几个班里比较闹腾不服管的去。我们领了铁镐、铁锹、竹筐,到了厕所(那个时候都是露天的)门口,她们都站着不动,有人提议让副班长先干。
呵,干就干,到了兵团谁还怕干活呀!我拿着铁镐就去,那可是冬天,粪坑里的屎和尿都结成了厚厚的冰。每刨一镐头,臭冰碴子就会溅到脸上和身上。
我不在乎,挥起铁镐一镐一镐卖力气地刨。其他战友们看到我一点也不嫌弃,都不好意思的陆陆续续加入进来。她们可都是自觉地加入劳动中的,我没有招呼她们一句类似“别都站着,来干活呀……”之类的话。因为我知道,越是叫她们干活,就越是没有人参与。这样,我们终于一起把厕所打扫干净收工啦。
又一次是平整土地挑土。
我们班有一个从海淀区黑山扈生产队来的农村女孩,从小就会干农活,身子骨长得黑壮黑壮的,像个假小子。我们有拿铁锹的有挑竹筐的,三人一组分工合作。
给我分配的是挑竹筐,两个战友用铁锹把土装满两个竹筐后,我负责把土从田地的东头运送到西头,有多远我也说不清。
干了一阵子,那个假小子就向我发起挑战,要和我比试一下谁挑得担数多。她嘴里还一口一个副班长叫着,不应战就是怂包。
尽管我从小没干过这些,连在家里擦桌子扫地都逃避的娇娇女,如今要和比自己大两岁的农村妞比体力,比干农活,那不是自找苦吃嘛!可我是军人的孩子,能认怂吗?绝对不能!
好,比就比,怕你不成,我也不是吃素的!结果,那天下午比到收工时,她挑了八担土,我也挑了八担土,打了个平手。最后,她把扁担一扔,一屁股坐在地头上边喘气边说:副班长,我算服了你了。
我才不坐下歇着呢,挺直了腰杆,昂起头摆出胜利的小样,牛哇!她哪里知道,我的右肩膀都磨出了血泡,又红又肿。
晚上我钻到李清菊的被窝里痛哭了一场。清菊比我大一岁分配在十班,却看见了我与假小子比赛的全过程。看着我肩膀伤的那模样直心疼,不停地唠叨我:你是什么身子骨,能和她比吗?以后别再干这样的傻事儿啦!我咬着牙说:她们不服气我还得这样拼命,直到她们服了为止!
自此以后,她们都佩服得不行,从而,奠定了我这个九班副的领导地位。开会时,只要有人乱说话不安静,不用我吭声就有战友大声吆喝:静一静,别说话了,听副班长的。
耶,小小的我好开心呐!
02
对人情世故,世态炎凉的初体验
在接近1969年底的一天,阳光明媚,我和一个闺蜜行走在荒漠的羊肠小道上,一路聊得挺开心,我把她送出连队已经很远了才依依不舍地分手返回连队。哪知道这次分别对我的打击力度相当之大,以至于使我决心和她断绝来往,不再做朋友,做闺蜜就更不可能啦!
她这次一走是彻底地离开兵团穿上军装当兵了。消息还是通过别人告诉我的,而不是她本人。当时我的心被狠狠地撕裂,脸上流着泪,心中流着血,有一种不被信任的羞辱感。那么好的闺蜜,不说在儿时的玩耍,只说在兵团艰苦的生活中曾经同甘共苦,互相慰藉。可她在离开的时候连一个字都不跟我说,这还是闺蜜吗?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今后我还能相信谁?我那15岁青春期的小心脏要崩溃了!
当我陆续收到她从部队寄来的信件和军装照后,慢慢的心情平静下来,理解了,释怀了。我想,要是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当兵,当然也是选择离开了。不过我不会和闺蜜们不辞而别的,因为我不想让幼小的她们和我一样受到刺激和伤害。
这事儿都过去50年了,早已经翻篇了,我们现在仍然是要好的闺蜜。
虽然我在花朵的年纪遭遇过信任危机,但在今后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都不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也不会听别人说他好我就去喜欢,更不会听别人说他坏就一定会疏远。而是要自己接触,自己了解,然后再做判断。
至今我依然是以真诚待人,热情助人。我觉得无论别人怎样,我的那颗善良的心不能变。要学会原谅,而且还要感谢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是他们激励我奋进,使我变得成熟,使我更加坚强,使我能够面对任何困难而永不退缩!
同样是在1969年年底,在兵团里还有一件事情让15岁的我深深的明白了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父母可能再也呵护不了我了。
那就是北京备战备荒的大疏散。我们部队大院的很多家庭,都随着父辈们的工作变动而牵出了首都北京。为了安抚我们在内蒙兵团屯垦戍边的七八十个孩子们,大院委派了三个军队干部两男一女来看望我们。那两个叔叔是谁我记不得了,阿姨是专门来看女孩子的,叫什么我也记不住,只知道是院里门诊部的。
我们七连一帮女孩围坐在炕上,阿姨在中间笑眯眯地跟这个女孩讲:你爸爸到哪个军区任职,她爸爸到哪个军分区当什么什么官了。女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阿姨自己家里的变化,爸爸妈妈都去哪个省份哪个城市了?我也找空隙不停地问阿姨我爸爸去哪儿啦,心里很着急,我间断性地问了好几次,阿姨只是看了看我不回答。
记得这个阿姨曾经来过我家几次找我爸爸,在大院里碰到我时总是很和蔼地和我说话,问长问短,所以我对阿姨很有好感。我想,阿姨被大家问得顾不上我吧,就等到她回答完所有同学的话再次问及我的爸爸。阿姨扭头看着我,那张与别的女孩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脸迅速耷拉下来,一脸阴霾并以温怒的低沉的近乎于低吼的声音说:你爸爸啥也不是了,退啦!
我去,这脸变得也太快了吧?!听到我爸爸不再担任职务的消息并没有让我惊讶,反倒是阿姨这张变幻多端的脸着实是吓着我了。这个大白眼,使我立刻联想到那些父母遭受迫害、挨整的孩子们、同学们,她们比我更惨,在比我的年龄更小的时候就遭受到比这更多更狠的白眼和辱骂。想想他们这个时候父母还在接受审查,我的爸爸不过是不再工作罢了,又没有被圈起来进行劳动改造,已经是不错啦。他们都挺过来了,我怕什么?我有两只手,能够生存,能够养活自己,不求多富贵,能填饱肚子就行。想到这里,调整好心情,第二天醒来,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和往常一样开工去了……

我时常在想,自己遭遇过的挫折和受到过的负面冲击,是人生中任何人都不可回避的事情,这些经历实际上是自己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日后除了当兵是托父亲的关系走后门入伍外,什么入党、提干、上大学,晋升职务,在朝为官也好,下海经商也好,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所以我时不时的感到自己很骄傲很自豪!
在政府部门工作时遇到的热情接待,我明白是因为自己的工作身份所致,万不可张扬跋扈,目中无人。在公司工作时遇到客户的挑剔和刁难,也会尽自己所能去沟通去协调,直到实现既定目标为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只是渺小的一粒沙子,早已融入到沙漠或者大海中了。
03
酝酿逃跑
在军科子女来兵团插队的同学们,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成功逃跑回家的实例刺激下,我也蠢蠢欲动,开始策划逃跑行动。
那时,爸爸妈妈带着弟弟已经离京去了北京军区驻临汾的休养所。听妈妈说这个地方还是受政治迫害仍然靠边站的叶帅给爸爸找的落脚点,叶帅还悄悄跟爸爸说如果不喜欢再给他另外找地方。为此,妈妈专门去临汾休养所看了一下,回来向老爸汇报觉得还不错,就把家搬去了。自然是爸妈到了哪里,孩子们就要投靠到哪里。
北京没有家了,去临汾,就这么决定了。
去临汾的路线怎么走呢?在一个休息日,我和同班的胡陵秋向连里请假外出被批准了。我们徒步走了15里地来到万水泉火车站,向一个值班的大叔咨询有没有去临汾的火车?大叔很耐心的告诉我们没有直达的,只有到太原再换车去,并且告诉我们发车时间和全程的票价,两段车程加起来要将近15元钱,而且去太原的车不是每天都有,好像是一周才一趟。

万水泉车站
这个信息太重要太及时啦。可是摸摸自己的口袋,积蓄还不足两元钱。没关系,我努力积攒。当时,我们兵团战士包吃包住,每个月有5元钱津贴(供我们购买牙膏、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和解馋的糖果)。我严格控制自己的支出,省吃俭用,溜溜的攒了三个月,终于把火车票钱凑足了。
我逃跑之前告诉了好几个闺蜜,印象最深的是李小俐那副走不了很无奈的模样。是一个午后,小俐坐在她们班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我走过去俯下身子悄悄地告诉她,明天天不亮我就逃跑了,特来道个别。小俐一听都快哭了,仰头看着我颤抖着声音说: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呀?入团了哪也不敢去,早知道就不入了。
可喜的是我这些闺蜜们一个也没有出卖我,都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算计好开往太原的火车日期,大概是1970年的4月4号凌晨,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极度紧张的大脑中枢神经唤醒了我,摸着黑从地铺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初春的季节怕春寒,把兵团发的棉大衣、棉帽带上,提着自己认为存放贵重东西的旅行袋,朝着万水泉火车站进发。
从连队到火车站有15里地,天还黑漆漆的,我头不回腿不停地一路向前。路过团部附近的一个村庄时,天空出现了一点点鱼肚白,直视远处堤坝上有个早起的老乡,我没有停下来,和他对视了一阵,谁也没有说话,直到他的身影落在我的背后也没有听见任何响动。
天渐渐泛起早霞的红光,火车站也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到了车站,售票窗口只有我一个人,问好值班员现在几点?去太原的火车过去没有?值班员的回答让我兴奋不已,时间赶上了。
当七点的火车进站时,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乘客。登上列车找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后,内心不能平静,眼睛不停的看着车厢门口,深怕连队派人来追我。要知道,我们一起来兵团的同学有好几个逃跑的都被抓回去了,有的不止抓回过一次。我那颗悬着的心随着一声汽笛和火车轮子的慢慢启动放下了。车厢里的喇叭开始播放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都是我会唱的。伴随着歌声和车轮的提速,我的心中狂喜,哈哈,逃跑成功啦!真想放开歌喉与喇叭里的声音一起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当火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有列车员和车长走过来问我会不会唱歌跳舞?那还用问,当然是小菜一碟了,我是兵团七连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呀!唱歌跳舞、独幕话剧都演过。
可是,我断然拒绝了,说我这些都不会。他们不相信,说一看我就会,别不好意思,为乘客们唱歌跳舞也是为人民服务。我坚持说不会,他们失望地走了。这个时候我是“逃兵”,哪能大张旗鼓地表现自己呢,招来横祸怎么办?我可不想被抓回去。眼瞅着他们组建的临时宣传队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表演节目,我为他们的付出和敬业鼓起了掌。
从内蒙万水泉-太原-临汾的两段火车,我坐了一天半多,除了喝点热水外,几乎没有吃饭。坐在对面的一个叔叔级的人看到我中饭和晚饭都不吃,直劝我吃点东西别饿着肚子。他哪里知道,我买完火车票后没有剩下多少钱,到爸爸妈妈家之前不知道还需要多少费用,我得节省着花呀!
我的逃跑决定完全是自作主张,从来没有和家里说过,给爸爸妈妈来了个措手不及。当我逃跑回到山西临汾后,爸爸怕组织上说他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就给连队写了一封信说要把我送回去,不过信中说我刚回家,让我在家住几天再回连队。连长在晚点名时,给全连读了我爸爸的信。连长以此为鉴奉劝大家不要逃跑了,跑回去也会被革命的英雄的父母们送回来。
要不是同班的胡陵秋写信告诉我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爸要送我回去。陵秋嘱咐我千万别回去,如果回去就白跑了,以后就更不好回家了,还用了好几个惊叹号??为此,我一直很感激陵秋给我通风报信。我看了陵秋的信就去问我妈妈,是不是爸爸要把我送回内蒙?得到妈妈的确认后,我傻眼了。我不敢找爸爸说,就趴在妈妈后背上一边摇她一边求着:妈妈呀,别把我送回去啦……我妈当时坐在小板凳上摘菜,她那小个子哪里经得住我的体重。妈妈快透不过气来,让我赶紧起来,并答应我去做爸爸的工作。后来妈妈告诉我说爸爸同意啦!欧耶?我又打了一个漂亮仗!
以后,爸爸没有再提送我回兵团的事情,而且在生活上还特别关照我。由于妈妈回北京照顾我大姐和外孙,捎带着找军科院领导安排我当兵的事。家里剩下我和爸爸、弟弟一起生活,弟弟上中学,家务活我全包了,爸爸也感到我在身边的重要。记得当我生病时,爸爸会把一天三顿吃的药一粒一粒给我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倒好一杯水催促我该吃药啦,直到我病好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爸爸如此对待哥哥姐姐和弟弟们,让我感受到了爸爸的慈爱和亲人相依为命的滋味。

我又要离开家当兵去了。上面的哥哥姐姐当兵时,爸爸都没有把他们送出过家门口,唯独我当兵时,爸爸拖着那条负过伤的腿,和弟弟一起从临汾休养所走到火车站。因为是偷偷送我去当兵,爸爸不敢张扬,更不敢找休养所要车。而且,我们选择晚上的火车,趁着天黑悄悄地走了。
自此,16岁的我又踏上了一个人的旅程,从临汾到西安再转车去往兰州参军。结束了我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身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从而实现了我 的人生转折,实现了我小学时就立下的志向和梦想。

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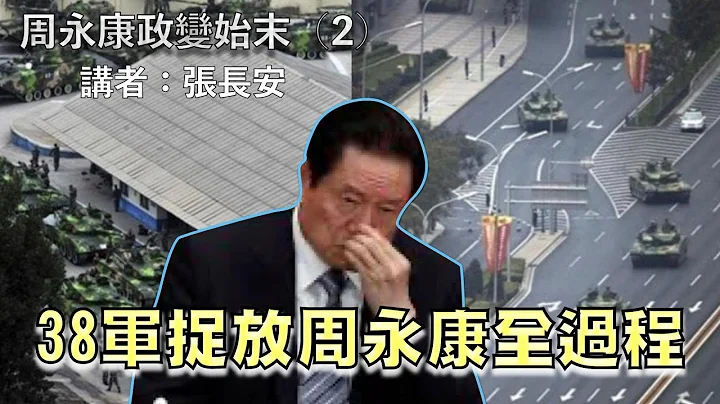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结】《我的女将军大人》女将军穿越意外嫁总裁,被心机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来了?总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宠#霸道总裁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