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接上篇(點我頭像進入主頁搜索標題關鍵詞查看)

13
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扶稷與我的關係達到了一種巧妙的平衡。
他不忙的時候,會來看看我,我不再有越界的舉動,他也從不在我這兒留宿。
經過上次,嬤嬤如今幾乎日日都來未央宮陪我。
除了蓮長使還是有意無意地想給我使絆子,宮裡的日子過得還算清閑。
扶稷一般酉時來未央宮,坐半個時辰便走。
我的心從酉時前一個時辰便開始期待,我叫鈴兒替我掌上燈,我泡上上好的毛尖茶,在小爐上溫著,靜坐著等待酉時的到來。
腦中卻因為心裡按捺不住的期待而思緒紛飛。
他怎麼還沒來?他何時來?他今日還會來嗎?
恍惚中我曾想過,如果寧寧沒死,我是不是現在該坐在長樂宮。
同樣地給扶稷留燈溫茶,扶稷下朝回來,抖落滿身的霜雪,我鑽在他的懷裡,聽他同我講哪個老學究又被氣得吹鬍子瞪眼了,而我聽得咯咯笑,還要埋怨他故意拿手掌冰我的臉。
這樣平靜的日子如果能日日過下去,也不錯。
可扶稷又開始玩失蹤,連著半個月沒再來看過我。
這一日,安嬤嬤憂心忡忡地來找我。
「凝長使,去勸勸陛下吧。」
我拉著嬤嬤的手,用哀婉的眼神看著她,我想求她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
嬤嬤嘆了口氣,告訴了我。
扶稷求了一盞往生燈,放在長樂宮日日燒著,往生燈五年來,從未有過異樣,但半個月前,往生燈突然無緣無故滅了。
扶稷殺了長樂宮那日當值的所有宮人,把自己關在了咸陽宮,日日酗酒。
往生燈?
從前我也曾疑惑過,自己是如何還魂的,如今看來,一切都是因為扶稷啊。
我的心一抽一抽地疼。
14
我在咸陽宮找到了扶稷,他爛醉如泥。
我從未見扶稷醉成這樣,好似下一刻便要同酒水化為一堆,日光一照,便隨風散去,了無牽掛。
我蹲在蜷縮在地板上的扶稷面前。
扶稷見我來了,黯淡的眼中一瞬間有了簇簇光彩。
「寧寧!」
待他仔細看清我的臉後,光彩又一寸寸被黑夜吞噬。
「不,你不是寧寧,你是小啞巴。」
扶稷彷彿下一刻就要碎了,我很心疼,我義無反顧抱住了他。
扶稷的身子冰涼,他可能也在期冀一抹溫暖吧,他罕見地沒有反抗。
扶稷靠在我的懷中,絮絮叨叨說著,濃得化不開的酒氣噴在我耳邊。
「小啞巴,你知道嗎?朕本來是要娶寧寧做皇后的。」
「她那日鳳冠霞帔,美得不可方物。」
「九皇子的暗衛藏在咸陽宮對面的城塔上,他拈弓搭箭,想要射死的是我。」
「是寧寧替我擋了那穿心的箭。」
「寧寧從小就怕疼,她那時該有多疼啊。」
「死的應該是我,寧寧本該安然無恙地待在長樂宮,她是來給我送海棠糕的。」
「是我的一句話害死了她。」
「她倒在我的懷裡,傷口不斷地往外冒血,我怎麼按都止不住,我真的好害怕。」
「血不停地流啊,流在她的紅嫁衣上,她變得越來越輕了。」
「她說扶稷啊,慢一點忘了我。我怎麼能忘呢,那是我的妻啊,我十幾年前就在佛前立誓要娶的人。」
扶稷哭得泣不成聲。
我輕輕地拍著他的背,我只道自己有夢魘,卻不知我也是扶稷的夢魘。
「她本該在六月初五就如願嫁給我的,是我執意要將婚期改到六月初七。」
「是我害死了她,她甚至連我一日明媒正娶的妻子都沒做成。」
扶稷的頭埋在我的肩上,淚蓄滿了我的鎖骨。
我又好到哪裡去呢,霧迷得眼都花了,大滴的淚珠卻還在止不住往外涌。
對不起,扶稷,是我害你獨自一人在痛苦中徘徊了五年。
我不知扶稷將這些話藏在了心裡多久,我在黑暗裡同他相擁,聽著他的宣洩,我想安慰他:
【不怪你,我從未怪過你。】,卻是徒勞。
我只能更用力地抱緊他,企圖用我的體溫去焐熱他寒冰似的身軀。
過了良久,扶稷哭累了,才抬起頭來。
他的眼中全是迷濛的霧氣。
「寧寧,是你嗎?你終於回到我身邊了?」
我未言答,他失而復得般攀上了我的唇瓣。
這是我們第二次同床共枕。
瘋狂的,甘之如飴的。
彷彿下一刻世界就要崩塌,我們在海中沉浮,只能更用力地靠近彼此才能免於溺亡。
夜半三更,這一次逃的不是扶稷,而是我。
15
我拖著酸軟的身軀起身,看著沉沉睡去的扶稷。
我想,還是不要讓他醒來看見「我」比較好。今夜,就留他夢中的寧寧陪他吧。
我不能再逼扶稷了。
我回了未央宮,鈴兒一見我,便心中瞭然,打來水給我沐浴。
以往,我總是為扶稷認不出我而懊惱痛苦,今日才發現我太自私了,從未去注意扶稷因為寧寧而忍受的千瘡百孔。
我不再糾結扶稷能不能認出我了。
若他一輩子都把我當成小啞巴凝凝,那便如此吧。
扶稷已經孤獨了太久,如今我只想默默陪著他,替他掌燈溫茶,無論以什麼身份。
第二日,嬤嬤告訴我,陛下終於走出了咸陽宮門。
我擔憂的心也隨之放下了,那就好,那就好啊,希望寧寧能讓他振作起來吧。
扶稷照例醉心於朝政,也沒再踏足過未央宮。
過了月余,我總是乾嘔噁心,嬤嬤看著我的樣子,眸光閃爍。
她出門去請太醫,而隨太醫一道來的,還有扶稷。
太醫把完脈象,樂顛顛地給扶稷行大禮。
「恭喜陛下,賀喜陛下,凝長使有喜啦。」
我的心一窒,那一夜之後,我憂思鬱結,並未想起喝避子湯。
扶稷斂退了眾人,他沉吟問我:「那一晚在咸陽宮的,是你?」
我點了點頭。
扶稷閉上了眼睛,他長長的睫毛輕顫,連帶著我的心也不安地顫動。
他終於睜開了眼睛。
「正如太醫說的,有喜了,是好事啊。」
扶稷沖我淡淡笑了。
可當真是好事嗎?扶稷雖在笑,為何我又在他的眼底看到了悔恨與哀傷。
打這日後,宮中的補品與珍玩絡繹不絕地往未央宮中送。
但真正令我開心的是,扶稷每一日都會來看我。
他似乎換了一種熏香,不是松柏香了,但依舊很好聞。
我也欣然地接受了肚子里有了一個小傢伙的事實,那是我同扶稷的結晶。
每晚躺在床上時,我都會輕撫上小腹,感受著這個小生命的醞釀。
他是男孩還是女孩呢?
男孩女孩都好,我阿娘去得早,自小我便沒有娘親的陪伴,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我都會把他寵成皇城裡最幸福的小娃娃。
白天的時候,我就讓嬤嬤教我綉小娃娃的衣裳。
雖然我繡得還是很醜,但這是我親手給肚子里的小娃娃做的,意義不同的。
鈴兒、嬤嬤和太醫們將我照顧得很好,我身子愈發圓潤了起來,肚子里的小傢伙也一天天地長大。
快快長大,來到阿娘身邊吧。
有了你,阿娘就不再是一個人啦。
懷胎兩個月的時候,我突然大出血,太醫院守了未央宮一宿,也沒能保住我腹中的孩子。
16
我躺在冷冰冰的床上,望著黑洞般的屋頂。
怎麼會呢?阿娘分明將你養得很健康。
我摸了摸小腹,那裡平平的,已然沒有了生命的跡象。
我好像又重新死了一次。
扶稷今日照例來看我了,不同的是,他又換回了從前的松柏香。
我大夢初醒,我盯著他的眼睛,想要一個答案。
扶稷揉了揉鼻子,低下了頭,默不作聲。
這個神情,是他說謊愧疚時才會有的。
我背過了身,臉朝向床內側。
原來這一個月的朝夕相伴都是假的啊。
我兩世第一次徒生一個念頭:我再也不想看到扶稷。
扶稷在未央宮裡站了很久。
末了,他聲音喑啞開口:
「小啞巴,是朕對不起你。但朕更不能對不起寧寧。」
我淚打濕了枕巾,我該怎麼釋懷呢?扶稷,你可知,你親手殺死的,也是同寧寧的孩子啊。
第二日,扶稷給我升了位分,我成了凝美人,一下越了四個品級,這是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的。
我知道,這是扶稷補償的方式,而我卻沒有一丁點兒的喜悅。
扶稷此後也來過未央宮很多次,我每次都讓鈴兒把門緊閉。
我還沒有辦法裝作若無其事地面對扶稷。
鈴兒說,長樂宮的宮燈又開始從天暗亮到天明。
這一日,蓮長使下了帖子邀我去南薰殿,她在信中說得了祈福的秘方,可以替早夭的孩童求個美滿的轉世。
我不喜歡蓮長使,但她信中的後半段我卻怎麼都拒絕不了。
哪怕她不懷好意,只要有一絲可能,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來世可以擁有平平安安的一生。
我帶著嬤嬤和鈴兒去了南薰殿。
蓮長使說事關天機,此事只能讓我一人知曉,她讓我隨她去屏風後再講給我聽。
我想,嬤嬤和鈴兒就在屏風外面,她也不至於做什麼吧,便隨她進了屏風後。
下一刻,她就從袖中掏出迷藥捂住了我的口鼻,我頓時沒了力氣。
嬤嬤和鈴兒聽到了動靜,就要拐進來,候在屏風外的侍衛立刻擒住了她們。
蓮長使近乎癲狂地看著我:「賤 人,你去死吧。」
她大抵是瘋了,在宮中明目張胆地劫持,應該也是沒想著活的。
她似乎讀懂了我的意思,陰惻惻地笑了:
「哈哈哈哈,反正我此生對皇上唯一有意義的,也就這張臉了。可自從你進了宮,我連這一丁點的價值都沒有了。」
「我早晚是要死的,黃泉路上,我得拉著你墊背,我要讓你看著你心愛的皇上親手殺了你!你和我本質上,又有什麼不同呢?!」
我沒聽懂她後半段話的意思,藥性上來了,我徹底昏了過去。
17
我醒來後,發現自己身處長樂宮。
我雙手被綁住,由一根粗麻繩系著,懸於房梁之上。
麻繩結節處被割了一寸深的口子,由於我的重量墜著麻繩,那口子似乎在一點點裂開。
我不知蓮長使為何要大費周章做此布置。
我低頭想看看離地面的距離有多遠,掂量一下我如果摔下的話是否致死。
低頭的那一瞬間,我的汗毛倒豎,周身凝結至冰點。
我看到了自己一身紅嫁衣躺在木棺之中,準確地說,是寧寧。
木棺前燃著一盞形態怪異的燈,那應該就是嬤嬤所說的往生燈吧。
但往生燈不是滅了,如今不是分明燃得好好的?
還有我,我死了有五年之久,為何屍身擺在長樂宮?為何屍身還未腐朽?甚至於,棺中的寧寧烏髮紅唇,看起來只是睡著了。
我有太多太多的疑惑,還不等我緩過神來,門「吱呀」一聲開了。
是扶稷走了進來。
他神態自若地走到木棺旁坐下,解開了衣服前襟。
他的左胸口處是一道道猙獰的傷疤。
我腦中飛速思考,我是與扶稷坦誠相待過的,以前他身上明明沒有這些可怖的傷口。
我思及最後一次與扶稷同床共枕,就是咸陽宮他爛醉如泥的一夜。
扶稷從袖中掏出一把匕首,毫不猶豫地刺向了左胸口。
我想,如果我不是個啞巴,此刻已經失聲尖叫了出來。
扶稷的左胸口湧出了鮮血,他端起往生燈,讓鮮血一滴滴流進了燈芯。
燈火未滅,反而燒得更旺。
我親眼目睹扶稷近乎虔誠地完成了整個過程。
他在新傷口處撒了些金瘡葯,簡單處理了一下,穿好了衣裳,又將往生燈複位。
嫻熟得好似已經歷了千百遍。
饒是我如今心中尚對扶稷有所埋怨,也止不住想罵他。
瘋子,你不疼嗎?
全程扶稷沒有皺過一下眉,但他的唇色已經蒼白。
他靜坐在木棺前,端詳著寧寧的臉。
他開始同棺木中的「我」說著些漫無邊際的話。
18
「寧寧,你不要擔心,往生燈再也不會好端端就滅了,你的樣子也永遠不會變的。」
「我求清微道長告訴我往生燈復燃的辦法,清微道長說雖然難,但尚有一計可施。只要每七日用與你血脈相連的新鮮血液滋養在往生燈中,往生燈就可以復燃。」
「可世間與你有親緣的只有寧丞相,朕不願傷害你的爹爹。」
「還好啊,天無絕人之路,老天爺是眷顧我的。你還記不記得,成親那日,我吃了你送給我的海棠糕,那海棠糕上沾了你的血。我們也是血脈相牽的夫妻了。」
原來,他自打走出咸陽宮的那一日起,就在割自己的血續「我」的屍身嗎?
扶稷笑了,像是沉浸在幸福之中。突然,他又緊皺了眉頭,聲調似在乞求。
「可是寧寧,我已經用心頭血養了你三個月,你為何還是不願意回來看看我呢?」
「你是不是怪我這兩個月很少來陪你,寧寧可不可以不要怪我。」
扶稷躊躇著,猶猶豫豫開口:
「寧寧,我犯大錯了。三個月前,我喝多了酒,把凝長使當成了你……」
「凝長使她懷孕了,可你還在孤零零地等我,我沒辦法接受和別的女人生子。所以我又幹了壞事,我害死了凝長使的孩子。」
「寧寧,我是個混蛋。看著凝長使魂不守舍的樣子,我的心竟也隱隱發痛,她脆弱的樣子讓我想到了那一日倒在我懷中的你。所以這兩個月來,我忍不住想去未央宮看看她。」
「寧寧,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唐,可我真的沒有為自己找借口。凝長使明明長得和你一點都不像的,但我時常在她身上看到你的影子。所以有時候面對她時,我根本無法做到全然地無動於衷。」
扶稷說著說著淚就滾落了下來,聲音也變得嘶啞。
「可我知道,你們終究是不同的兩個人。你看向我的眸子永遠是亮晶晶盛滿了歡喜的。而凝長使看向我時,眼中永遠寫著悲傷。」
「我好害怕,我怕我不受控制地喜歡上凝長使。寧寧,我是個混蛋,我是個 畜 生!我對不起凝長使,但我更對不起的,是你。」
「寧寧,你回來吧!你罵我,打我,你拿刀刺我的心口。我只要你回來,好不好?」
扶稷哭得泣不成聲。
這是我第一次聽扶稷的心聲。
扶稷可以肆意地說出「對不起」,可我又該站在何種角度談原諒呢?
我的死也帶走了扶稷的一部分,寧寧成了執念,留給了他痛苦的深淵。
還魂後,我只道自己是寧寧,所以奮不顧身要陪在扶稷身邊。
但我不知道在扶稷眼裡,作為凝凝的我帶給了他無盡的掙扎。
老天啊,你多麼狠心,給了我希望,又叫我失望。哪怕我能說出隻言片語,都不會落得如今靠近是錯,遠離是錯的地步。
如今我和扶稷的距離,是真正天涯海角的近,又近在咫尺的遠。
我閉上了眼,任由眼淚縱橫,心口疼得發悶。
扶稷在無數個日夜,活在期冀中,一刀刀割向自己心口時,又該有多疼呢?
在這一瞬間,我突然想和扶稷一起共赴黃泉作罷,是不是死了,就不用再痛苦掙扎了?
我手腕上的麻繩此刻完全裂開了,我摔了下來,直直砸在往生燈上,燈碎了一地。
19
扶稷不可置信地看著從天而降的我。
他聞聲又望向地上的碎片,發出了震天的哀嚎。
我的身子僵住了,我突然在這一刻懂得了蓮長使後半段話的陰狠意義。
她想讓我殺了扶稷的希望,再讓扶稷親手殺了我。
扶稷撲向棺木,我也看向棺中的自己。
寧寧臉上的血色以飛快的速度流逝,變成了慘白色。
「啊!!!!」
扶稷的臉漲得猩紅,目眥欲裂,他舉起了匕首,一步步走向跌坐在地上的我。
我第一次在扶稷的眼中看到了滔天的恨。
雖然害怕這樣的扶稷,但我的心太累了,我閉上了眼睛,讓這些都結束吧。
預料中的匕首卻沒有落在我身上。
我睜開了眼睛,嬤嬤衝進了長樂宮,擋在我身前,雙手接下了刀刃。
「陛下,請您清醒些吧!小姐看到你這個樣子,不會開心的!」
提到小姐,扶稷稍微恢復了神志。
我抱住了嬤嬤,我想讓嬤嬤鬆手,嬤嬤的手掌止不住地在流血啊。
「安嬤嬤,是她砸壞了寧寧的往生燈,世間再無第二盞往生燈了!」
嬤嬤牢牢將我護在身後,「陛下,這都是蓮長使的奸計,凝美人手無縛雞之力,她如何能出現在這長樂宮啊!」
扶稷這才鬆了手,他深深望了我一眼,我看不懂眸中的情緒。
「蓮長使?哈!哈哈哈哈!好哇!」
扶稷疾步出了長樂宮,我油然而生一股不好的預感,如今的扶稷不知會做出什麼。
我扶嬤嬤回未央宮,讓鈴兒去請太醫來給嬤嬤包紮,所幸傷口未及筋脈。
鈴兒回宮時還帶回了扶稷的消息,她告訴我,扶稷去了南薰殿,令人活剝了蓮長使的皮,扔到了油鍋上。
「陛下說,蓮長使不配帶著那樣的一張臉死去。」
我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扶稷,是我害了你。
宮中亂做了一團,因為扶稷又提劍去了地牢,一身戾氣,無人敢攔。
我用眼神央求嬤嬤,求她告訴我地牢里有什麼。
我很擔心如今陌生的扶稷,他已經被刺激得瘋魔了。
嬤嬤嘆了口氣,告訴了我全部。
地牢里關著策反的九皇子。
五年前扶稷就沒有殺死他,而是挑了他的手筋腳筋關在了地牢中。
每日扶稷都令人用箭刺穿他的周身又避開要害,再讓太醫為其醫治,再刺,再治,周而復始。
扶稷又在九皇子額頂上方的牆壁上鑿了一孔泉眼,水每日都「噠」「噠」滴在九皇子額上。
嬤嬤說,九皇子在第二年就瘋了,但扶稷始終吊著他一口氣。
「陛下說,小姐什麼時候回來,他什麼時候才有資格死。」
我的心彷彿被一隻手攥得生疼,我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卻還是感覺要窒息了。
我衝出了未央宮,我要去找扶稷。
扶稷,收手吧!是我害了你。
我終是沒能衝進地牢,嬤嬤死死地拖住我。
「凝美人,老奴不能讓您去送死啊!陛下如今已經神志不清了!」
我蹲在地牢門口哭,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好怕扶稷也在地牢里自戕,扶稷,我什麼都不求了,我只求你活著走出來好不好?
20
一個時辰後,夜幕低沉,扶稷終於從地牢里走了出來。
他右手提著劍,劍刃並藍色衣袍上沾滿了血跡,暗紅一片,臉上也濺了一滴滴鮮血,不知是他的還是九皇子的。
我想九皇子大抵是死了,我已經哭了太久,脫了力,斜靠在嬤嬤懷中。
扶稷空洞的眼神掃了我一眼,便彷彿沒有看到我般,直直地走進了咸陽宮那片黑暗中。
爹爹進了皇宮,帶著滿朝文武守了咸陽宮一夜,他們也擔心陛下自戕。
我在未央宮中獨坐到了天明。
第二日,扶稷安然無恙地走出了咸陽宮。
只是他滿身戰甲,嬤嬤告訴我,扶稷要御駕親征,討伐東夷了。
我素來知道異邦騷動,對我朝社稷心存不軌,但扶稷為何偏偏在這個時候選擇討伐東夷呢?
「五年前,九皇子勾結北狄南蠻西戎東夷造反。陛下這些年在外征戰,已顛了北狄、南蠻、西戎的政權。東夷是最後一個,而那日射殺小姐的塔樓兵,正是東夷人。」
扶稷出征時,我跑到城樓上去看他。
他高坐於駿馬之上,如同少時一般意氣風發軒然霞舉。
但他走得那麼蕭然決絕,彷彿皇城沒有什麼再值得留戀的了。
我突然害怕,扶稷會一去不復返。
扶稷走後,我在宮裡過上了一潭死水般的日子。
我免了諸少使的請安,日日和嬤嬤、鈴兒待在未央宮中。
嬤嬤總是安靜地陪著我,鈴兒是小姑娘,她可能也是怕我想不開吧,總是嘰嘰喳喳地尋些話來說,想逗我開心。
不過也好,這宮裡太安靜了。
鈴兒的名字取得真的很好,她的聲音清脆,就像一隻小鈴鐺。
而這些恰恰是我沒有的。
我說不了話,寫不出書信,可是情緒積壓在心中,總在尋找一個突破口。
於是我的淚腺變得格外發達,我總是無緣無故地就開始流眼淚。
我 日日靜坐在宮中以淚洗面,夜間做的噩夢格外清晰地閃現在我的腦海中。
我夢到了扶稷渾身是傷倒在戰場上,夢到了扶稷舉著匕首雙目猩紅地走向我,夢見了一個看不清臉的小娃娃跌跌撞撞奔向我,喊著「娘親」「娘親」。
我又開始做在沛縣時重複的夢,夢見了扶稷抱著我,淹在一片血海中。
我的身體愈發不好,心口總是絞痛,眼睛也酸痛。
扶稷是立秋時出征的,我在未央宮數著日子等了扶稷一整個輪迴。
秋,冬,春,夏。
第二年夏,扶稷在六月初二這一日凱旋歸京。
21
此時我的眼睛已經看不太清了,鈴兒和嬤嬤扶著我,去皇宮門口接扶稷回家。
我聽著耳邊噠噠的馬蹄聲,眼前卻霧茫茫一片。
有一道腳步聲向我靠近,我嗅到了熟悉的松柏香。
扶稷離我很近了,我眯著眼睛,這才堪堪看清他的臉。
他臉上的稜角更鋒銳了,有一些細小的傷口,索性並無大礙。
扶稷察覺出了我的異樣,瞳仁微顫,猶豫了一下,輕輕地抱住了我。
靠在扶稷懷中,我這才感覺到了安心。
【還好,你活著回來了。】
扶稷剿滅了東夷,還帶回來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聽說是先皇流落民間的皇子,扶稷將其立為了儲君。
第二天,扶稷來未央宮看我。
我倆面對面無言靜坐,扶稷嘆了口氣,打破了沉默。
「本就是小啞巴了,若是哭瞎了眼睛,可如何是好。」
第三天清晨,向來勤政的扶稷罕見地沒有上朝。
小太監說,扶稷尋了塊上好的黃花梨木料,在咸陽宮不知搗鼓些什麼。
下午的時候,扶稷又來看我了,還帶來了一根拐杖。
我有些意外,他今日未上朝,不會是在搗鼓這個玩意兒吧?
我同他比畫。
【你親手做的?】
他眼神閃躲,點了點頭。
「小啞巴,要愛惜身子,往後就由這根拐杖攙著你吧。」
幸福是虛無縹緲的,有些時候那麼遙遠,有些時候又好像努力伸伸手就可以夠到。
第四日,辰時開始宮中就十分熱鬧。
我同嬤嬤比劃,【宮外怎麼那麼吵?】
嬤嬤告訴我,今日是儲君繼位大典。
儲君?繼位?
那扶稷呢?我串聯起扶稷凱旋後這幾日的種種舉動,心中警鈴大作。
直覺告訴我,扶稷隱瞞了所有人。
嬤嬤將玉璽和一份聖旨遞給我,我顫抖著打開聖旨。
聖旨上說,冊封沛縣凝凝為凝夫人,輔佐幼帝。
若凝夫人百年後薨逝,特准葬於驪山別陵。
我急得將聖旨翻來覆去,上面卻隻字未提扶稷自己。
而驪山陵墓是扶稷另外督造的,葬的是忠臣與國士,但卻不是皇陵。
我驀然回想起進宮伊始,鈴兒同我說過的。
「高一等的長使同低一等的少使也沒什麼不同嘛,反正末了都是入不了皇陵的。」
為什麼偏偏是皇陵?
扶稷界限感強,從小他想守護的東西,都不允許旁人染指分毫,直覺告訴我,此事同「我」脫不了干係。
寧寧……長樂宮!
22
我發了瘋似的奔向長樂宮,如今我是輔佐幼帝的凝夫人,無人敢攔。
長樂宮還是收拾得一塵不染,我緩慢地走向殿中,每一步都似灌了鉛一樣沉。
殿中擺著兩具冰棺。
扶稷換上了大婚那日的婚服,躺在冰棺之中,了無生氣。
而旁邊另一具冰棺中躺著的,正是同樣一身紅裝的「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未央宮的,我跌了很多跤,膝蓋和手掌上皆是傷。
今日是繼位大典,爹爹是丞相和帝師,他整日都在宮中。
我讓嬤嬤去請來了寧丞相。
在宮門前,我將玉璽交給了爹爹,深深地給爹爹行了一禮。
【爹爹,女兒不孝。】
爹爹很惶恐,他慌張地扶起我,「凝夫人,老臣受之有愧。」
我了解爹爹的,他是兩代忠臣,往後,也會是三代忠臣。
爹爹走後,我同嬤嬤和鈴兒比畫,讓他們去御膳房給我做些牛乳酥酪來,我要帶給幼帝吃。
嬤嬤和鈴兒不疑有他,立刻去了。
對不起啊嬤嬤,我又支開了你。
我撐著扶稷送我的拐杖,一步步摸進了未央宮屋內。
我靜靜地坐在窗前,突然想起,今日也是六月初五啊。
是我上一世同扶稷原本的婚期。
我拔下頭上的簪子,攥在手中,我在等。
窗外響起了鑼鼓喧天的喜樂。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日與扶稷大婚時,也是一個鑼鼓喧天的黃道吉日。
我坐在長樂宮中,心中盛滿了嫁給心上人的羞澀、喜悅與期待。
時辰到了。
我奮力將簪子刺向心口。
「扶稷,我們成親啦。」
番外——
我是個道士,道號清微。
我是師門中最小最離經叛道的那個,但師父說我獨具慧根,將來宜承襲道觀大統,於是在而立之年我背著師門的寶器出門遊歷了。
我走到皇城,發現皇城沉浸在一片死亡的悲寂當中。
有個短鬍子的儒雅老頭來找我,他說他是當朝丞相,宮裡死了人,要請我過去超度。
我問他死的是誰,他說死的是新皇的未婚妻,他的女兒。
我心想,這小老頭有點東西,死了女兒還能強忍悲傷,四處籌謀,不愧是丞相,顧全大局!
但我是來遊歷的,師父也不喜歡我接私活,所以我拒絕了他。
小老頭硬拉著我不讓我走,說新皇扶稷已經把自己鎖在長樂宮七天七夜了,他們都怕皇上跟著殉情了,只有我能幫幫他們了。
我清微一身反骨,心想這不是道德綁架我嗎,但是他說出了新皇的名字——扶稷。
這我就來精神了,我們道士一直住在山上,擇亂世而出,從來不理會這些朝代更迭。
但扶稷我卻略有耳聞,這個小子在做太子的時候就致力於民生社稷,躬身力行,是個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
好吧,我是個惜才的人,那就跟著這老頭進宮勸勸扶稷那小子吧。
我進了宮才發現根本不是老頭說的那麼簡單。
扶稷這小子居然把人家姑娘的屍體擺在長樂宮裡還未下葬!
雖然用冰棺冰著,但最多也只可以保存一年。
他聽說我是被請來超度亡靈的道士,護著冰棺不準別人碰,又拉著我求我救救他的心上人。
可人死不能復生,我剛剛已經偷偷捏了個訣,看了這姑娘的命線,雖未入輪迴,但魂魄都已經離體了。
就算我是個道士,也改變不了這一點啊。
我跟他講我辦不到,讓他另擇高明。誰知道這小子立刻印堂發黑,身上有死相。
這不是吃准了本道長是個愛賢的,在以死相逼呢嗎!
看來這小子不僅是個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還是個世間難尋的痴情種。
罷了,我轉頭看了看身後的丞相老頭,是個滿臉都寫著「忠」「義」「禮」的老實人。
這樣的爹教出來的閨女又會差到哪裡去呢,那躺在冰棺里的姑娘看面相就是個純良心善的。
糾結之下,我做出了一個違背師門的決定——我把師門的寶器往生燈給了扶稷,還把我自己知道的通通一股腦告訴了他。
我跟他講了往生燈的用法,放在逝者身邊點燃了,可以保證他心上人的屍身不朽,同時也可以幫助他的心上人聚魂。只要往生燈不滅,他的心上人就有回來的可能,要是滅了那就徹底嗝屁,永遠都回不來了。
扶稷立馬活了,對我感恩戴德,但我讓他別高興得太早。
師父早就告訴過我,泄露天機,必遭天譴。
我同樣要提醒扶稷這件事背後的利害關係,我們這是在逆天改命,他的心上人到底回不回得來都說不準,而他是註定要遭大大的天譴反噬的。
我問他還干不幹,他義無反顧地沖我點點頭。
好吧,那就干吧!小毛頭都不怕,我這個老道長還怕什麼呢。
出了宮門我就吐了一口血,我不僅助紂為虐逆天改命,我還泄露天機,這天譴第一個遭在了我身上。
丞相老頭追在我後邊讓我先別走,我不知道他葫蘆里賣什麼葯。
誰知道他竟然給我深鞠一躬行了個大禮,眼裡閃著淚光,感謝我願意救他女兒。
他這一刻才卸下了為人臣的擔子,有了點父親的樣子。
媽的,我在心裡翻了個白眼,怎麼都是些好人,你們讓我說什麼好。
沒遊歷成功還丟了寶器,我悻悻回了山上。
師父問我可知錯,但我絲毫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不出意外,我被逐出了師門。
嚯,那我就正好繼續遊歷去了,在道觀里我已經學不到什麼了,最好的道就在世間人生百態中。
五年里我走了世間許多地方,我在一處富饒的鄉鎮歇歇腳,這裡原本是一個荒涼的漁村。
我果然沒看錯扶稷這小子,他將這天下治理得很好。
但這小子命也未免太苦了點吧,被親爹猜忌,被弟弟謀逆,死了老婆,痛不欲生還得對得起天下百姓。
媽的,這裡不是水鄉嗎?怎麼風沙這麼大,本道長的眼睛好酸。
這一天,萬念俱灰的扶稷找到我,告訴我往生燈滅了,問我可還有一線生機。
我遊歷不是白遊歷的,這些年也增添了一點知識儲備,確實還有另外的唯一一個辦法。
但是我看著眼前的扶稷,他如今執念已經太深了,我不知道告訴他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小子不好的就是太聰明了,他看出了我的猶豫,猶豫就說明有希望,他立刻「砰」一聲給我跪下了。
要死了!男兒膝下有黃金,他這膝下何止黃金啊,那是江山氣運啊!我不信這小子不知道這一點!
要命了要命了,被人皇一跪,我豈不是又要折壽了!
我趕緊扶他,他不肯起來,這小子也才二十三四歲吧,怎麼身上背負了這麼多呢。
我清微生平第一次心疼一個大老爺們。
我又做出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我告訴了他往生燈復燃的辦法。
聽說這小子回去後就開始割自己的心頭血給燈芯供燃。
這獃子!割哪兒的不好,偏偏割心口的。
我是真擔心那姑娘還沒醒過來,他自己就先嗝屁了。
於是我又去遊歷了。
活到老,學到老,或許我能獲取其他的信息呢,那小子長此以往地放血也不是個辦法。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遊歷了一年多,在一本失傳已久的秘本中了解到,往生燈一旦燃起後,如果好端端熄滅了,除了是逝者再也回不來之外,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逝者魂魄已經歸來!
我對於這一發現十分驚喜,我調轉方向,日夜兼程騎馬向皇城奔去,我得早點告訴扶稷這個消息。
我跑死了三匹汗血寶馬才趕到皇城,誰知道皇城中正舉國喪。
扶稷,你小子最好別給我出事!
我在城門口碰到了丞相老頭,他短鬍子都白了,看起來老了十歲。我最後的一點期待也破碎了。
媽的!扶稷你這小子怎麼不打招呼就死了!
丞相老頭帶我去了皇陵,扶稷的屍體就停在那兒。
我耳邊全是師父從前告訴過我的話:天譴不是固定的,但一定會以某種方式到來。
扶稷躺在冰棺當中,旁邊果不其然躺著他的心上人。
棺前有一墓碑,上頭刻著:吾妻寧寧。
我捏了個訣,我是實在想看看扶稷這小子同他心上人的命簿。
這也是我遊歷時學來的,當然,屬於窺探天機。
我咬了咬牙,折壽就折壽吧!
果不其然,扶稷這小子的命宮已經亂七八糟一塌糊塗了,沒有辦法,這都是逆天改命的反噬。
但在一團污遭中卻有一線新生的光亮,扶稷同他那心上人此生端的是情深緣淺的姻緣,就算死後也是不入同一輪迴道的。
可現在那光亮一點點擴大,兩輪魂魄牽繞著共入輪迴,端的是鸞鳳和鳴共白頭的姻緣!
我口中吐出一口鮮血,我看了眼冰棺中的扶稷,那小子神色安然,嘴角帶笑,想來死前應該是獲得了解脫的吧。
我清微生平第一次落淚,媽的,逆天改命,你小子成功如願了啊!
我又隨丞相老頭去了皇宮,他讓我再去給幼帝祈個福。
換在以往我是不會去的,但我看了看眼前這個鬍子花白的老頭,於心不忍。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聊表慰藉,他也辛苦了。
給幼帝祈完福,衝出來一個老嬤嬤和宮女攔住我的去路,他們說自己的主子凝夫人失蹤了,非要讓我幫忙去找找。
哎我說,怎麼皇宮裡的人都這麼會見縫插針啊!我腦門上寫著「勞碌」兩個字嗎?
不對,等等。
扶稷那心上人名字是不是也喚作「寧」來著?
我又踢踢踏踏跟著他們去了未央宮,一路上他們說門口的侍衛沒見凝夫人出來過,凝夫人就在屋中失蹤了。
未央宮裡還保留著凝夫人失蹤前的原狀未動過。
我環顧了一番,在窗前發現了一抔黃土並一隻染血的簪子。
我閉上眼,嘆了口氣,可不能再多說了。
我只能同那老嬤嬤和宮女說,他們的主子也如願了!
哎喲,可累死我了。
我要用我那所剩無幾的陽壽繼續雲遊去嘍!
江湖再見。
(完)
更多好看故事進入主頁→點擊文章→查看超爽故事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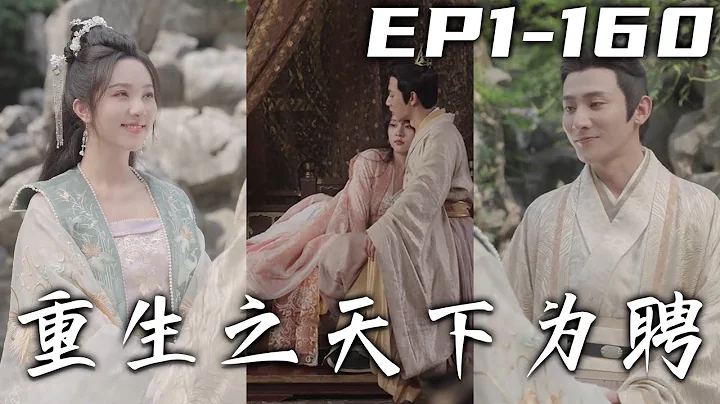





![【搞笑】虧成首富從遊戲開始 [EP176-255] #小說 #繁體中文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lx1W-xi5aEY/hq720.jpg?sqp=-oaymwEcCNAFEJQD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DQfu9hgfmB9IOhrITD1fLKK0Rf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