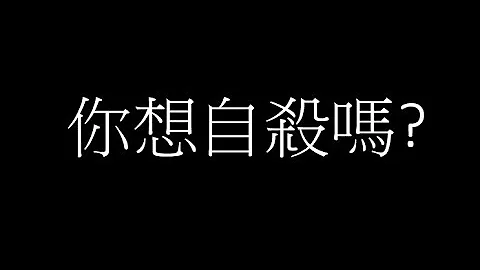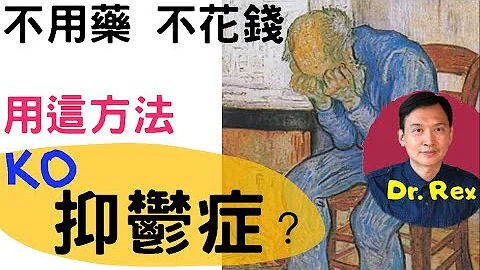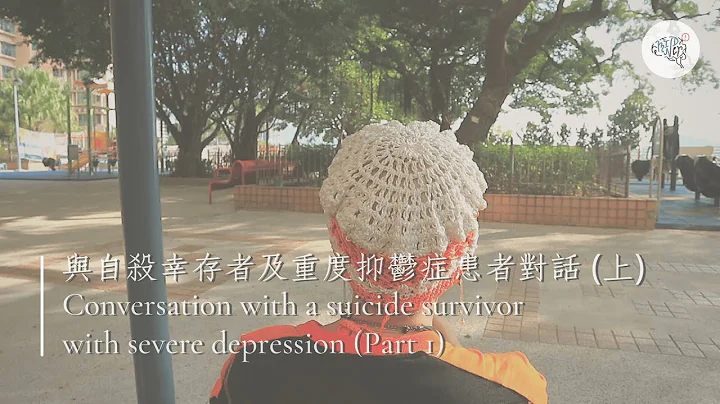《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中國精神衛生調查顯示,我國成人抑鬱障礙終生患病率為6.8%,其中抑鬱症為3.4%,目前我國患抑鬱症人數9500萬,每年大約有28萬人自殺,其中40%患有抑鬱症。
根據我國《社會保險法》第三十七條【1】和《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2】規定了認定工傷的三種除外情形,即:(1)故意犯罪;(2)醉酒或者吸毒;(3)自殘或者自殺。職工具有上述情形時,即使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認定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也不予認定工傷。
因此,「職場抑鬱症」因抑鬱症自殘或者自殺是否會被認定為工傷,也成了近年來我們律所接到比較多的法律諮詢。趁著最近幾天有空,我整理了近幾年相關司法裁判案例,探究在沒有相關法律將精神類疾病納入到職業病的範疇情況下,法院對「職場抑鬱症」以及其他精神類疾病是否屬於工傷如何進行認定?

一.因「身體傷害」導致精神疾病,由於身體傷害與精神傷害二者存在密切關聯,法院通常會將傷害整體看待,在符合一般工傷構成要件的情況下,因「身體傷害」導致精神疾病將被認定為工傷。
在(2019)閩04行終13號案件中,陳某系中學教師,2012年3月陳某在值班時發現學生傅某毆打老師,在勸阻過程中被學生周某打傷,造成嘴部受傷事故,2012年4月底治癒出院。2012年5月至7月期間,陳某因出現被毆打後應激障礙,先後到醫院治療抑鬱症。2012年7月6日早上,在前往醫院就診時走失,後屍體被發現,經公安局法醫鑒定陳某為自殺。2013年6月26日,經公安局委託,XXX司法鑒定所作出《法醫精神病鑒定文證審查意見書》,其鑒定意見為:陳某生前精神狀態與2012年3月30日被毆打事件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係。
2012年7月26日,陳某所在學校向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人社局認定陳某在值班過程中受到的傷害為工傷。2013年7月5日,陳某妻子因陳某死亡向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2013年7月16日,人社局認定陳某的自殺行為,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認定工傷或視同工傷的情形,不予認定為工傷或視同工傷。
法院認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的規定,自殘或者自殺不得認定為工傷。但本案中,陳某於2012年3月在學校值班過程中被學生用石塊砸傷已認定為工傷。因陳某在自殺時系處於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影響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誘發的自殺,是患者精神障礙影響下的病態自殺,這與《工傷保險條例》中工傷排除的「自殘與自殺」中的與工作沒有必然聯繫的故意自殺非同一性質。
對工傷直接導致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誘發的自殺,是工傷傷情進一步的延續和發展,認定該情況為工傷,是符合「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制定本條例」的立法精神。
因此,判決撤銷人社局所作《工傷認定決定書》,並責令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為。二審法院支持了一審法院的觀點,維持原判。
二.因工作中的「特殊刺激」導致的精神疾病,如果在醫學上可以證明,員工在工作中受到該類刺激則必然引發相應的精神疾病,則屬於工傷,反之亦然。大部分普通人並不會因受到此類刺激而激發精神障礙,即不構成必然因果關係,不能認定為工傷。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在張紅仁、甘肅省金昌市人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管理(勞動、社會保障)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行政裁定書中認為:本案中,張紅仁主張其患精神分裂症系工作環境惡劣所致,因此本案的核心即在於張紅仁所患精神分裂症是否屬於工作原因引起。
參照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GB/T16180-2006)c.2.2的規定,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均為內源性疾病,發病主要決定於鬱症人自身的生物學素質。在工傷或職業病過程中伴發的內源性疾病不應與工傷或職業病直接所致的疾病相混淆。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不屬於工傷或職業病性疾病。
本案張紅仁患精神分裂症之前既未受到事故傷害或意外傷害,亦未被診斷為職業病,故其所患精神分裂症既不是工傷或職業病直接所致,也不是工傷或職業病過程中伴發而生。工作環境惡劣可能會影響張紅仁身心健康,從而誘發精神分裂症,但患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張紅仁自身的生物學素質,因此工作環境惡劣與精神分裂症之間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不能認定其所患精神分裂症系由工作原因引起。
三.「工作壓力大」導致精神疾病。結合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對於該類由工作引發的「慢性」疾病,只有在滿足《職業病防治法》中「職業病」之內涵界定的情況下,方構成工傷。目前我國並未有相關規定將精神類疾病納入多職業病的範疇。因此,工作壓力大導致的精神類疾病不構成工傷。
案例:原告姜凱原系首都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網路工程師,與該公司簽訂了期限為2009年6月11日至2012年2月25日的勞動合同。2010年6月4日,首信公司向姜凱出具了解除/終止勞動關係證明。同時,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及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等醫院出具診斷證明認為,姜凱患有重度抑鬱症伴發精神分裂症等癥狀。之後其父代其向行政機關申請工傷,該案經過行政複議、行政訴訟均不予認定工傷。
法院均認為:本案中相關醫學證明書載明原告患有精神分裂症等病症,但目前並未有證據表明原告上述病症系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而導致,亦未有證據證明其病症屬職業病。因此,不構成工傷。

四.認定工傷的舉證責任
對於是否存在「自殘或自殺」的認定,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4]9號)第一條,也應當以有權機構(如公安機關、醫療機構)出具的結論性意見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書為依據。對於前述法律文書不存在或者內容不明確,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就前款事實作出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其提供的相關證據依法進行審查。
比如職工發生墜亡或溺亡,公安機關的結論性意見為「排除他殺」,無法查明死因是否為「自殺」時,法院一般會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二款:「職工或者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定為工傷的情形第(一)項:「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受到傷害,用人單位或者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沒有證據證明是非工作原因導致的;」之規定,支持應認定工傷的結論。
另外,實踐中對於「自殘或自殺」的爭議還包括當員工因工作原因自殘、自殺,或者因精神疾病導致非自主性自殘、自殺時是否構成工傷。對此,社保行政部門及裁審機關尚較謹慎,僅有少數案例認定了工傷。
五.結論:
當職工出現因重度抑鬱而出現自殺或自殘等行為時,用人單位需注意,該種情形不必然被排除認定工傷,還需結合職工的患上抑鬱症而自殺是否為工作原因導致的,與工作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職工因抑鬱而自殺的具體情形進行具體分析。
參考資料:
1.《社會保險法》第三十七條
2.《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
3.中國裁判文書網:(2019)閩04行終13號案件
4.《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GB/T16180-2006)c.2.2的規定
5.《職業病防治法》
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4]9號)第一條
7《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