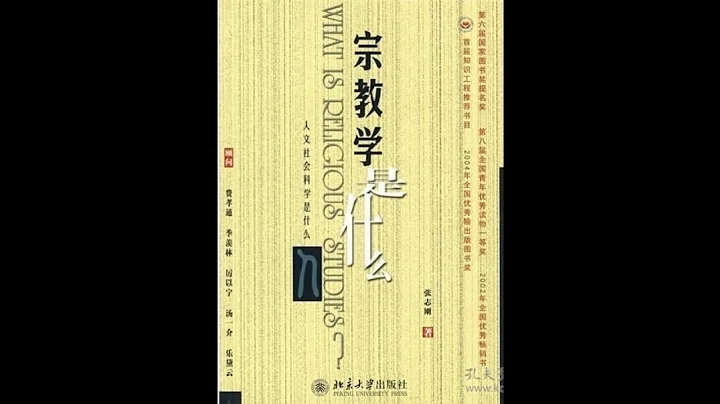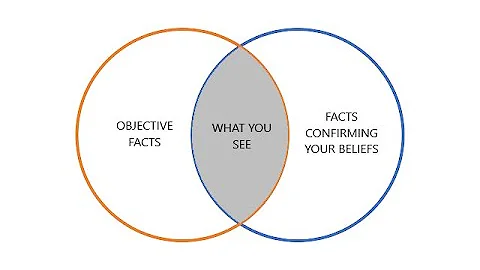專題導言
本專題旨在對巫術研究進行掛一漏萬的呈現,試圖通過例舉巫術研究中的若干重要文獻片段,描摹出人類學、社會學、以及中國學者對於巫術研究的圖景。
首先,第一部分(no.1-no.6)將聚焦於人類學視角的巫術研究。歐文·戴維斯編著的《巫術的歷史》向我們介紹了人類學中巫術研究的若干關鍵時刻。進而從泰勒、弗雷澤、馬林諾夫斯基和列維—斯特勞斯再到大衛格雷伯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學家是如何對巫術進行定義、解構、及能動性的分析。考察巫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現形式、社會功能及其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
其次,第二部分(no.7-no.9)將著重於社會學的視角下對巫術的研究。我們將從塗爾乾的《宗教生活基本形式》、韋伯的《中國的宗教 宗教與世界》到顧忠華的《巫術、宗教與科學的世界圖像》入手,探討巫術與社會結構、權力關係以及文化認同之間的相互作用。通過社會學的分析框架,我們將深入探討巫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功能、影響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聯。
多數情況下,學者們將「巫術→宗教→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發展的普遍路徑,將巫術作為一種具有完善個人、組織社會、成為象徵的存在。但是這種界定是基於西方歷史事實所作出的抽象歸納,巫術的發展在中國可能更為複雜。
最後的第三部分(no.10-no.12)將聚焦於中國研究者對巫術的研究。我們將從楊清媚對於陶雲逵占卜研究的分析,林富士對於中國古代巫覡的社會形象與政治形象的討論,再到李澤厚巫史傳統的闡發入手,探討古代中國的巫術實踐,歸納巫術在中國文化和社會中的演變與影響。
鳴謝
專題策劃人:阿土
詹姆斯·喬治·弗雷澤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英國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神話和宗教,最著名的作品是《金枝》(the golden bough),這是一部涉及宗教、神話和民間信仰的重要著作,被認為是人類學和宗教研究的經典之作。
上一章所搜集的事例,可能足以闡釋交感巫術兩個分支的一般原則。那兩個分支我們曾分別命名為「順勢巫術」和「接觸巫術」。我們看到,在前面所列舉的某些事例中,首先確認有神靈存在,並且還以祈禱和奉獻供品來贏得神靈的庇護。但總體來說,這類事例尚屬少數,它們只表明,巫術已染上並且摻和了某些宗教的色彩和成分而已。無論在任何地方,只要交感巫術是以地道的、純粹的形式出現,它就認定:在自然界一個事件總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接著另一事件發生,並不需要任何神靈或人的干預。這樣一來,它的基本概念就與現代科學的基本概念相一致了。交感巫術整個體系的基礎是一種隱含的,但卻真實而堅定的信仰,它確信自然現象嚴整有序和前後一致。巫師從不懷疑同樣的起因總會導致同樣的結果,也不懷疑在完成正常的巫術儀式並伴之以適當的法術之後必將獲得預想的效果,除非他的法術確實被另一位巫師的更強而有力的法術所阻擾或打破。他既不祈求更高的權力,也不祈求任何三心二意或恣意妄為之人的讚許,也不在可敬畏的神靈面前妄自菲薄,儘管他相信自己神通廣大,但絕不蠻橫而沒有節制。他只有嚴格遵從巫術的規則或他所相信的那些「自然規律」,才得以顯示其神通。哪怕是極小的疏忽或違反了這些規則或規律,都將招致失敗,甚至可能將他這笨拙的法師本人也置於最大的危險之中。如果他聲稱有某種駕馭自然的權力,那也只是嚴格地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完全符合古代習慣的基本威力。因而,巫術與科學在認識世界的概念上,兩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認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規律的和肯定的。並且由於這些演變是由不變的規律所決定的,所以它們是可以準確地預見到和推算出來。一切不定的、偶然的和意外的因素均被排除在自然進程之外。對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並能接觸到這部龐大複雜的宇宙自然機器運轉奧秘發條的人來說,巫術與科學這二者似乎都為他開闢了具有無限可能性的前景。於是,巫術同科學一樣在人們的頭腦中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強有力地刺激著對於知識的追求。它們用對於未來有著無限美好的憧憬,引誘那疲倦的探索者、睏乏的追求者,讓他穿越過當今現實感到失望的荒野。巫術與科學將他帶到極高的山峰之巔,在那裡,越過他腳下的滾滾濃霧和層層烏雲,可以看到天國之都的美景,它雖然遙遠,但卻沐浴在理想的光輝之中,放射著超凡燦爛的光華!
巫術的嚴重缺點,不在於它對某種由客觀規律決定的事件程序的一般假定,而在於它對控制這種程序的特殊規律性質完全錯誤的認識。如果分析一下前面考查過的交感巫術的各種情形(它們是作為恰當的實例而經過選擇的),我們就會發現,正如我曾指出過的那樣,它們都是對思維兩大基本規律中的這一或那一規律的錯誤運用。這兩種思維的基本規律就是空間或時間中的「相似聯想」和「接觸聯想」。錯誤的「相似聯想」產生了「順勢巫術」或「模擬巫術」,錯誤的「接觸聯想」產生的則是「接觸巫術」。這種聯想的原則,本身是優越的,而且它在人類的思維活動中也確實是極為基本的。運用合理便可結出科學之果,運用不合理,則只能產生科學的假姐妹——巫術。因此,說什麼「一切巫術必然是荒謬的和無益的」,這完全是多餘的老調。因為,如果巫術能變為真實並卓有成效,那它就不再是巫術而是科學了。早在歷史初期,人們就從事探索那些能扭轉自然事件進程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普遍規律。在長期的探索中他們一點一點地積累了大量的這類準則,其中有些是珍貴的,而有些則只是廢物。那些屬於真理的或珍貴的規則成了我們稱之為技術的應用科學的主體,而那些謬誤的規則就是巫術。
巫術就這樣成為了科學的近親。但我們仍須追問,它與宗教又有著什麼關係呢?我們腦海里早已形成的關於宗教本質的概念,將必然影響我們對這兩者關係的認識。因此,每一個作者在著手調查宗教與巫術的關係之前,總是先提出他自己關於宗教的概念。世界上大概沒有比關於宗教性質這一課題的意見更紛紜的了,要為它擬出一個人人都滿意的定義顯然是不可能。一個作者能做的僅僅是:首先講清楚自己所說的宗教指的是什麼,然後在整個作品中前後一致地使用這同一含義的詞。我說的宗教指的是:相信自然與人類生命的過程乃為一超人的力量所指導與控制的,並且這種超人的力量是可被邀寵或撫慰的。這樣說來,宗教包含理論和實踐兩大部分,就是:對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討其歡心、使其息怒的種種企圖。這兩者中,顯然信仰在先,因為必須相信神的存在才會想要取悅於神。但這種信仰如不導致相應的行動,那它仍然不是宗教而只是神學。用聖雅各的話說:「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換句話說,如果某人的立身處世不是出於對神某種程度的敬畏或愛戴,那他就不是一個宗教信徒。另一方面,若只有行動卻排除了一切宗教信仰,那也不是宗教。兩個人的行為可能完全一致,然而可能一個是宗教信徒,而另一個卻不是;如果其中一人的行為是出於對於神的愛或怕,他就是一個教徒;如果另一個人的行為是出於對於人的愛或怕,那他就是一個品行端正或不端正的人,這需根據其行為與公眾利益相一致或相抵觸而定。因而信仰和實踐,或者用神學的語言說即道和行,同樣都是宗教的基礎,二者缺一不可。但宗教實踐並不總是非要舉行儀式不可,也就是說它並不一定要供獻祭物、背誦禱詞及採取其他外表形式。這些形式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取悅於神。如果這位神喜歡仁愛、慈悲和貞潔更甚於帶血的祭品、讚歌和香火,那麼他的信徒們使他高興的最好的做法,就不是拜倒在他腳下,吟誦對他的讚詞,或用貴重禮物擺滿他的廟宇,而是以廉潔、寬厚、仁慈去對待芸芸眾生。因為這樣做人們就會盡人類的柔弱心靈之可能去模仿神性的完美無缺。希伯來的先知們出於對上帝的美好與神聖的崇高信念而孜孜不倦地教誨人們,正是宗教的這一倫理學的方面。正如彌迦所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而在以後的一個時期里,基督教用以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這種對上帝的道德性質的崇高信念和人們使自己遵奉上帝的責任感。聖雅各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
但是,如果宗教所包含的首先是對統治世界的神靈的信仰,其次要是要取悅於它們的企圖,那麼這種宗教顯然是認定自然進程在某種程度上是可塑的或可變的,可以說服或誘使這些控制自然進程的強有力的神靈們,按照我們的利益改變事物發展的趨向。現在,這種關於自然具有可塑性或可變性的暗示,恰恰同巫術以及科學的原則相對立。它們二者都認定自然的運轉過程是固定不變的,既不可能用說服和哀求,也不可能用威脅和恐嚇來稍加改變。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宇宙觀之差異,取決於它們對這樣一個關鍵性問題的回答:統治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有意識的和具有人格的,還是無意識的、不具人格的?宗教,作為一種對超人力量的邀寵,所認定的是兩個答案中的前者。因為所有的邀寵做法都暗示著那位被討好者是一個具有意識或人格的行為者,他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定的,可以被勸說來按照人們所希望的方向改變,只要這種勸說審慎地投合他的興趣、口味和感情。人們絕不能向那些被看成是無生命的東西討好,也不會討好那些在特殊情況下已知其行為確實被絕對限定的人。總之,宗教認定世界是由那些其意志可以被說服的、有意識的行為者加以引導的,就這一點來說,它在基本上是同巫術以及科學相對立的。巫術或科學都當然地認為,自然的進程不取決於個別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取決於機械進行的不變的法則。不同的是,這種認識在巫術是暗含的,而在科學卻毫不隱諱。儘管巫術也確實經常和神靈打交道,它們正是宗教上所假定具有人格的神靈。但只要它們按其正常的形式進行,它對待神靈的方式實際上和它對待無生物完全一樣,也就是說,是強迫或壓制這些神靈,而不是像宗教那樣去取悅或討好它們。因此,巫術斷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對象,無論是人或神,最終總是從屬於那些控制著一切的非人力量。任何人只要懂得用適當的儀式和咒語巧妙地操縱這種力量,他就能夠繼續利用它,例如在古埃及,巫師們宣稱他們有能力迫使甚至最高的天神去服從他們,並且確曾對天神發出如抗拒即予毀滅的威脅。有時巫師雖然尚未達到那種地步卻也宣稱過類似的恐嚇:如果奧錫利斯不服從他的命令,他將到處亂扔它的骨頭或揭露關於它的傳說;同樣,今天在印度還有類似的情況:偉大印度教的三相神婆羅賀摩、毗濕奴、濕婆也受男巫師們支配。他們用其符咒指揮這些至高無上的神靈:無論在地下或在天上神祇們必須恭順地執行巫師們的任何要求。在印度到處流傳著這樣的話:「整個宇宙聽從天神的支配,天神們聽從符咒(曼哈斯)的支配,符咒聽從婆羅門支配,因此,婆羅門是我們的天神。」
巫術與宗教之間在原則上的根本抵觸,足以說明在歷史上為何存在祭司經常追擊巫師的這種毫不放鬆的敵意。巫師的驕傲自滿和對更高權力的妄自尊大的態度,以及滿不在乎地宣稱他擁有和神靈同樣權力的做法,都不能不引起祭司的厭惡。從祭司對神權的敬畏和在神面前那種卑躬屈膝的表現來說,這樣的聲稱和態度必然被看成是在篡奪僅屬於上帝的特權,而這是極邪惡而不恭的。我們還可以想到,巫師們的動機有時比較卑劣,這會更加激起祭司的敵意。祭司既然自稱是上帝和人之間的正當媒介、真正中間人的角色,無疑他的利益,以及他的感情常被對手巫師所傷害。這個競爭對手勸導人們走一條更為可靠和平坦通往幸福的途徑,以代替為獲得神的恩惠所要走的崎嶇不平、不可靠的道路。
然而,我們已如此熟悉的這種對立,似乎只是在宗教歷史的較晚時期才清楚地表現出來。在較早階段,祭司和巫師的職能經常是結合在一起的,或更確切地說,他們各自尚未分化出來。為了實現其願望,人們一方面用祈禱和奉獻祭品來求得神靈們的賜福,而同時又求助於儀式和一定形式的話語,希望這些儀式和言辭本身也許能帶來所盼望的結果而不必求助於鬼神。簡言之,他同時進行著宗教和巫術的儀式,也幾乎是同時喃喃地念著禱詞又念著咒語,並不注意他的行為和理論之間的矛盾,只要能設法獲得其所需就好。我們已在美拉尼西亞人及其他民族中見到過這種把宗教和巫術融合或混淆在一起的事例了。
宗教和巫術的這種混淆還一直殘留在那些文化程度較高的民族中,既曾經流傳在古印度和古埃及,也沒有從現代歐洲農民中消失。關於古印度的情況,一位名聲顯赫的梵文學者告訴我們說:「據我們掌握的詳細資料,早期歷史上的獻祭儀式普遍帶有原始的巫術精神。」談到東方的巫術特別是在埃及的重要性時,馬伯樂教授強調說:
我們不應當對巫術這個字眼抱有那種在現代人心目中幾乎不可避免地引起的鄙夷的看法。古代巫術正是宗教的基礎。虔誠的、要想獲得神的恩惠的人,除非雙手抓住神,否則就沒有成功的機會。而這隻有通過一定數量的典儀、祭品、禱詞和讚歌等等才能得到。神自己也啟示過,只有這樣對待它,才能使它去做那些要求它做的事。

馬伯樂(gaston maspero,1846-1916),法國學者,埃及學家。[圖源:wikipedia]
在現代歐洲愚昧的階層中,這種類似觀念上的混淆,這種把宗教和巫術混在一起的情況,常以不同的方式出現。我們曾聽說,在法蘭西,「大多數農民仍然相信祭司擁有一種神秘的、不可抗拒的、駕馭自然的力量。一旦遇到燃眉之急,透過背誦那些只有他才知道和有權說出的禱詞,他便能夠在一段時間內阻止或顛倒物質世界的永恆運轉規律,儘管為了這種禱告,他必須緊跟著就請求神的赦免。風、雹、雷、雨都聽從他的指揮,服從他的意志,連火也聽他調遣,只要他一句話就可撲滅一場火災的烈焰」。例如,法國的農民也許至今仍在相信祭司們能夠以一種特定的儀式來做「聖靈彌撒」。這種彌撒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它從未遇到過任何神靈的反對。上帝也不得不在這種情況下同意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不管這種要求是多麼輕率和糾纏不休。在那些生活極為窮困的人們心裡,由於企望以這種簡單的手段佔領天國,所以對這樣的儀式絕無任何不虔誠或不恭敬的想法。世俗祭司通常拒絕這種聖靈彌撒,但僧侶們,特別是聖方濟清教派的僧侶們,卻負有盛名,願意滿足急切而痛苦的懇求。天主教國家的鄉下人認為神父們具有敦促神做這做那的本領,這同古埃及人認為他們的巫師所具有的那種特殊本領極為相似。
再舉一例:在普羅旺斯的許多鄉村裡,人們仍然相信神父具有消除暴風雨的本事。當然並不是每一個神父都享有這種聲譽。在有的村子裡,每當調換教堂神父時,教區中的居民們就急於了解新任神父是否具有這種他們所謂的「道行」。當一次大風暴的第一個徵兆出現之時,他們就邀請他來驅趕可怕的烏雲,以此對他進行考驗。如果正好如願以償,這位新來的神父就贏得了他的教徒們的信賴和尊敬。在有些教區里,教區神父在這方面的威望比他的教區長更高一些,因而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如此緊張,以致主教不得不將教區長調任別的聖職。還有,加斯科涅的農民相信這樣的事:壞人有時會誘勸牧師念一種叫做「聖色伽利」的經文,用以報復他的仇人。只有很少的神父知道這種經文,而他們當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又不願為人情或金錢念這種經文。除了那些不道德的神父,沒有人敢舉行這種肯定最後的審判日將會為之付出沉重代價的可伯儀式。任何教區神父、主教甚至奧什的大主教都不能赦免他們,只有羅馬教皇本人才具有這種赦免權力。這種「聖色伽利」彌撒只能在一座荒廢的或已毀壞的教堂里舉行。在那裡,貓頭鷹愁悶地叫著,蝠蝠在黑暗中亂飛,流浪者夜宿於其中,而癩蛤蟆匍匐在被褻瀆的聖壇之下。那位邪惡的神父帶著他的輕佻的情婦在夜裡來到這裡。當十一點的鐘聲敲響第一聲時,他就開始咕噥著倒背經文,而恰好在鐘聲發出午夜的哀鳴時終止。他的情婦充當著他的執事,他那祝福用的聖餅是黑色且帶有三個尖角,他不供酒但卻喝一種井水,在那並里曾扔進過未受洗禮的嬰兒。他也畫十字,但卻是用他的左腳在地上畫的。他還做其他的許多事情,任何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看到這一切都會被嚇得終身說不出話來。而他用經文詛咒的那個人也將慢慢地衰弱,任何人都說不出他究竟害了什麼病,甚至連醫生也束手無策,他們並不知道此人是由於「聖色伽利」經文的詛咒而慢慢死掉的。
雖然在許多世紀里和許多國土上巫術與宗教相融合、相混淆,但是我們仍然有理由認為這種融合併非自始即有,曾有一個時期人們為滿足他們超越一般動物需求的願望而只相信巫術。首先,考慮到巫術與宗教的基本見解,我們就傾向於作出這樣的判斷:在人類歷史上巫術的出現要早於宗教。我們已經看到:一方面巫術僅只是錯誤地應用了人類最簡單、最基本的思維過程,即:類似聯想或接觸聯想;另一方面,宗教卻假定在大自然的可見的屏幕後面有一種超人的、有意識的、具有人格的神存在。很明顯,具有人格的神的概念要比那種關於類似或接觸概念的簡單認識要複雜得多,認定自然進程是決定於有意識的力量,這種理論比起那種認為事物的相繼發生只是簡單地由於它們互相接觸或彼此相似之故的觀點要深奧得多,理解它必須有一種更高的智力和思考。甚至野獸也會把那些彼此相似的東西或在它們經驗中被一起發現過的東西聯繫起來,如果它們不這樣做就連一天也難以生存下去。但有誰會認為野獸也具有信仰,即它們也相信大千世界是由在其背後一群看不見的野獸或一個極為巨大神奇的野獸所操縱的呢?如果我們把發明這樣一種理論的榮譽留給人類的理性,對於無理性的野獸來說,大概沒有什麼不公正的吧!假如巫術是直接從推理的基本程序中演繹出來的,而且實際上人的思想幾乎也毫無自省地陷在誤信之中,那麼,宗教則是以非愚昧的心智所能企及的一些概念為基礎的。所以,很可能是:在人類發展進步過程中巫術的出現早於宗教的產生;人在努力通過祈禱、獻祭等溫和諂媚手段以求哄誘安撫頑固暴躁、變幻莫測的神靈之前,曾試圖憑藉符咒魔法的力量來使自然界符合人的願望。
這種從巫術與宗教的基本概念推演出來的結論,已為我們對澳大利亞土著民族的觀察結果所證實:在那些我們已掌握準確資料的最原始的野蠻人中間,巫術是普遍流行的;而被視為對更高權威的一種調解或撫慰的宗教則幾乎不為人所知。可以粗略地說,在澳大利亞所有人都是巫師卻沒有一個人是神父;每一個人都自以為能夠用「交感巫術」來影響他的同伴或自然的進程,卻沒有一個人夢想用祈禱和祭品來討好神靈。
既然在目前已知的人類社會的最落後狀態里,我們發現巫術是如此明顯地存在而宗教卻顯然不存在,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據此推測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在他們歷史的某個階段也經歷過類似的智力狀態,即在他們想用獻祭和禱詞來討好自然偉力之前也曾企圖強迫它服從於自己的意願呢?簡言之,是否如人類文明在物質方面到處都有石器時代一樣,在智力方面各地也都有巫術時代呢?我們有理由對這個問題給予肯定的回答。當我們從格陵蘭到火地島,從蘇格蘭到新加坡綜觀人類現存的各個種族之時,我們觀察到它們都各具不同且種類繁多的宗教。我們還觀察到這種宗教種類之繁雜不單是跟那些種族一樣地眾多,而且還深人到各個國家和聯邦,滲透到各個城市、村莊甚至家庭之內,以致在宗教紛爭具有的分裂特點的影響下,整個人類社會的外觀是破碎的、龜裂的、受到削弱和破壞,因而呈現出許多裂隙和分歧。但是,宗教體系的矛盾分歧主要是影響著這些社會中善於思考的知識階層,一旦走出這矛盾分歧的範圍,我們就會發現,愚昧的、軟弱的、無知和迷信的人們在信仰問題上是完全和諧一致的,不幸的是,正是這些人佔了人類的大多數。19世紀的一項重大成就乃是把研究深人到世界許多地方智力底下的階層,從而弄清了各地在實質上都是一樣。這個智力底下階層就在我們腳下,就在今天的歐洲,並且也在澳大利亞荒無人煙的中心地帶和已有教育文明但尚未使它完全絕跡的一切地區。對於巫術功效的信仰,是一種真正全民的、全世界性的信仰。
當宗教體系不僅在不同國家而且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代都有所不同之時,交感巫術體系的原則和實踐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保持了實質上的相似。現代歐洲的無知和迷信階層中的情況跟幾千年前在埃及和印度的情況十分相似,也跟目前還生存於世界最偏僻角落的最原始野蠻部落中的情況十分相似。如果可以按舉手或人頭計算辦法來測定真理的話,那麼巫術體系就比天主教會更有理由引用這一豪言,作為自己絕對正確的憑證:「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人所共知」。
我們並不打算在此考慮這樣的問題:在社會的表層下,如此牢固且不受宗教和文化表面變化影響的愚昧階層之長期存在,對於人類的未來有何影響?任何不持偏見的觀察者,只要他的研究工作使他探測到這個問題的深度,就很難不將其視為對文明的一種長期的威脅!我們好像是行走在一個薄殼之上,隨時都可能被隱藏在下面正在打盹的力量所破碎。偶爾從地底下發出的一聲空響,或突然進發到空中的一點火焰都會告訴我們,腳底下正進行著什麼。這個文明世界不時被報上發表的這樣的消息所震驚:在蘇格蘭怎樣發現了一個偶像被扎滿了針以達到殺死一位可憎的地主或大臣的目的;在愛爾蘭一個女人怎樣被當成一個女妖而被慢慢的烤死;或者在俄羅斯一個姑娘怎樣被暗殺和剁碎,以便竊賊們製作那種他們所希望的在夜間既能用其光源又可保證其行竊勾當不被人看見的人脂蠟燭!
但究竟是為推動進步而出現的勢力,還是對已獲得的成就具破壞危險的勢力終將獲勝呢?究竟是少數人的衝擊能量還是人類大多數極為沉重的分量,是能使我們上升到更高水平或沉落到底層的力量呢?這些問題與其說是應由過去和現在的卑微學者解答,不如說是應由聖人、道德家和以其銳敏的目光審視著未來的政治家來解答。我們在這裡要研究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同宗教信仰的無窮多樣性、多變性相比,巫術信仰呈現了單一性、普遍性和永恆性。那麼我們如何據此而引出這樣的假說,即:巫術體現了人類更早歷史時期的、更為原始的思想狀態,全人類各種族也都曾經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這一狀態而走向宗教與科學?
如果正如我所冒昧臆測的那樣:在所有地方都是宗教時代跟著巫術時代之後到來,我們自然要問:是什麼原因使得人類,更確切地說是人類的一部分,放棄了作為一種信仰和實踐根源的巫術而投身於宗教呢?當我們仔細想想需要解釋的事實的龐大數量及其多樣性與複雜性,以及有關它們的調查尚不很充分之時,我們將隨時承認這一點:對於這樣深奧的問題很難指望得到一個充分和滿意的答案。而就我們目前所具有的知識狀況,我們最多只能大膽地提出一種或多或少近似合理的假說。我懷著應該有的審慎精神,準備提出這樣一個假說:日久天長,對於巫術所固有的謬誤和無效的認識,促使人類之中更富于思想的人們去尋求一種關於自然的、更為真切的理論,利一種更為有效地利用其資源的方法。較為精明的人們到一定時候就覺察出了:巫術的儀式和咒語並不能真正獲得如他們所希望產生的結果,而頭腦比較簡單的大多數人們還仍然相信。這種對於巫術無效的重大發現,必然會在那些精明的發現者的思想上引起一種可能是緩慢的但卻是帶根本性質的革命。這個發現的意義是:人們第一次認識到他們是無力隨意左右某些自然力的。但迄今為止他們卻相信這些自然力是完全處在他們的控制之中,這是一種對人類的無知和無力的反思。人們看到了他原來以為是動因的東西實際卻不是動因,而他憑藉這些動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他的痛苦的辛勞已被虛耗,他驚人的巧智也已被無目的地浪費,他曾經使勁地提拉過沒有系住任何東西的繩索,他曾以為他正向著自己的目標前進,而實際上只是在一個狹小的圓圈裡打轉轉。並非他努力製造的效果不再繼續顯現出來,它們仍被製造出來,不過那並不是他製造出來的:雨仍然落在乾渴的土地上,太陽仍然繼續著它的日出日落,而月亮繼續著它橫貫天空的夜遊;四季的更替也繼續在大地上無聲地進行著;在光亮和陰影之中、在烏雲和陽光之下,人們仍然降生在這個世界上,辛勤勞作,經受痛苦,仍然在世上短暫寄居之後又聚集到父輩居住的墳墓里。儘管一切都確實在照舊進行,然而由於過去的障眼蔭翳已經剝落,因此一切在他看來卻不同了。他已不再可能沉湎於他的愉快的幻想中:正是他引導著大地和上天的運行,而且一旦他把自己孱弱的手撤離大自然的車輪時,那它們就會停止那偉大的運轉。現在,他在他的敵人和朋友們的死亡過程中,再也見不到自己或自己仇敵的法術具有什麼不可抗拒的力量了。他現在知道了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得屈從於一種力量,這個力量比任何他所能支配的都更為強大,因而大家都得服從於一種他無力控制的命運。
就這樣,我們的原始哲學家,當他的思維之船從其古老的停泊處被砍斷繫繩,而顛簸在懷疑和不確定的艱難的海上時,在他原來的那種對自身以及對他的權力的愉快信心被粗暴地動搖之後,他必曾為此悲哀、困惑和激動不已,直到他那思維之船,如同在充滿風暴的航行之後進入一個安靜的避風港一樣,進入一種新的信仰和實踐的體系之中為止。這種體系似乎解答了那些使他陷入煩惱的懷疑,並且替換了他原本不願放棄的統治自然之權力,儘管這種替換是危險的。他還認為如果這個偉大的世界竟然可以不用他和他的同夥們的幫助而照常運行下去,那就必然另有別的像他一樣的人物,不為人們所見,卻遠為強大有力.指揮著世界的運行並引出所有變化萬千的事件來。而這些事件迄今為止他都以為是憑藉他自己的巫術才實現的!他現在相信了:正是他們而不是他自己,使暴風呼嘯,使閃電輝耀,使驚雷轟鳴;正是他們為堅固的大地奠定了基礎,給不可逾越的洶湧的大海以限制,使天上那無數光輝的星辰發亮,給天空中的飛禽以食物,給沙漠中的猛獸以被捕食的動物;是他們令沃土產生碩果,讓高山覆蓋著森林,叫涓涓的泉水從山谷的石頭下面噴涌而出,使綠色的牧草長滿寧靜的水邊;正是他們向人的鼻孔里吹氣使人獲得生命或用饑荒,瘟疫和戰爭促其滅亡。對於這些強有力的人物,他已在大自然的一切輝煌壯觀的萬千景象中看到了他們的行為的後果。人現在謙卑地承認自己要依賴於他們那看不見的權力,懇求他們的憐憫,懇求他們賜予他一切美好的東西,保護他免遭從各個方面威脅著他有限生命的危險與災難,最後,在痛苦和悲哀到來之前,將他的靈魂從軀體的重負下解脫出來,帶到一個更為歡樂的世界去,在那裡他可以和一切好人的靈魂永遠同在,享受安寧與幸福。
可以想像:具有比較深刻思想的人們正是在這樣的或類似這樣的思想下做出了從巫術到宗教的偉大轉變。但即使在這些智者中間,這種轉變也難以突然產生。這個過程可能是十分緩慢的,它的最終完成需要漫長的世紀。因為要廣泛地樹立關於「人無力去影響自然進程」的認識,只能是漸進的過程。不可能在一擊之下就剝奪掉他幻想的所有統治權。一定是一步一步地把他從驕傲的地位上擊退,使他一寸一寸地嘆息著放棄他曾一度認為是屬於自己的地盤。他承認自己不能隨心所欲地支配的事物,一開始可能是風,後來可能是雨、是陽光、是雷電;而當他一點點地失去對大自然的控制,直到最後好像從一個王國即將縮小成為一個監獄之時,人必然會愈來愈深刻地感覺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和那些雖看不見卻存在著的巨大威力,並相信自己是被他們包圍著。因此,宗教從一開始僅是對超人力量的少許、部分的承認,隨著知識的增長而加探為承認人完全地、絕對地依賴於神靈。他舊有的自由自在的風度變為一種對那看不見的,不可思議的神的極其卑下的臣服態度,而他的最高道德準則就是對神靈意志的屈從。「我們的平安都在它們的意志之中」,但是,這種更深的宗教觀念,這種凡事以神的意志是從的皈依,只能對那些有較高知識的人起作用,他們具有足以理解宇宙之浩瀚和人之渺小的寬廣視野。渺小的心靈不可能掌握偉大的思想,以他們那種狹隘的理解力和近視的眼光看來,除了他們自己之外似乎沒有任何東西是真正重要的和偉大的了。具有這樣思想的人完全難以上升到接受宗教的高度。實在說他們只是在其宗教長輩的教海下表面上遵從教義,口頭上承認教條,但在內心卻仍然固守他們那古老的巫術迷信。這種迷信可能表面上不被讚許乃至被禁止,卻並不能被宗教所根除。因為它的根子已經深深扎在人類絕大多數的心中了。
讀者可能要提出如下問題:為什麼有智慧的人們竟沒能更早地識破巫術的謬誤呢?他們怎麼會繼續對那些根本無望之事懷抱希望呢?他們出於什麼心理要堅持表演那些毫無效果的古老的滑稽動作和叨念那些不起任何作用的莊嚴的胡言亂語呢?他們為什麼對那些跟自己的經驗有著如此明顯矛盾的信念戀戀不捨呢?怎麼會如此地勇於重蹈覆轍呢?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應當是這樣的:巫術的謬誤並不容易識破,它的失敗也不明顯。這是因為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隨著某種巫術儀式的完成,它想要產生的結果多半會在隔了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之後真的產生出來。要想在這種情況下仍能察覺到這些結果之產生並非由於巫術,這需要比一般人具有更為敏銳的頭腦才行。在舉行一次或為呼風喚雨或欲置敵人於死地的巫術儀式之後,或遲或早,經常會隨之出現它所希望產生的結果。這就可以理解原始人為什麼將這些事變視為儀式的直接後果和對它的效力的最好證明。與此類似,那些在早上呼喚日出和在春天喚醒冬眠大地的儀式,將肯定獲得成功,至少在溫帶地區是如此。因為在這些地區,太陽總是每天早晨在東方點燃它的金色的明燈,春天的大地總是年復一年地在春回大地之時將她自己重新用綠色的罩衫打扮起來。因此講求實際的野蠻人,出於他保守的天性,就絕不會去理睬理論上的懷疑者,和過激的哲學家的「詭辯」了。後者竟然敢於暗示日出和春歸併不是每日每年準時舉行的巫術的直接的結果,敢於暗示即使這種儀式偶然中斷或是完全停止舉行,太陽也仍可能繼續上升,樹木也仍可能繼續開花結果。這些懷疑論者的疑惑將很自然地被聽者懷著義憤和譴責加以拒絕,因為這些懷疑以虛妄的幻想破壞了他的信仰,並明顯地和他的經驗相衝突。他可能說:「我在地上點著了那值兩個便士的蠟燭,然後太陽就會在天上點亮他那偉大的火光。還有比這更明白的事么?我倒想知道:在我春天穿上綠袍的時候而樹木卻能不這樣做!這些是每個人都明白無誤的事實,我的立場正是建立在這些事實之上。我是一個宜率的講求實際的人,而不是像你們這樣的理論家、吹毛求疵的人和詭辯家。理論和思考以及所有這類的事,就其本身而論也許並不壞。對於你們這樣耽迷於其中,我也沒有絲毫的反對,倘若你們並不將其見諸行動的話。你們不要干擾我,讓我忠於事實,遲早我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這種論調的錯誤對於我們來說是很明顯的,因為他所討論的事實的荒謬性在我們說來早已是毫無疑義的了。但假如類似這樣的辯詞是涉及正處於討論階段的問題,那就可以問一問,英國的聽眾能不認為這是鑿鑿有理的辯詞而為它鼓掌嗎?能不認為這位辯論家是個精明細心的人嗎?他雖不是才華橫海、追求炫人的效果,但卻絕對地通情達理和講求實際。如果上述那些論點在當今社會尚且可以認為是合於情理,那又何須為原始人長期不能察覺這種錯誤而感到驚奇呢?
〇本文節選自j.g.弗雷澤的《金枝》,汪培基、徐育新、張澤石譯,第四章「巫術和宗教的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為閱讀及排版便利,本文刪去了部分注釋與參考文獻,敬請有需要的讀者參考原文。
〇封面圖《金枝》是約瑟夫·莫羅·威廉·特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年)於1834年展出的作品。這是一幅用油彩繪製在畫布上的作品。這個主題來自於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來到庫麥,諮詢一個先知女祭司西比爾。她告訴他,只有在他從一棵神聖的樹上割下一枚金枝並向普蘇佩尼獻上時,他才能進入冥界與他的父親的魂相見。特納展示了西比爾手持鐮刀和新鮮切下的金枝,面前是阿菲諾斯湖,傳說中通往冥界的入口。[圖源:google.com]
〇編輯 / 排版:及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