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關注

南昌,是一座有著悠久歷史的江南古城,又是一座有著光榮革命鬥爭傳統的英雄城市。對於這一地區先秦社會經濟狀況,有關歷史文獻里僅是廖廖數語,甚至一字不提;對於漢以後南昌城的變遷與發展,文獻記載中也不甚詳備,在一些地方志書,鄉人文集中雖有一些言及,又苦於零亂、分散。為了理出南昌古城的變遷與發展脈絡,給今天我們制訂南昌城的總體發展規劃提供一些歷史資料,本文擬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依據有關文獻,再結合一些新的考古資料,對古代南昌城的變遷與發展歷史作一簡略的概述。
(一)「襟江帶湖」的地理形勢
南昌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形勢險要。地當大江南北和上、下游的交叉點上,負江依湖,南臨五嶺,北接宣揚,西控荊楚,東翼閩越。南朝雷次宗描述予章的地理形勢說:「予章水陸四通,山川特秀,咽扼荊淮,翼蔽吳越。」唐代的王勃更以他超眾的才華、驚人的詞藻高度概括予章的形勝:「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滕王閣序》)
的確,南昌踞贛江下游,處江湖之間,平原綿衍,贛汝交流,在我國東南各省中,可稱為一中心城市,正因為它有如此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所以歷來為兵家必爭之戰略要地。
(二)最早的原始居民點
根據解放以後的考古發現,在東郊的齊城岡,南郊的青雲譜和西郊的西山等地先後發現有新石器時代遺址,如果把南昌、新建甚至豐城、進賢境內的遺址算進去的話,就有數十處之多。這些遺址,就是古代的原始居民點。眾多的原始居民點的建立,對此後南昌城的創建和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目前可以準確指出的南昌最早居民點是齊城岡和青雲譜磚瓦窯廠附近兩處。齊城岡遺址有著較厚的文化堆積,經過科學的發掘,出土了大批石 、石斧、石箭頭和紡輪等生產工具,以及鼎、罐、豆、壺等陶質生活用器,年代距今約五千年。遠古的南昌,水網密布,荊棘叢生,四周還有原始森林,無數的毒蛇猛獸常常出沒其間,而我們這些勇敢的先民們,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與天斗、與地斗,與洪水猛獸斗,極其艱苦地開拓出這塊富饒美麗的土地,充分顯示出人是戰勝大自然的決定因素。
、石斧、石箭頭和紡輪等生產工具,以及鼎、罐、豆、壺等陶質生活用器,年代距今約五千年。遠古的南昌,水網密布,荊棘叢生,四周還有原始森林,無數的毒蛇猛獸常常出沒其間,而我們這些勇敢的先民們,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與天斗、與地斗,與洪水猛獸斗,極其艱苦地開拓出這塊富饒美麗的土地,充分顯示出人是戰勝大自然的決定因素。
據齊城岡遺址出土含有稻草桿痕迹的草拌泥觀察,當時南昌的古代居民和江南其它一些地區的原始居民一樣,也已能人工栽培水稻。農業的發展,給人類提供了穩定而豐富的衣食來源,改善了生活,從而為當時原始居民點的形成創造了物質基礎。
石箭頭和網墜的出土,說明他們還用弓箭和魚網來獵取野獸和捕捉魚蝦。從當時生產力的水平和社會組織的情況分析,他們大體還處在母系氏族社會晚期或向父系氏族過渡的時期。
(三)「揚州之域」與「南楚之地」
商周時期的南昌,古代文獻記載極為貧乏,只簡單面籠統地彌為「揚州之域」。在舊史家的筆下,南昌猶如江南其它地區一樣,被描繪成愚味、落後的「荒蠻腹地」。然而,歷史的真實果真如此嗎?近年來,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的發現終於解開了這一「歷史之謎」。
根據考古工作者的初步調查,南昌地區先後發現類似吳城的商周時代遺址達二十餘處,諸如齊城岡、青雲譜、蓮塘斗門山、小蘭瀝山、生米、長頭嶺以及艾溪湖畔周圍的一些台地上也有零星商周文化遺物的出土。這就表明,三千多年前,今日南昌市區周圍,特別是從東北郊艾溪湖延續到南郊青雲譜的這一弧形地帶,古代居民的分布是較密集的。
根據這些遺址出土的文物,我們初步可以勾畫出商周時代南昌地區古代居民社會生活的大體輪廓。
儘管目前尚未發現奴隸殉葬墓,但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青銅兵器的製造等諸方面考察,南昌地區至少在三千年前已由原始社會跨進了階級社會的門檻。
前人論述春秋戰國時的南昌形勢,有所謂「吳頭楚尾」之稱。在具體歸屬上,眾說紛雲。
《史記·貨殖傳》:「江南予章,長沙,此南楚也。」
《通典》:「洪州,春秋戰國時並屬楚。」
《史記·正義》:「江南,指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
《文獻通考》:「洪州、江州,春秋屬楚。」這說明,漢唐以來的多數學者,都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南昌歸屬於楚。但是,也有的學者認為是屬吳地。如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洪州,春秋時吳地,戰國屬楚」。正由於古代學者的考證不一,故後來編纂地方志書時則各有從違,清康熙《南昌府志》稱:「先屬吳,次屬越,後屬楚。」到乾隆五十四年重修《南昌府志》時又采唐杜佑《通典》之說。
實際上,從當時吳、楚、越相互兼并的全部歷史考察,吳、越勢力抵及南昌的時間很短,整個春秋、戰國五百五十年間,南昌基本上都是楚的東境。司馬遷、杜佑的論述是正確的。正由於南昌長期屬楚,因而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更多的表現出與楚相一致的特點。近年在新建昌邑發掘的戰國中期墓葬,出土有銅戈、銅矛、銅劍等遺物,特別是陶器中如鼎、敦、壺的組合形式,更明顯具有楚文化作風。
解放以來,在小蘭、羅家集、長頭嶺、西山和梅嶺等地都先後出土過東周時期的銅鼎(炊器)、銅餑子(軍樂器)以及大量的銅工具,兵器等,這些青銅器,烏黑髮亮,鑄作精工,反映這時的青銅鑄作技術在商周以來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提高和發展。
春秋,戰國之際,是我國社會制度發生大變革時期。從新建大塘赤岸山戰國遺址中出土有鐵斧范(模子)來看,南昌地區開始使用鐵的時間應該不晚於戰國。由於鐵農具的出現,整個社會生產力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從而社會的階級關係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奴隸制的生產關係逐漸向封建制過渡。
(四)最早的予章城—灌嬰城
南昌究競從什麼時候開始形成為一個城市?商周以來,南昌地區就有著較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已逐步進入階級社會,但至今還沒有證據說明那時已建立起城市。
據有關文獻記載,南昌城的創建,當和漢高帝劉邦立予章郡有密切關係(《漢書·地理志》)。一般認為,在漢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當大將灌嬰率軍平「定吳、予章、會稽郡」(《漢書》卷九十五,《灌嬰傳》)之後,即開始在南昌地區築域,俗稱灌嬰城或灌城。郾道元《水經注》雲「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為予章郡治,此即灌嬰所築也。」這樣,最早的予章城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八十多年的歷史了。從那時起,南昌就一直是本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然而,兩千多年前的灌域卻不在今天的市區,而在城東南,大約東起順化門外十五華里的隍城橋(黃城橋),西至順化門外的興福庄,延袤數里,也即距今南站東南約四公里的黃城寺一帶地方。解放初屬黃城鄉,後屬肖坊鄉,現屬湖坊公社範圍。
據說,為了營建灌域,灌嬰委任本地一個叫章文的人具體總管建城亭宜。
灌嬰城的四周,有高大的夯築土城牆,周圍計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門:南有南門和松陽門:西有皋門和昌門;東北二門則以方偶為名。當時的予章城內外,盛產樟樹。松陽門內有大樟樹,高達十七丈,大四十五圍,「枝葉扶疏,庇陰數畝」(《太平寰宇記》引《予章記》語)故此,歷來不少著家認為,予章當以此樹得名,如應劭《漢官儀》云:「予章樟樹生庭中,故以名郡。」酈道元《水經注》和陳弘緒《江城名跡記》都同意其說:實則不然,當以「予章水」得名為是。《後漢郡國志》云:「贛有予章水」,雷次宗《予章記》中說得更清楚:「似因以水為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
自西漢初年創造予章城之後,歷東漢、三國和西晉五百餘年,也曾不斷地對予章城進行過整治和擴建,如:三國吳五鳳二年(公元254年)予章太守張俊就在郡城東南興建兩座圓樓,高四丈佘(《興地記》),是當時南方較有名的高台建築,所謂「予章之闕高,則長沙虎食人」指的就是這一樓圓建築。但是,在這五百年間,南昌城的規模基本仍是漢初灌嬰城的範圍。《太平寰宇記》引《予章記》云:「先是樟樹(指松陽門內的大樟樹——筆者按)並枯,水嘉中,一旦華茂,晉以為中興之祥」這雖然講的是城南的樟樹,但也說明,西晉末年即晉懷帝司馬熾時,南昌城依然在漢時的灌嬰城,並不曾往西移。
漢時灌嬰城之西北,即今日南昌主要市區,當時應是一片沼澤水網地帶,其中有一較大的湖泊,名叫太湖(今天家湖的前身)。湖的四周地勢稍高,間有山阜和丘陵,零星分布著一些村舍,一九七三年在墩子塘發現了一口西晉時期的民用水井就是有力的證據。井呈圓形,內徑六十四厘米。
井近底層還保留有用網錢紋磚築砌的井壁。井內出土有西晉時候的銅盆和青瓷罐、壺、缽以及勾桶打水的鹿角,這些都應當是當時居民取水時遺落下去的。在村落周圍的一些山阜台地上,漢、西晉時期也曾是基葬區,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先後在老福山、丁公路、永和門外發掘有西漢墓葬;在墩子塘、都司前、京山、七星街、新溪橋、繩金塔、徐家坊、青雲譜等地距地表五、六米以下發掘有東漢、三國和西晉時期的基葬。
漢、晉時的太湖、南緣回折,與位於灌城西南的南塘相連而接予章江,因而江漲則湖漲,江退湖水也退。東漢永元年間(公元89~105年),予章太守張躬組織群眾築堤修塘,籍以捍江,人們稱為南塘水,這是有史可查的疏竣開發東湖的最早一次水利工程。
自予章建城以來,贛江里行船如梭,繁忙異常。面位於郡城西南濱江的南浦亭(在後來的橋步門外),就是當時的泊舟之所(猶如今天的碼頭),凡南來北往的人,都在此靠岸上船。之所以稱「南浦」,乃取《九歌·河伯》「子交手奪東行,送前人奪南浦」意。當時詩文中多以此來泛指送別之地,如南朝梁時文學家江淹在《別賦》中寫道:「春草獸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這一時期,郡、縣以下的行政組織有鄉和里。
漢晉以來,予章地區有五大姓:熊、羅、雷、諶、章(《太太寰宇記》)。一九七三年在老福山上窯灣發掘一座西晉予章地主豪強的墓,根據墓內出土的一方銅印,得知基主就是姓諶。墓內出土有三十餘件鍋、鐵、玉、石、漆器和金銀器皿,反映了地主階級的奢侈豪華,同時,也足以證明這時期南方封建經濟的發展。
(五)東晉予章城的變遷
予章城何時從灌城遷至今日南昌市區?地方志書中多記載道:「(唐)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自灌城移置東湖太乙觀西」但根據是什麼?不得而知,其它一些地方史籍,或主前說,或語焉不詳。一九八〇年,我們在編寫《南昌史話》時,也曾沿用舊說,黃長椿先生經過一番精深的考證,提出了今日南昌城「始建於晉代」說,認為「這新城在東湖以西,南塘以北,贛江以東」。此說很給人以啟發,儘管目前尚不能達加定論,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和研究,但細審有關古代文獻,並參照一些考古材料,我認為黃先生的說法是可信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在東晉,而非在西晉。至於郡城西遷後,舊灌城是否仍是南昌縣治?南昌縣署是唐貞觀年間還是更早什麼時間遷往新城?這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今南昌城始建於東晉時代的理由,從文獻來看,東晉末劉宋初南昌人雷次宗在《予章記》中說:「州城東有大湖,北與城齊,隨城回曲至南塘。」這裡說州城系指江州之州城,因西晉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如「割揚州之予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水之名而置江州。」江州治所就設在予章郡。東晉初,即元帝時(公元317~323年),江州曾一度移治武昌,但不久又遷回予章,至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又由予章「移治潯陽。庾翼又治予章,尋還潯陽」。新設的江州統管十郡,其州治雖幾經搬遷,但主要仍在予章郡,因此西晉後期到東晉一代,南昌城既是予章郡城,又是江州州城。「州城東有大湖」,說明城是在大湖之西,而非是大湖以西的灌嬰舊城。北魏都道元《水經注·贛水條》中云:「贛水又北遙南昌縣故城西。」漢高祖六年灌嬰築子章郡城時,同時在予章城設南昌縣署。酈道元既然稱灌嬰城為故城,則當時必有新城無疑。部道元在《水經注·贛水條》還說:「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回折至南塘。」這與雷次宗所說完全雷同。
此外,我們還可提供兩個佐證:
第一,漢末,佛教在我國開始逐漸傳播開來,到了魏晉特別是東晉時期,由於佛款徒迎合了當時統治者中流行的玄學和清談之風,佛教逐漸中國化,佛教成了王公貴族和世家地主的共同信仰,因面各地佛寺建築一時猛增,地處江南的予章古城也不例外。據現在有據可查的,予章城星外從西晉到南朝先後興建的宮寺院觀建築達十座,而東晉一代百多年間興建的就有六座之多,諸如大安寺、禪居寺、琉璃寺、建德觀、紫極宮、觀音寺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建築的始建位置,都是在今日南昌市區之範圍,如禪居寺,為東晉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武昌太守熊鳴鵠舍宅而建,後改名為普賢寺,唐中宗時改為隆興寺,地址在惠民門內:又琉璃寺,「東晉元帝即位之歲,郡人有耕於東湖之艮隅者,獲琉璃像焉,其高三尺,其狀殊異,守臣上啟,詔之寺以處之。」後屢經興廢,唐曾改名延慶寺,一直延至清代,地址就在順化門內。此外,紫極宮在惠民門外大安寺(曾名東寺、宣明寺、普濟寺)和建德觀也都在城區。既然,東晉的寺院建築多建在大湖周圍地區,顯然,那時的予章城已移至大湖以西,如果,那時的郡城或州郡仍在灌城,則上述寺院道觀建築的布局就不好理解了。
第二,解放以後,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曾配合人防工程,先後在老福山,繩金塔、都司前、墩子塘、永和門外等地清理和發掘了數十座西漢——東晉時期墓葬,其中大部分都屬於西漢、東漢、三國和西晉時期的,目前確認為是屬東晉時期的墓葬,只有京家山(今罐頭啤酒廠內)的一座,且在昔日予章郡城之外。當然,這些墓葬都屬偶然情況下被發現,所反映的資料很不全面,但已被清理的這些墓葬的分布情況,也多少為我們探討予章古城的變遷提供一些線索。
東晉以後,隨著大江流域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予章城也日趨擴展和繁榮。
特別是由於郡城的遷建,更靠近予章江,過去位於灌城外西北方向的大湖,現在也已位於新城之東,而且緊鄰新城,這樣既有利於「憑江守險」,又可以「阻江為城」「蓄湖為池」。正因如此,東晉以後更加重視對濱江和大湖地帶的整治,南朝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予章太守蔡廓就曾發動群眾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改造治理工程,其項目除加築堤牆,在大塘之處更挖小塘外,主要是在南塘與予章江相接處置水門(水閘),江水漲時關上水門,內湖水多時則開門排泄。自此之後,大湖水患大為減少,而且經過整治後的大湖,「水清至潔,而眾鱗肥美」(《興地紀勝》引《予章記》語)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則稱之:「水至清源,魚甚肥美」。成為當時南昌地區重要的天然水產場。
在予章城西北七里的濱江地帶,大江衝下來的淤沙,連亘五、六里,蜿延如龍形。所以稱龍沙或北沙,當年是予章城外最高處,舊俗是九九重陽登高的地方。《水經注》中記載著這樣一條史料:「昔有人於此沙得故塚,刻增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重沒於水,所謂筮短龜長也。」它雖然蒙上一層神異色彩,但材料本身,卻為我們探討予章江的河道變遷提供了極可貴的線索。
作者:彭適凡
來源:南昌市城市總體規劃-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彙編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吳雪菲
校對:計夢菲
審定:羅舒平
責編:吳雪菲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註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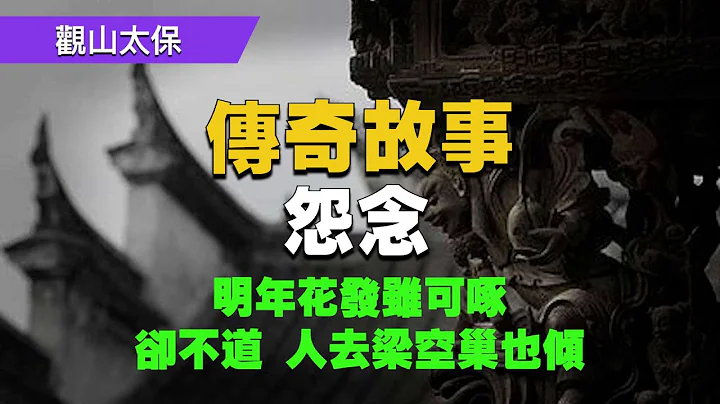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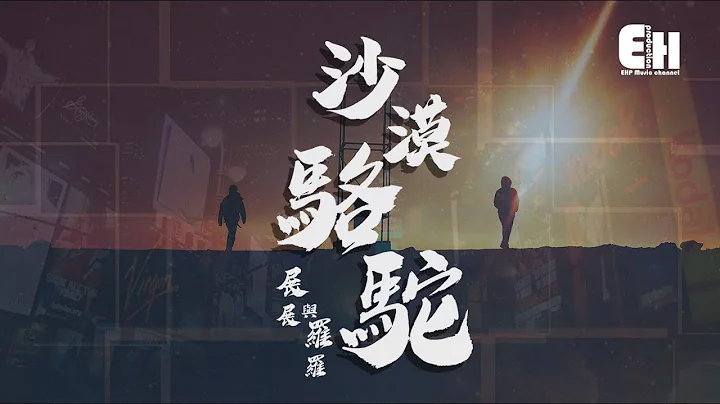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