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八年(1590)的夏天,京師大理寺突然收到了一份朝廷命官的血書。
告狀之人是時任四川永川(今重慶永川)知縣的張時照。在血書中,張時照一再聲稱自己的身家性命受到嚴重威脅,原因是他的直屬上司兼侄女婿、加封驃騎大將軍的播州宣慰使司都指揮使楊應龍寵妾滅妻,殺了妻子、岳母后,還想把張氏剩餘人等殺光屠盡。
明朝時期,為方便管理邊境少數民族,朝廷在各省級行政機構下設宣慰使司,由少數民族首領充任並世襲。盤踞播州的楊應龍,實際上就是土皇帝,只聽調不聽宣,對當地的軍民一應事情均有獨斷專行的權力。所以,大理寺官員一開始並不重視張時照的控訴。然而,越往下讀,狀紙的內容越觸目驚心。
除張時照外,狀紙中還有六七名小土司聯名控告楊應龍「閹割民人為太監」「奪占幼婦為綉女」「殺死長官,抄沒親叔」等種種惡行。
事關重大,大理寺官員立即趕出一份案情奏摺,呈遞御覽。
結果,等這份控狀放到萬曆皇帝的案前,他卻連看都懶得看一眼,只草草給了個批複,讓楊應龍收斂己行,好自為之!
張時照真的是欲哭無淚。為保住張氏家族的香火,他只能帶着剩餘的族人或走黔、或奔蜀,躲避楊應龍的追殺。

萬曆皇帝畫像。圖源:網絡
01
放眼偌大的明帝國,楊應龍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土司,但他及其背後的楊氏家族在播州的影響力實是不容小覷。
播州,即今天的貴州遵義。清道光《遵義府志》曰:「遵義,山國也,舉目四顧,類攢孴嶮巇,無三里平。偶平處,則澗壑縈紆,隨山曲直,名之不勝名也,書之不勝書也。」由於多山,遵義歷來發展落後、民風彪悍,時有「土酋叛」。

明朝播州地理位置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唐末,南詔王蒙酋龍僭越稱帝。為擴大勢力影響,他在位期間屢犯西南邊境,縱兵擄掠西川、安南、邕管、播州等地。彼時,播州雖地處邊陲,但名義上還是唐朝西川節度使的地盤。因此,即便唐朝深受「黃巢起義」的影響,危在旦夕,朝廷還是頂住壓力下詔征將收復失地。
而楊應龍的先祖楊端,本屬南廣溪洞僚人,因仰慕華夏漢人之風,遂自稱太原人,孤身往西南聯絡當地土著羅氏、謝氏,共同率領八部族眾徑入播州白錦堡,迫使酋龍部將羅閩納款結盟而退。至此,楊氏之名始在播州打響。唐朝方面為免西南戰事迭起,故在楊端凱旋時,賞其播州之地世襲,由此開啟了播州楊氏傳29世逾700年的土司家族歷史。
與同時期的其他土司有所不同,播州楊氏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最講究家族團結、緊靠中原。平日里,楊氏土司也不像其他土司那般蠻橫無理,而是注重域下教化,適時地為歷代中原王朝提供軍民人等物質保障。
即使是到了楊應龍當政的時候,這種家族傳統依舊深刻影響着播州與明朝的關係。楊應龍自承襲土司之職以來,「播州宣慰使司應襲楊應龍差楊羙等進馬二匹賀登極」「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備馬匹差官趙鳳鳴等赴京進貢及慶賀」「播州宣慰司楊應龍差長官楊正芳進馬匹慶賀萬壽聖節」等效忠明朝的記載屢見於《明神宗實錄》。
由於楊氏在播州統治的時間非常長,當地也流傳着不少關於楊氏土司的傳說。例如,今天的重慶綦江一帶,從古至今都傳說楊應龍乃隆慶皇帝的私生子,其力大無窮,能倒栽杉樹,經常腳蹬數百斤的靴子出門,儼然神人。

隆慶皇帝身體偏瘦弱,很難有楊應龍這般力大無窮的私生子。圖源:網絡
在這種情況下,張時照的血書傳到了京師,但朝廷想在楊應龍殺妻之事上對其治罪,難度相當大。更何況,張時照的血書雖有多人聯名舉報,但充其量也不過是下屬控告上司的一面之詞,並無第三方的說法,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無人知曉。
殺妻事件發生前,楊應龍不僅按時朝貢,還經常親自帶隊入山,為萬曆皇帝運送超規格的金絲楠木供紫禁城修繕。萬曆十六年(1588),楊應龍甚至出兵協助朝廷跨境平叛、犁庭掃穴,萬曆皇帝專程下旨讓有司為其打造一塊記功碑。自此,楊應龍更加威震西南,揚名天下。
眼下,若是輕易定楊應龍的罪,在萬曆皇帝看來,只會使西南動蕩,得不償失。
02
那麼,楊應龍殺妻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史書中保存着兩種說法。
據明代史書《兩朝平攘錄》記載,楊應龍本不喜歡正妻張氏,納田氏為妾後,對張氏的興趣就更寡淡了。因耐不住寂寞,張氏此後經常與人私通,給楊應龍「戴綠帽子」。某次,田氏恰好撞破張氏醜事,遂藉機告知楊應龍。楊應龍登時便想提刀殺了張氏及其姦夫,但被聞訊趕來的楊母阻攔。
楊母認為,張氏年紀尚輕,少數民族又有收繼婚的傳統,既然兒子不要她,那乾脆將她贈予族弟楊勝龍。楊應龍應允,可田氏卻不想輕易放過張氏。
碰巧,某日楊應龍醉酒來到田氏房中,見族弟楊勝龍也在。楊應龍懷疑二人有不倫之事,自己又被「綠」了,十分生氣,遂質問田氏為何與楊勝龍私會。結果,田氏故意揭楊應龍的傷疤,聲稱這是效仿張氏所為,並鼓動楊應龍去找張氏算賬。就這樣,正在氣頭上的楊應龍命人殺了張氏及其母官氏,引發張時照上京告狀。
而《明史》卻是另一種說法:楊應龍有三位夫人,其中,三夫人即是張時照控訴的「寵妾」,名叫田雌鳳,是播州地區白泥田氏土司的女兒。自從被楊應龍娶入門後,田氏就一直很受寵,但田氏平日里沒什麼愛好,就好「爭風吃醋」。張時照的侄女是楊應龍的大夫人張氏,出自江西龍虎山張天師家族。因家族聲望及娶進門的先後順序,張氏在家中可以行使主母的權力,田氏對此十分不滿。
仗着楊應龍的寵愛,田氏四處造謠張氏與楊應龍離心離德,不守婦道。某日,楊應龍醉酒歸家,聽到田氏又開始狀告張氏,一時氣急,提刀就沖入房中,將張氏殺死。其岳母聞訊趕到,想勸女婿收手,卻被楊應龍藉著酒勁一通亂砍,亦當場死於非命。酒醒後,楊應龍擔心張氏族人事後報復,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藉機屠戮張氏全族。
上述兩種說法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張氏有沒有過錯。考慮到《明史》在記載楊應龍殺妻時,援引的是曾巡撫四川、總督湖廣、四川、貴州三省軍務的李化龍的奏疏,其說法或許更接近於事實。但不管怎麼說,楊應龍殺妻,衝動而為應是事實。

屠「龍」名將李化龍。圖源:紀錄片截圖
張氏作為楊應龍的正室,擁有朝廷賜予的誥命。誥命夫人是君王冊封,殺了她就相當於藐視朝廷。可等六部會同大理寺對案件進行深入調查時卻發現,楊應龍殺妻案發生於萬曆十五年(1587)。如今,三年都過去了,張時照才出來喊冤,不免讓人覺得內有隱情。
更令六部堂官們頭疼的是,在西南地區的土司自治中,有條不成文的法律規定:「凡土官之於土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來,官常為主,民常為仆......土司虐使土民,非常法。所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與人也。」換句話說,在西南地區,土民乃土司的私有財產,土司可以隨意處置。楊應龍殺妻,若按這條規矩處理,朝廷也難以深究。
無論是從皇帝本人的意願,抑或當時朝廷與土司的關係來看,楊應龍殺妻案似乎都要不了了之了。
03
但在朝廷介入調查楊應龍殺妻案期間,隸屬播州的土同知羅時豐、播州長官何恩、千戶長官宋氏等土官聯名上疏朝廷,希望「改土歸流」,從而脫離楊應龍的掌控。
改土歸流,即由朝廷介入廢除西南各少數民族的土司制度,改派任期有限的朝廷命官代表中央鎮撫地方,進行直接統治。此舉的確有助於打破原有土司制度「蠻不出峒,漢不入境」的民族禁錮,但如果站在土司的角度,這顯然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為什麼要作出違背自身利益的選擇呢?
原來,自播州楊氏第24代土司楊輝在位時起,土司統治就出現了嚴重的內部矛盾。上京告狀的土同知、安撫使、長官司長官等,實際上都是播州地區「五司七姓」的首腦。
所謂「五司」,就是除播州外,受播州宣慰司管轄的黃平、草塘兩個安撫司,以及餘慶、白泥、重安等三個獨立的長官司。至於「七姓」,則是播州楊氏在治理轄下區域時,經常倚重的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大家族。他們與播州楊氏的關係,大致類似於中原春秋戰國時代的「卿族」,不僅在當地擁有「世為目把」、可以左右土司行政決策的能力,還與楊氏家族累世通婚,結秦晉之好。
楊輝與「五司七姓」的矛盾就出現在這裡。楊輝的大兒子叫楊友,由妾室田氏所生;嫡長子楊愛居次,生母乃正室袁氏。由於楊輝偏愛田氏,故希望打破「立嫡立長」的規矩,將播州土司之位傳給楊友,而楊輝手下的「五司七姓」土司們則更看重儒家「立嫡立長」的規則,堅持以楊愛為主。
按照慣例,楊氏土司需要將更換繼承人的意見在土司大會上提出,由「五司七姓」投票決定。楊輝的提議一上桌,其手下的各大安撫使、長官司長官們就敲桌子表達強烈不滿。草塘安撫使宋滔甚至認為,楊輝悖逆了楊氏家法,不忠不孝,遂聯合另外幾名長官司首腦宋淮、羅忠等提出更換土司,讓楊愛之子楊斌掌印理事。
這出鬧劇,以楊愛獲得朝廷任命為播州宣慰使,楊友被遷往保寧(今四川閬中)羈管而結束。但,楊輝怨氣難消,他借口支持「立嫡立長」的長官韓瑄「不順己意」,派人杖殺了他。由於這是播州楊氏內部之事,明朝並未擅加干預,但楊氏與「五司七姓」之間從此結下了梁子。
此外,播州楊氏因內部爭儲矛盾,導致與西南地區其他大土司之間的關係持續惡化。
在川貴的歷史上,播州楊氏與水西安氏都是舉足輕重的大土司。但兩個家族共治西南期間,卻齟齬不斷。嘉靖年間,楊斌之孫楊烈又與兄弟楊煦爭奪土司繼承權。跟自己的曾祖父楊輝類似,楊斌之子楊相也偏愛小妾所生的兒子楊煦,但鑒於曾祖父與「五司七姓」鬥爭失敗的教訓,楊相併沒有明着改立繼承人,而是通過疏離嫡妻的方式,降低楊烈及其生母張氏的影響力。

水西土司的「奇女子「奢香夫人。圖源:影視劇照
然而,楊烈的生母張氏頗有武則天之風,她私下與「五司七姓」的首領達成協議,讓他們支持楊烈發動政變,事成之後將以播州土地、特權等許之。在她的慫恿下,「五司七姓」公然背叛楊相,致使後者逃到水西土司境內請求避難,並最終客死在那裡。
楊相死後,楊烈曾向水西宣慰使安萬銓提出返還父親屍首,安萬銓趁機向楊烈要求返還被佔地盤。楊烈表面答應,得到父屍後立即反悔,並派兵殺死了前來接收的水西長官王黻,由此引發播州、水西十年戰爭。
可以說,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播州楊氏傳承二十餘代後,在利益面前,已經很難再像先祖那樣追隨大義了。
04
就在播州內部亂象迭起之時,明朝中央與播州楊氏的關係則更加微妙。
自明朝建立起,朝廷就一直想通過「改土歸流」來治理西南地區。彼時的貴州過於貧窮,自明初建省以來,那裡不僅錢荒、糧荒鬧得厲害,就連所轄地盤也不及今天貴州省的三分之一。而與之相反,本應歸屬於貴州省的播州宣慰司卻相當獨立,且經濟發達,史稱「播稱沃土,人人垂涎」。在明朝中央的默許下,包括播州楊氏在內,所有的西南土司均持有世襲田畝,一個個鉚足了勁兒,發展私有經濟。播州綏陽縣令母揚祖曾在述職報告里提及,稷、黍、豌豆、菱藕等作物在當地產量持續上升。可知,就農耕品種的多樣化而言,播州地區的水平絕對是黔北的佼佼者。如若將播州納入貴州省的統轄範圍,派朝廷命官去治理,豈不更有利於整個貴州的經濟平衡發展?
然而,由於明初天下初定,皇帝根本沒有太多精力鎮撫西南,「土司治土」依然是帝國必須倚靠的防衛力量。但這樣做,另一個弊端就是,不管楊氏還是其他土司,與中央王朝都不過是彼此利用的關係。
以楊應龍的先祖楊鏗為例,明朝平蜀次年,他就率部前來歸附,讓朱元璋在西南地區的聲勢得到極大增長。朱元璋龍顏大悅,詔「仍置播州宣慰使司,(楊)鏗、(羅)琛皆仍舊職」。可接下來,隨着雙方的關係變化,明朝中央對楊氏的提防之心日益加重。
據史料記載,洪武七年(1374),中書省曾奏明朱元璋,稱「播州土地既入版圖,當收其貢賦」,最好每年收二千五百石作為軍糧,以示其忠誠。朱元璋認為不妥,播州楊氏歸附有功,大明氣度恢弘,沒必要在錢糧上斤斤計較。不過,他實際上另有打算。待洪武十四年(1381)明軍征雲南,朱元璋突發一道詔令,聲稱楊鏗「有貳心」,讓他務必「率兵二萬、馬三千為先鋒」,以證明他的忠誠。

明太祖朱元璋畫像。圖源:網絡
對此,楊鏗只能應旨照做。而此後,播州楊氏為報此仇,等到成化、弘治年間明軍在西南地區的影響力稍弱之時,便開始慫恿地方時不時鬧些「匪患」,給明朝戍守西南的衛所增加工作壓力,衛所軍官也因此沒少被朝廷下旨申飭。
這種極限拉扯的關係,一直持續到楊應龍時代。
播州諸土司奏議楊應龍各項罪名後,支持「改土歸流」的貴州巡按陳效、巡撫葉夢熊又給楊應龍定了二十四條大罪,如殘害多命,縱慾欺惘,賄賂公行,禁錮文字,寇讎儒生,焚儒坑書等等,要求朝廷叛楊應龍死刑。而聞訊趕來維護本地利益的四川巡撫李化龍卻極力保護楊應龍。
李化龍認為,播州楊氏在西南聲望仍盛,楊應龍又未有明顯反相,加上四川三面鄰播,播州兵人多勢眾、驍勇善戰,朝廷這些年也沒少調他們出外征戰,當下,如果貿然對播州實施「改土歸流」政策,恐會逼反。
從表面上看,李化龍與葉夢熊之爭像是在為楊應龍作控辯,但兩者背後所透露的糾結卻是一樣的,那就是明朝中央始終無力在西南治理上找到一把稱心的「鑰匙」,更難以解決黔、川兩省發展不均衡的歷史難題。
05
既然朝議無果,萬曆皇帝只好讓黔、川兩省會勘,並召楊應龍對質,再商議如何處理這樁棘手的指控。
楊應龍十分清楚自己的公道和人心都在四川,所以接到命令的他,拒不赴貴州受審。萬曆二十年(1592),楊應龍到重慶受審,朝廷很快給出了一審判決:以嗜殺罪,判其斬刑。楊應龍提出交二萬兩贖金,請求寬恕。當時,日本的豐臣秀吉正打算吞併朝鮮,入侵明朝。楊應龍聞此消息,為了脫身,又在上訴材料中改口稱,自己可率播州5000兵出征,希望朝廷允許他戴罪立功。萬曆皇帝最終下詔同意了。
但是,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楊應龍剛返回播州,明朝就以「封貢」的形式招安豐臣秀吉。雙方短暫停戰,楊應龍也就錯過了贖罪的機會。
眼見事態變化,新任四川巡撫王繼光便想儘早了結此案。他讓官差到播州請楊應龍回重慶聽勘結案,結果差遣出去的人一個都沒回來——全被楊應龍殺害。

嗜殺的播州土司楊應龍。圖源:紀錄片截圖
王繼光三番五次要求楊應龍到案,結果均被播州方面回絕。無奈之下,他只好以楊應龍拒不出播聽勘為由,發兵攻打播州。
考慮到楊應龍已開罪川、黔二省,王繼光便派人去信貴州巡撫林道楠,提議四路用兵,讓林道楠務必遣一路黔兵助陣。但林道楠對此並不積極。
貴州方面的推諉,最終導致川軍在婁山關被楊應龍擊敗,王繼光因此遭革職查辦。
然而,王繼光的失敗倒是把楊應龍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朝廷主剿的聲音越來越高漲,連萬曆皇帝也說楊應龍這是「負固拒敵,罪無可恕」。楊應龍見事態越來越嚴重,當即命人從播州選出12名戰俘連同四萬兩贖罪金一併送到四川,同時第一時間上書朝廷稱:「何恩之訴,七姓之詞,皆屬於仇語,乞代罪立功!」
但這一次,朝廷不想再給楊應龍任何免罪的機會。
06
不得不說,楊應龍對時機的把握十分精準。他再次提出贖罪時,明廷第一次「抗倭援朝戰爭」剛剛結束,朝廷兵困財乏,根本無力通過戰爭降服播州。於是,在兵部侍郎邢玠的建議下,朝廷敲定了「用剿為撫」的策略,讓楊應龍戴罪松坎(今屬貴州遵義桐梓縣),送一子楊可棟到重慶為人質,另以其長子楊朝棟接管播州事務為土司,以期用最省事的方法解決播州爭端,平復西南局勢。
然而,「五司七姓」與楊氏的血仇由來已久。他們不希望楊應龍還活着。
以張時照為首的一群「五司七姓」首腦向朝廷上書,聲稱楊應龍及其族人才是製造西南混亂的罪魁禍首,朝廷要想順利實施「改土歸流」,唯一的辦法就是剿滅播州楊氏。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被楊應龍送到重慶的兒子楊可棟死了。儘管楊可棟被認定的死因是「病死」,但楊應龍始終認為兒子的突然死亡另有內情,並要求明廷歸還兒子的屍首安葬。重慶方面則要求他足額繳納四萬兩罰金後才能領屍。
楊應龍勃然大怒,對部下說:「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逢州打州,逢縣打縣,大做一番。」隨後,他率播州兵傾巢而出,流劫江津、南川及合江等地,「索其仇袁子升,縋城下,磔之」。之後,他又率另一支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曾狀告楊應龍的宋世臣、羅承恩等攜家眷藏匿在偏橋衛(今貴州施秉縣北部),楊應龍當即率兵「襲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女」。
可以看出,楊應龍一開始出兵只是為了報仇泄憤,但之後的幾場戰役則坐實了他「嗜殺」的罪名。萬曆二十七年(1599),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部三千剿播,楊應龍全殲都司楊國柱所部官兵之後,「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游擊張良賢戰死,綦江陷。應龍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為赤」。次年,楊應龍又率兵「焚龍泉,殺土官安民志。」
楊應龍的殘暴,終於讓萬曆皇帝下定決心剷除這顆「毒瘤」。
萬曆二十七年(1599)三月,抗倭援朝戰爭結束,萬曆皇帝立即下詔,讓力保楊應龍無罪的四川總督李化龍持尚方寶劍,調天下兵馬,會同抗倭名將麻貴、陳麟、李如松、劉綎等征播,平播之戰爆發。此戰後來被列入「萬曆三大征」,成為明朝鞏固華夏疆土、維護東亞主導地位的經典戰例。
楊應龍獲悉明軍興兵而來,已知無力抵抗。但,他做的錯事太多,無法回頭,只能硬着頭皮率諸苗兵與明軍決戰於海龍屯(今貴州遵義西北),希冀這座凝聚了楊氏先祖數百年心血的土司城堡能給予其最後的庇護。
萬曆二十八年(1600),在勇將劉綎的猛攻下,曾經成功抗金、抗蒙的海龍屯也守不住播州楊氏逾700年的潑天富貴。楊應龍見大勢已去,一把火點燃了帳幔,與愛妾一同自縊而亡。

生命最後時刻的楊應龍。圖源:紀錄片截圖
衝天的大火吞噬了海龍屯,也終結了楊氏割據播州的歷史。此後,播州被一分為二。明朝終於可以在此「設官兵,丈良田」,改土歸流。
自萬曆十五年(1587)楊應龍殺妻算起,這場由家庭命案作為導火索的央地爭鬥與戰爭,前後歷經14年,總算畫上了句號。然而,平播之役打到明朝國庫空虛,為日後李自成、張獻忠發動農民起義、推翻大明統治埋下了伏筆。這或許就是歷史的蝴蝶效應——你永遠不知道,帝國深處的哪一隻蝴蝶輕輕扇動翅膀,就將引起席捲整個天下的颶風暴雨。
參考文獻:
[明]張惟賢:《明神宗實錄》,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
[清]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
王興驥等:《播州土司民間傳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王興驥等:《海龍屯與播州土司綜合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顏丙震:《楊應龍議處紛爭與明代土司治理的缺失》,《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冉詩澤:《萬曆「播州之役」爆發原因再探——以「五司七姓」為中心進行考察》,《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王凌寒:《鐵血興亡錄》,紀錄片,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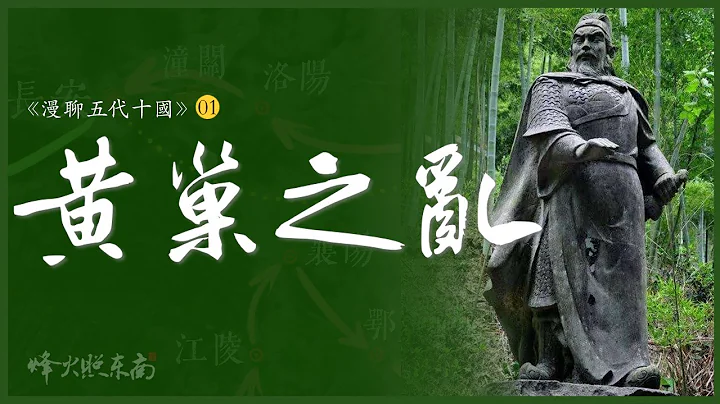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