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分為春秋與戰國兩個時期,而由春秋到戰國的分水嶺,是哪一歷史事件呢?
經過春秋時期長期的爭霸戰爭,東周許多小的諸侯國被大國并吞了。有的國家內部發生了變革,大權漸漸落在幾個大夫手裡。這些大夫原來也是奴隸主貴族,後來他們採用了封建的剝削方式,轉變為地主階級。有的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還用減輕賦稅的辦法,來籠絡人心,這樣,他們的勢力就越來越大了。
一向稱為中原霸主的晉國,到了春秋末期,國君的權力也衰落了,實權由韓、趙、魏、智、范、中行等六家大夫把持,另外還包括郤、欒等大家族。他們各有各的地盤和武裝,互相攻打侵奪。後來有范、中行兩家被打散了,還剩下智、趙、韓、魏四家。這四家,又以智家的勢力最大。
智家的大夫智伯瑤想侵佔其他三家的土地,對三家大夫趙襄子、魏桓子、韓康子說:「晉國本來是中原霸主,後來被吳、越奪去了霸主地位。為了使晉國強大起來,我主張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戶口來歸給公家。」
韓、趙、魏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瑤心懷鬼胎,想以公家的名義來壓迫他們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齊,韓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萬家戶口割讓給智家;魏桓子不願得罪智伯瑤,也把部分土地、戶口割讓給智家。

貪得無厭的智伯瑤又向趙襄子索要土地,不料碰了釘子,趙襄子拒絕說:「土地是祖輩留下來的產業,我怎麼會輕易送人。」
智伯瑤火冒三丈,馬上命令韓、魏兩家一起發兵攻打趙襄子。
公元前455年,智伯瑤自己率領中軍,韓家的軍隊為右路軍,魏家的軍隊為左路軍,三隊人馬氣勢洶洶地直奔趙家。
趙襄子自知寡不敵眾,就帶着趙家兵馬退守晉陽(今山西太原市)。
智伯瑤指揮的三家人馬已經把晉陽城圍困地水泄不通。趙襄子命令將士們固守城池,不許交戰。當三家兵士攻城的時候,城頭上箭似飛蝗般射下來,使三家人馬無法前進一步。
趙家軍隊在城裡死守了兩年多,智伯瑤指揮的三家兵馬始終沒有能把晉陽攻下來。
智伯瑤到晉陽城外察看地形,看到城東北的晉水,心生一計:晉水繞過晉陽城往下游流去,要是把晉水引到西南邊來,晉陽城不就淹了嗎?於是,他馬上吩咐兵士在晉水旁邊另外挖一條河,一直通到晉陽,又在上游築起壩,攔住上游的水。其時正逢雨季,壩上的水很快蓄滿了。智伯瑤命令兵士在壩上挖開了個豁口。這樣,大水就直衝晉陽,灌到城裡。
晉陽城裡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頂上去避難。然而,晉陽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瑤,寧可淹死,也不投降。
智伯瑤於是約韓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勢。他指着晉陽城忘乎所以地對那兩位說:「你們看,晉陽不是就快完了嗎?早先我還以為大水能像城牆一樣能攔住敵人,現在才知道大水也能滅掉一個國家呢!」
韓康子和魏桓子聞聽此言,大吃一驚,頭上冒出冷汗。原來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韓家的封邑平陽(今山西臨汾縣西南)旁邊各有一條河道。智伯瑤的話正好提醒了他們:晉水既能淹晉陽,說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陽也會被水灌。
晉陽被大水淹了之後,趙襄子非常着急,對他的門客張孟談說:「民心固然沒變,但要是水勢再漲起來,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張孟談說:「我看韓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讓給智伯瑤,心有不甘,我想去遊說他們攻打智伯瑤。」
當夜,趙襄子就派張孟談潛出城,先找到了韓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約他們反戈一擊,一起攻擊智伯瑤。韓、魏兩家開始還猶豫,經張孟談苦心說服,最終都同意了。
韓、魏倒戈,聯合趙家後,放水倒灌智家軍營,智伯瑤很快就全軍覆沒了,他自己也命喪黃泉。
趙、韓、魏三家擊滅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瑤侵佔兩家的土地收了回來,連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後來,三家又把晉國留下的其他土地也瓜分了。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韓、趙、魏三家派遣使者上洛邑去見周天子周威烈王,要求中央政府封他們三家為諸侯。糊塗的周威烈王竟然做起順水人情來,答應了三家的無理要求。打那以後,韓(都城在今河南禹縣,後遷至今河南新鄭)、趙(都城在今山西太原東南,後遷至今河北邯鄲)、魏(都城在今山西夏縣西北,後遷至今河南開封)都成為中原大國,加上秦、齊、楚、燕四個大國,「戰國七雄」開始登上了角逐攻伐的歷史舞台。

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編的著名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正是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作為寫作起點的。司馬光為何從這一年寫起呢?這是富含深意的。自言將《資治通鑒》通讀過「一十七遍」的毛主席,晚年在同身邊工作人員的談話中,道出了箇中玄機,他說:
「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說主要是司馬光認為發生了一件大事噢!
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選擇這一年這件事為《通鑒》的首篇,真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鑒》的書名完全切題。
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樑不正下樑歪嘛。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作上面的敢胡來,下面憑什麼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就「三家分晉」發表了長篇評論,似乎也在表明自己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發生的這件大事為開篇之原因。
司馬光認為,天子最大的責任是維護禮(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尊卑秩序以及由此產生的典禮儀式和根本的行為準則)的尊嚴。他強調,君臣之名分不可亂,禮就是用來定君臣之名分的。
司馬光認為,周雖衰落而不亡,原因是歷代周王尚知禮,而現在周威烈王承認「三家分晉」是對禮的破壞,是輕授人以利器,導引了天下人的奸貪之心。
司馬光在評論中沉痛地指出,周威烈王任命晉大夫趙襄子、魏桓子、韓康子為諸侯,是導致中央失去權威,以至引起天下混亂的根源。因為當時的東周王室是「天下共主」,雖然不是十分有實力,但是只有它才具有名義上的仲裁權。而魏氏、趙氏、韓氏做為晉國的臣子,聯手滅了晉國,把晉國一分為三,成了魏、趙、韓三國,這本身就是篡逆之舉,所謂「名不正,言不順」,極不合禮法。
但是,周威烈王卻封魏、趙、韓為諸侯,這無疑就肯定了他們的行為,使其大逆不道的行為合法化了。其直接後果是,其他的諸侯、大夫們一看,做臣下的奪了國君的權,不但不會受到懲罰,反而一下子從大夫成為諸侯了,這樣的好處誰不願意撈啊!於是,你窺視我,我窺視你,你提防我,我提防你,大家都不講道德仁義,只講實力和智謀,只考慮爭奪各種權力和利益,導致天下大亂。
因此,「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是一個轉捩點,此前是尚禮儀的春秋時期,此後則是尚智謀的戰國時期了。毛主席無疑是同意司馬光的觀點的,認為周威烈王無原則、無是非地首肯「三家分晉」合法化,是東周帝國衰落以至於滅亡的關鍵點,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這也是毛主席批評周威烈王「沒有原則,沒有是非」、「胡來」、「上樑不正」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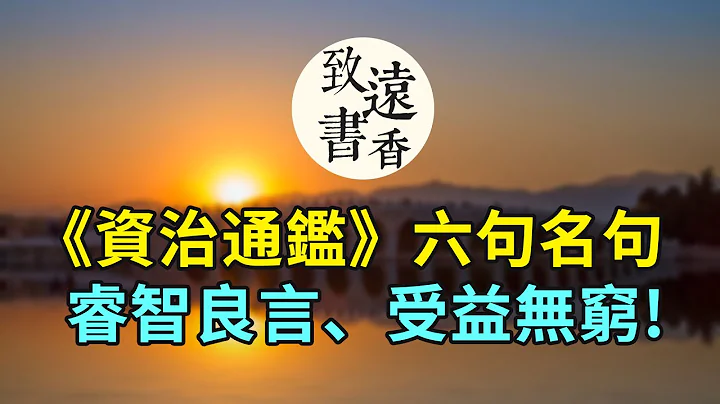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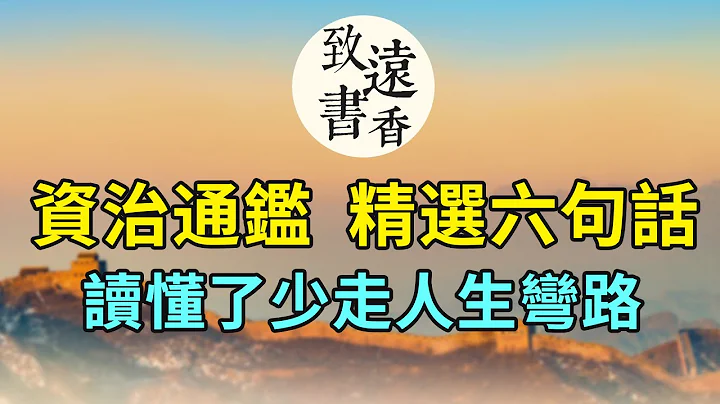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