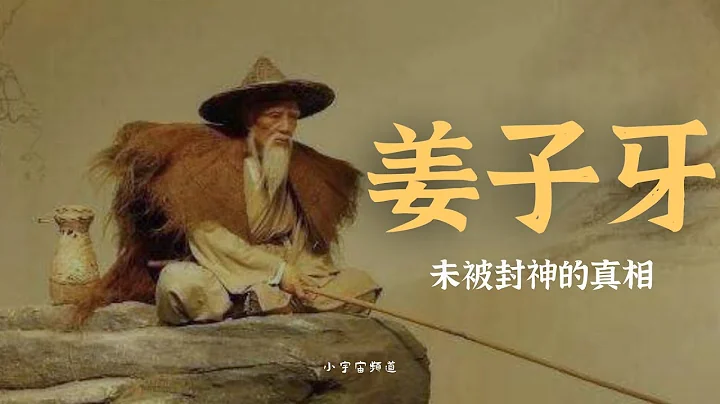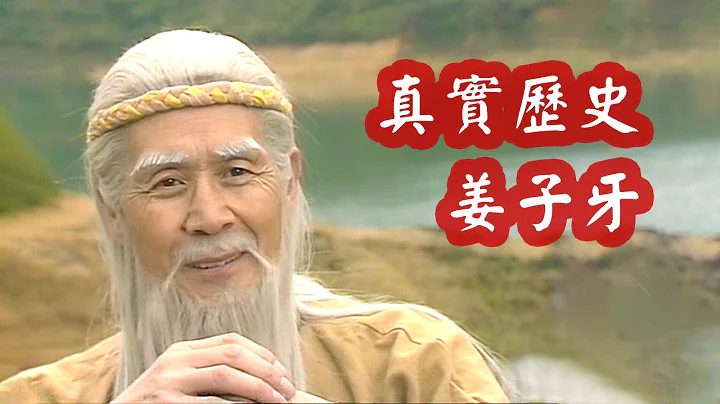西周初期的時候,生產力低資源少,基本就是各個部落不停地攻伐,各部族內也是年輕力壯的幹掉年老體弱的族長,周公搞禮制,能把人的身份利益關係確定下來,停止內部不斷的攻伐,天下能獲得平穩的發展,所以周公的方案獲得了各個部落族長的支持。等到春秋時期,生產力大發展,各種各樣的勢力有點能力搞生產的都能積累龐大的資源,養尊處優的宗室依靠落後的井田制,實力上已經不再具備優勢,別人自然也就不甘於身份的低微,這時候就是靠實力說話。

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都有小宗取代大宗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卻面臨著更爛更壞的問題,就是貴族實力膨脹完全壓過國君,這個就是三家分晉與田氏代齊的原因。就算這些貴族怎麼爭鬥,奪來的權利都與國君公室無關,國君也只能通過平衡貴族的權利來得以苟存。

但隨着實權的貴族越來越少已經無法通過平衡來苟存,晉國是最後三家誰也奈何不了誰就去相互交換土地,而齊國是最後勝家直接取代。這裏面最牛的還是秦國,商鞅變法前秦國國君是要權臣陪葬的,這個就是秦國幾百年來都沒有形成晉國那種能壓國君公族的貴族,無論春秋時期秦國怎麼弱也是把權力握在手裡,內部在怎麼亂也沒有其他貴族有機會架空。

田氏代齊是百年大計,是經過九代人努力才完成。由結果來看是田氏一開始的計劃,但人家落難跑過來的時候,前幾代還是恭恭敬敬一點謀反之心都沒有,更多是要求生存而已。而齊國宗室大亂,才給了別人機會覺得能取而代之,但這也是某一代開始行動。

齊國的故事就像一條大船,姜太公的後裔在東方開拓,在中原與東夷之間奠定了姜齊的性格,而時代的裂變也讓襄公、桓公等人站在了歷史的潮頭、開創了讓後來人不斷艷羨、美化的霸業。然而,姜齊的性格(或者說特色)讓齊國變得有多強大,最終也讓它變得多空虛。霸業成了代代齊軍背不動、忘不掉的包袱,公室和卿族在時代的洪流中搏殺。最悲劇的就是,姜齊和他的卿族們都成了田氏的墊腳石。

田氏代齊的成功可以說是集齊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就是當時的春秋時代,已然是禮樂崩壞,而當時天下又剛經歷三家分晉這一標誌事件,這就讓這些非正義的人有底氣互相聯合起來這麼干。地利,田氏在齊國經營了三百多年,足足是一個西周的壽命,齊國各個城池各個地方都了如指掌,別的大臣啥的也都跟他們沾親帶故休戚相關,行篡位之事自然輕而易舉。至於人和,眾多類似「小斗進大斗出」的收買人心的行為已經為他們積攢了足夠的人望,再加上連着大幾代家主都是有識有志之人,而不是只沉醉於做個權臣。這麼多優勢的聚集,讓他們不成功都難。

春秋時期君王大權旁落有個共同的特性,就是幼主即位,宗室和卿族爭奪權力,宗族成功就是換個君王,卿大夫成功就是世代權臣。比如晉國權力被卿大夫代替,就是晉襄公早逝形成的權力真空,齊景公也是,廢長立幼,結果幼子年齡太小又沒有勢力。一旦這個時候發生宮廷政變,君主就很容易失去權力。到了後世大一統的和平年代,有了體系,幼子即位影響不大,比如順治,萬曆,明堡宗,但是春秋戰國連年戰爭,一旦權力繼承出現問題,那必然大權旁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