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2年第8期P13—P14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原題《中國共產黨關於“中華民族”的百年論述及其話語發展》,摘自《貴州民族研究》2022年1期,周學軍摘


“中華民族”作為理解現代中國的基本概念和核心概念之一,雖然在嚴格的學理意義上是一個相當晚近的產物,但在文明淵源和文化傳承上卻連通着我們共同的歷史。從現實維度上看,“中華民族”不僅構成了中國現代國家的人群基礎,也是確認“國家”與“民族”雙向對應關係的關鍵環節。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具有高度歷史自覺和理論自覺的政黨,其關於“中華民族”的話語闡發與創新發展,來源於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形而上”提煉和對中國國情具體而微的觀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對於“中華民族”內涵和概念的界定與把握,直接關係到它所指向的目標與團結的對象。“五四”前後,“中華民族”觀念得到了廣泛傳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十月革命以及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的影響,這一時期民族主義的理論構建是民族自決,也就是要把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和奴役中解放出來,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自由。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逐步登上歷史舞台。作為理解中國社會和闡釋自身政治主張的關鍵一環,“中華民族”自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命題。針對中國如何得救、中國革命如何團結國民等問題,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均對“中華民族”這一論題傾注了大量心力,並展開了深入論述與探討。他們認為,中國人應激發一種以各民族融合為基礎的“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自覺,以實現中國的獨立和民族的復興。在國民大革命和第一次土地革命時期,伴隨着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的開展和對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動員,特別是在與各少數民族產生直接深入的接觸之後,中國共產黨對團結“中華民族”開展內外鬥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與感受。
抗日戰爭既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和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歷史節點,也是中國各界對於“中華民族”展開熱烈討論的又一高潮時期。在此階段,為了反擊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東亞民族主義”和“東亞協同體論”,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基本概念與內涵範疇等問題展開了較為系統的思考與論述,其間具有創見性的觀點和見解廣泛散佈於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文件政策及其領導人的著述講話之中。
除對“中華民族”的基本概念與內涵範疇展開系統論述之外,中國共產黨還對中華民族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的辯證關係進行了深刻分析。這不僅有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情境和中國土壤下的生根生長,而且也較為妥善地解決了中華民族利益與國際無產階級利益的潛在張力問題。
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
實現中華民族的完全統一,既是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銘記於心並為之不懈奮鬥的偉大歷史重任。在革命年代乃至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以及系統化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推進中華民族的團結與凝聚上厥功至偉,它不僅很好地承擔了思想引領和制度黏合的作用,而且也成功地將差異化的各族人群整合成為一個具有共同政治身份的“人民”,從而使中華民族在結構與人心的雙重意義上均得以被鑄牢和夯實。但具體到港澳台地區,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這裡涉及相異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如何相互兼容共處的問題。這就需從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和民族情感出發,通過各個地區對於共同性“中華民族”身份的深切體認,來統轄和超越彼此在制度體制上的具體分歧。由此,“中華民族”的意義和價值得以進一步彰顯:不僅中華民族自身的團結凝聚需要政治國家的引導與支持,政治國家的和平統一和領土主權完整同樣需要中華民族為之提供內在性的情感認同與道義支撐。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在這一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更加強調要發揮中華民族的內在凝聚力,通過對“中華民族”之歷史生成性與內在凝聚性的深入闡發,明確中華民族對於不同歷史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傳承和聯結作用,從而把中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與中國政治國家的統一性直接聯繫起來。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闡述中國多民族形成發展歷史、考察中國現實民族狀況以及分析中國民族關係與格局的重要理論成果,它“將學術界對‘中華民族’的闡述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另一方面,費孝通等老一輩學者們當年更多還是從民族學和人類學的視角出發,通過對中華各民族流動遷徙的民族史分析、不同區域和民族文化單元內在關聯性的論證,對中華民族內部的多層次結構及不同結構層次之間的“統一性”與“差異性”關係進行了整體性觀照。因此,它雖然能夠系統論證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是如何形成和維繫的,卻沒有言及其與中華現代國家的直接關聯。中國共產黨基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洞察力,敏銳地發現並回應了這一根本性問題。通過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強調和引申,使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相關話語直接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表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用以解釋中國國情、闡述政策方針以及處理民族事務的重要邏輯依據和理論支撐,它的指向不再只限定為文化層面,而是立體性的。由此,“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也就不僅僅呈現為一種學術話語,而是進一步上升成為黨和國家的政治話語。它與中國共產黨團結領導中華民族爭取自由獨立和建立發展社會主義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奮鬥進程,緊密結合成了一個整體性的歷史敘事和理論體系。
新時代以來
新時代以來,“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相關話語闡述中的地位和意義變得更為凸顯。在“中華民族”這一本體概念及其內涵屬性的闡發上,中國共產黨賦予了其更具縱深性的內在結構和更為廣闊的意義空間——中華民族共同體。
由強調“中華民族”,到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二者之間不僅僅是話語的轉變,而且深刻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對中國現實國情與歷史奮鬥使命的認識把握上,始終保持着實事求是的清醒頭腦和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在“中華民族”之後加上“共同體”,意味着與以往各個歷史時期相比,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要更加突出“中華民族”的“團結性”與“共同性”。而且,這種“團結性”“共同性”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又有所不同。當時主要是基於推進多民族國家統一的深層考慮,是將中華民族自外向內推向“團結”。新時代所強調的“團結性”與“共同性”,則是對中華民族內在精神性要素的確認,是由內而外的“團結”,這在程度和性質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同時,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上,還強調要在“意識”層面予以“鑄牢”。這意味着,新時代不僅要追求中華民族“團結性”與“共同性”的外化於行,還要將之內化於心,在人心和靈魂層面上鞏固下來。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終目的是把各民族群眾更好地團結起來,並在更深層次上凝聚為一體,從而建立社會主義國家與國民之間牢固緊密的雙向對應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充分調動中華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使之聚合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宏偉目標之下,勠力同心建設社會主義祖國。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在上升成為黨和國家的政治話語之後,其內涵意義在新時代得到了進一步挖掘與提煉。簡言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既是對於中華民族共性與個性、整體與部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系統調適和有機結合,也是能夠完整準確歸納中華民族性質與特點、真正在歷史與實踐邏輯上實現高度自洽的重要理論概念。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這一論述,也意味着在“中華民族”及其縱深性問題的理解和把握上,已經實現了形而上的“揚棄”過程和更為清晰透徹的理論自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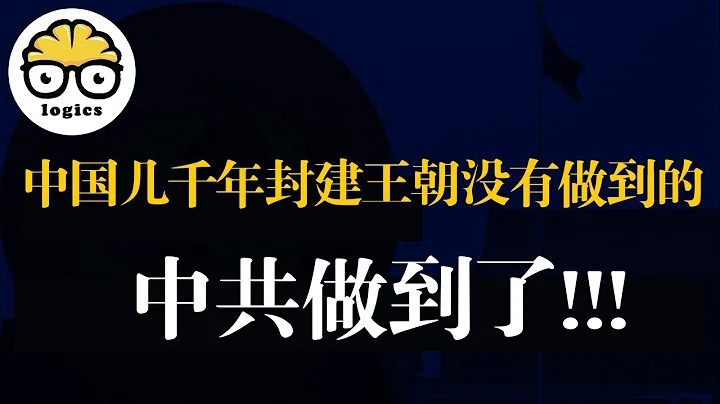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結】《我的女將軍大人》女將軍穿越意外嫁總裁,被心機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來了?總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寵#霸道總裁 - 天天要聞](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