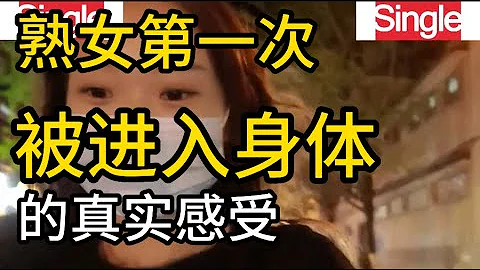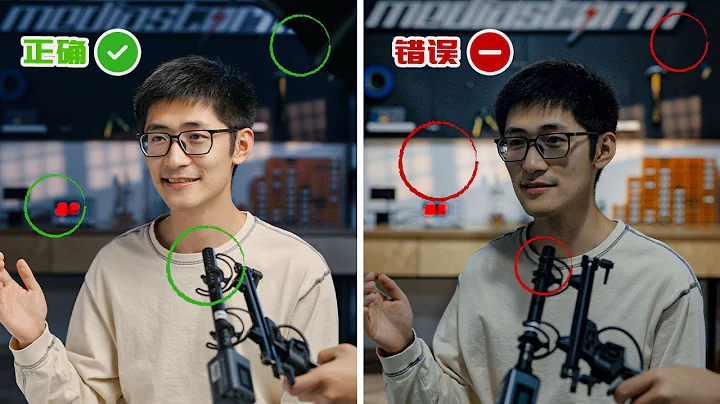⩥在閱讀此文之前,麻煩您點擊一下“關注”,既方便您進行討論和分享,又能給您帶來不一樣的參與感,感謝您的支持。

文|御史流芳
編輯|御史流芳
«——【·前言·】——»
世界範圍內紀錄片確立獨立地位是在20世紀20年代,格里爾遜提出了 “documentary”一詞。格里爾遜認為紀錄片具有像檔案、文獻一樣的功能,因而可以用來進行宣傳教育;其次,他強調紀錄片的根本任務是“對現實進行創造 性處理”。這就是說,紀錄片可以用於宣傳教育,但是不能突破紀實精神的底線。

此後20世紀50年代起“直接電影”“真理電影”“真實電影”等理念蓬勃發展, 紀錄片是“非虛構影片(non-fiction film)”的觀點被普遍接受。再到20世紀 90年代興起的“新紀錄電影(new documentary)”開始對於“非虛構影片”的否定,紀錄片經歷了“虛構——非虛構——再虛構”的完整回歸。

這個過程中一 直保持不變的則是紀錄片不依賴新聞和電影等其他任何影像類型的獨立性,這恰 恰是中國紀錄片發展存在的問題:電影方面新聞片與紀錄片分不清邊界,電視方 面專題片沿用電影新聞紀錄片的模式。尋找中國紀錄片獨立性,最根源是要將三 者界限廓清。
«——【·“新聞片”與“紀錄片”的分離·】——»
以建國後紀錄片發展為基準,從時間上梳理三者,可發現“新聞片”與“紀錄片”最初是混雜的。1953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成立統管新聞紀錄片的製作與發行。

基於技術的限制,兩者分屬一處管理,長此以往便造成了“新聞片”“紀錄片”“紀錄電影”等概念混雜不分的狀況。單萬里認為1976年後“新聞 片”與“紀錄片”逐漸分離,1但兩者分離的具體時間卻無從判斷,至90年代還出現了“中國特色”的“專題片”,而對於“專題片”概念也是不明確的。

根據1992年大連出版社出版的《新聞通訊員手冊》稱“新聞紀錄影片”是“運用電影手段進行新聞報道的一種大眾傳播工具,屬於新聞範疇,在表現手法上具有電影藝術的某些特徵”1,足以證明“新聞片”與“紀錄片”分離持續時間之久, 混沌迷離的情況甚至持續到九十年代。

既然冠以“紀錄”一詞,為何不將其歸入 紀錄片的範疇,如此看來,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分離的標準是什麼。紀錄片脫離電影獨立存在的地位,主要是劃清了“故事片”與“紀錄片”的 界限。

因此往往會將非“故事片”歸為“紀錄片”,以至於後期發展出的美國“新聞電影(journalisme filmé)”德國“論戰電影(un cinéma de combat)”等諸多類型都被冠以“紀錄片”的名號。這類影片製作時使用最新攝製的紀錄片鏡頭, 更多地是傳遞新聞事實,本質與格里爾遜認為的紀實性相符,將其歸為“紀錄片”是合理的,但是這也只能證明“新聞電影”可作為“紀錄片”的小眾分支。

20 世紀20年代攝影技術傳入中國不久,很多影片公司都是既拍故事片又拍新聞紀錄片,新聞紀錄片多用資料片編輯後演變為宣傳電影,但創作者大多隻管拍攝, 不探究理論,中國紀錄片本身就處於相對蒙昧的狀態。新中國成立後,主要與蘇 聯交流學習,大多西方的理論並未有效的傳播,長此以往便造成了“新聞片”與 “紀錄片”的混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經過紀錄片的獨立化就直接將“新 聞紀錄電影”意義擴大至“紀錄片”,“新聞電影”帶着“紀錄片”的畫皮偷偷 篡位。

此外,還有一個極為現實的原因,西方紀錄片相對獨立於政府,而中國紀錄 片對於體制有高度的依附,加之技術的局限,新影廠拍攝大量影像用以製作“新 聞片”,這也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務,而編輯和生產“紀錄片”的空間則沒有那麼 大。這種局面的改變主要從電視的普及開始,這意味着故事片有了更大的市場, 紀錄片也要開始轉型,“電視紀錄片”隆重出場。

只是電視剛開始普及,電視新 聞工作者可謂毫無經驗,很多電視新聞工作者過度依賴報紙、廣播等現有的新聞 資料,創作出來的作品勢必存在相似性,許多作品在成片上仍然屬於“新聞片”。 這時再看專門從事紀錄片創作的機構“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就可以清晰的認識到其中的“紀錄”一詞與“documentary”是不能劃等號的。

新影廠所說的“紀錄”大範圍指的是將發生的重大事件通過攝影技術保留為文獻,並不是將其進行“創造性處理”生成“documentary”,這樣就能理解八十年代初期所說的有關名詞諸如“新聞電影”“紀錄電影”“新聞片”“紀錄片”“新聞紀錄電影”等,只有“紀錄片”一詞與“documentary”最為接近,其中所謂的“彙編電影”應當是距離紀錄片最近的影片了,其他大多都應劃分至“新聞片”的範疇。

畢竟“新 聞片”與“紀錄片”兩者從職能上來講新聞片更重要的是傳播新聞事態,紀錄片 更多是“對客觀事物的記敘、描繪和評論”。
1976年後“新聞片”與“紀錄片”開始分離,電視普及只是一個開始,表現並不明顯,真正能明確“紀錄片”脫離“新聞片”是80年代文獻紀錄片的繁榮,這種基於文獻檔案整合的紀錄片才算真正認可了格里爾遜對於“documentary”的定義。

後期基於文獻紀錄片演變而來的政論片更是將“新聞 片”與“紀錄片”拉開了距離。20世紀20年代就獨立的“documentary”在中國 步履維艱,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開始了實踐與理論的統一。
«——【·“紀錄片”與“專題片”·】——»
20世紀90年代,新影廠併入中央電視台(1993),影視合流、內外接軌,此時產生了一個新的概念“專題片”,這一說法可謂是中國的“創造發明”。最終隨着國際交往的增多,“專題片”的說法開始淡出並逐步被“紀錄片”一詞取代。

但“紀錄片”與“專題片”到底有何區別卻沒有定論,2006年《文匯報》 報道《忠貞》時在3月9日與4月1日分別使用了“大型文獻專題片”與“大型文獻紀錄片”,這種情況屢見不鮮。當然,學界也曾對此作過討論,部分學者認 為對兩者進行區分和定義會束縛電視人的創作實踐,也有學者認為如果不將兩者區分,更不利於紀錄片理念持續發展。

因為兩個概念總是分不清,因此還出現了“紀錄專題片”以及“專題紀錄片”的說法。直到2011年張瑞林的《專題片與 紀錄片屬性再議》,2012年熊高的《視覺傳播下對電視專題片的再認識》等文章還在對這一爭論進行探討。實則如果理順改革開放前中國紀錄片發展流變,就 能明確“專題片”實際是從“新聞紀錄片”即“新聞片”發展而來的。

關於“專題片”與“紀錄片”的爭論由來已久,但無論討論多麼熱烈,都改 變不了“專題片”即具有“新聞片”特徵又具有“紀錄片”特徵的狀況。

隨着電視的普及,電視節目需求量增多,電視片逐步發展繁榮,1976年就已然出現了“電視專題片”這一名詞概念,而這一時期卻是“新聞片”與“紀錄片”尚未明 晰之時。表面看是“專題片”與“紀錄片”的鬥爭,實則是“新聞片”與“紀錄 片”的博弈。隨着“新聞片”與“紀錄片”逐步分離,“電視專題片”也在潛滋 暗長,當兩者明確分離時,專題片也羽翼豐滿。

反觀西方卻沒有“專題片”類似 的概念,如此“專題片”的出現便可歸因於中國紀錄片獨立性的缺失。如果說“新 聞片”與“紀錄片”的分離給與中國紀錄片完成獨立的喘息之機,那麼“專題片” 的出現則是將中國紀錄片獨立化攪得天翻地覆。
«——【·結語·】——»
直至2010年前後才有學者將專題片與紀錄片徹底區分開來,並將專題片劃歸至新聞片的範疇。之所以總是出現混沌,則是因為電視興起帶來了節目需求,創作者想要抓住受眾則需要不斷學習與創新,但是發展長期滯後的中國紀錄片, 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都很難在短時間將最新的理論與手法進行完整地消化,然而 拍攝手法和理念魚龍混雜,創作者們只管學不管分,學得太多太快勢必會造成創作上的積食,“專題片”被創造了出來,卻不知它是什麼。

因此,對於“紀錄片”與“專題片”不可通過一刀切來分類,如將90年代在國際獲獎的諸如《沙與海》的此類影片都算作專題片,那麼中國紀錄片的歷史必將一片蒼白。可以說新聞片 與紀錄片的分離,紀錄電影與電視紀錄片的分離,專題片的不斷增多都促使中國 紀錄電影藝術開始覺醒,這也是紀錄電影進行藝術探索的前提。
«——【·參考文獻·】——»
1.Judith N,Martin,Thomas K,Nakayama,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M]foreing language teavhing and resesrch press
2.[英]斯特拉·布魯茲,新紀錄:批評性導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3.[日]小川紳介著山根貞男編馮艷譯,收割電影: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M],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