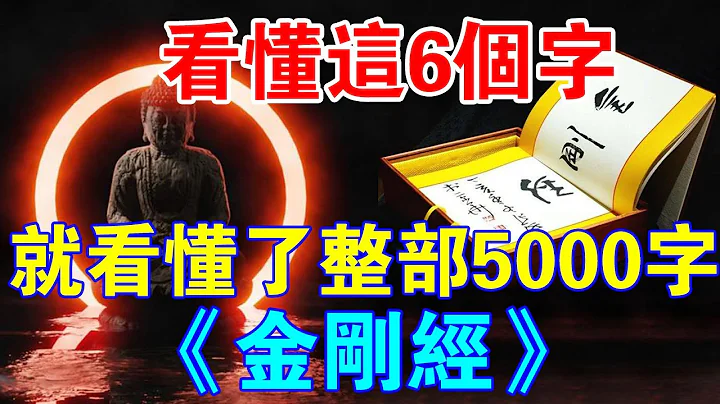據《楞嚴經》云:“何名為眾生世界?
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
我們所居住的國土便是由最小的“一世界”構成(一世界:以須彌山為中心,加上圍繞其四方之九山八海、四洲及日月,合為一單位),其上更有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一大千世界為一佛所化之土。
“世”與“界”,僅僅用兩個字,便含括了流動的時間與廣闊的空間,這集合了穩固與脆弱的矛盾體也在提醒人們——
我們所居住的國土,不但有東西南北上下的分界,而且是有生滅的,不是永恆存在的。

與廣大宏偉的世界相比,佛經對於極細微的、短暫的時間也有着自己的計量單位。
其以“一剎那”為時間的最小單位,而一個起心動念的瞬間便有“剎那”相續飛逝。
如《楞嚴經》云:“沉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
雖然在不同的經典中,“剎那”的計算標準各異,但其換算至今日,均為零點零幾秒,可見其短暫。

因緣是產生結果的一切原因,其中“因”是直接原因,“緣”是間接條件。
例如種子是“因”,泥土、雨露、空氣、陽光、肥料、農作是“緣”,由此種種因緣的結合才能讓種子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因此,影響結果的不光是“起點”,中間的過程一樣很重要。

佛經中對於無常有着諸多比喻,這些比喻無不瑰麗又脆弱。
常見有夢、幻、影(謂鏡中之影像)、陽炎(遠處地面炎熱導致光線像火焰一樣的跳動的現象);
響、水月、浮浪、虛空花(病眼昏花,於空中所見的種種花狀幻象)等等。

“覺”有覺察、覺悟兩層意思:覺察即察知惡事,覺悟即開悟智慧。
“佛”便是完全、徹底的“覺悟者”,既能自覺,又能覺他。

佛菩薩以塵世為苦海,恆發願以般若為船,救度眾生出離苦海。
如《大悲經》云:“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速乘般若船。”
又如《萬善同歸集》云:“駕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渡法界之飄溺。”

海潮聲勢雄壯,漲落有時,常用來比喻佛、菩薩應時對機說法的音聲,亦可比喻如海潮抑揚起伏的唱贊誦經之聲。
除了“海潮音”外,經典中還曾用“雲雷音”“獅子吼”等形容佛陀說法。

“遊戲”給人以鬆弛、自在之感。
在佛教中便以此顯示佛菩薩任運自如,能夠毫無障礙、隨心所欲地渡化眾生的能力。
在造像中,亦有一腿盤坐、一腿下垂的“遊戲坐”佛菩薩形象。

行者常指佛法修行者。
在學修的過程中,“行”是必不可少的一環,要求我們在信樂、了解佛法後,還要效彷彿菩薩的身語意,去修正自己的言行。
正如俗語所說“光說不練假把式”,如果只信解而不實行,在面對煩惱時仍然會隨順習氣,也就無法從中獲得實益。

“抖擻”為“頭陀”的異名,是僧人修持的一種苦行。
通過此種修持,而能斷除對飲食、衣服、住處等貪著煩惱,恢複本來面目,猶如振衣去塵,得返清凈。
如今常被用於鼓勵,意為振作、奮發等。

在佛教中,“塵”不光指塵土,還包括通過“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向外攀援所觸及的對象,即“色、聲、香、味、觸、法”。
這“六塵”會像塵土一樣覆蓋我們本來清凈的本性,引起許多迷妄與煩惱。
而通過日常的修持,即可“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也即“一塵不染”。

其是“前所未有”的近義詞,如《法華經》云:“我等今日,聞佛音教,歡喜踴躍,得未曾有。”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正宜勤加精進,莫負良緣。
結語
在上述詞彙之外,還有“讚歎、緣分、成就、懺悔”等等。
得益於大德們的深入理解及精妙翻譯,這些詞彙在保有教義的同時,也充滿了凝練深遠的中文之美。
而當這樣的詞彙串珠成鏈,那渾灝流轉的機鋒與睿智超妙的哲思,便匯聚為一首首佛偈、一部部經文,值得我們反覆持誦、細細揣摩。
來源:上海玉佛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