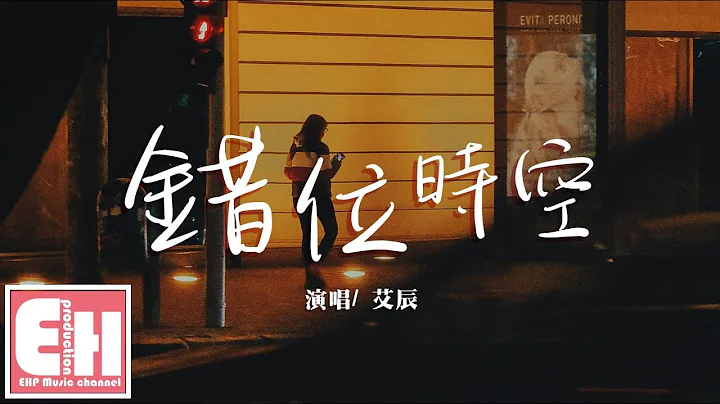2022年10月,应《报恩》所邀,摄影师王坚与杂志编辑人员热情分享了其在七塔寺拍摄多年的所见、所思、所感,以及作为一名资深摄影爱好者多年来对于摄影艺术的热爱、坚守与期许。
人物介绍
王坚,宁波鄞州人,别署“觉路七塔”。秉持“无它,唯手熟尔”理念,悉心创作,坚持以摄影的方式读懂一座寺院、一个城市。

叶伟 摄
从影介绍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接触摄影,师从洪柏春先生。90年代起开始摄影艺术创作,主要方向是风光题材,先后师从郭一清先生、李元先生。
2001年,获“柯达杯”《中国摄影》2001年度专业反转片优秀摄影师提名奖。
2001年,获第八届佳能杯“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人与自然类三等奖。
2002年,多幅作品入选《中国上海第六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2002年,获中国摄影家协会网首届“影友拼图”半月赛十佳作者奖。
2016年,个展“钱湖早安——王坚摄影作品展” 分别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宁波艺术中心、宁波市文化馆开展,此次展览共展出钱湖早安系列作品50余幅。与此同时,个人摄影作品集——《钱湖早安》在叶伟先生的悉心制作下完成,一段甬城东钱湖岁月变迁的影像记录史,由此诞生。
2016年,开始创作《觉路七塔》系列摄影作品,并为《报恩》杂志和七塔禅寺、栖心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微信公众平台提供图片。
2020年,“栖心梵影——王坚摄影作品展”在七塔禅寺栖心图书馆举办,此次展览精选了王坚在寺院拍摄创作的艺术佳品20余幅,吸引了广大甬城信众、读者及摄影爱好者观展。展览结束后,王坚将所有展品对外义卖,所得善款悉数赠与栖心图书馆。

“栖心梵影——王坚摄影作品展”部分展品
一、佛教题材摄影:七塔开觉路,光影传正道
《报恩》:您在网络上专门发布七塔寺相关摄影作品的账号名为“觉路七塔”,背后有何寓意?
王坚:2016年12月25日,在整理七塔寺相关摄影作品以备后续出影集相关事宜时,可祥法师定调取名为“觉路七塔”。2017年,我在今日头条号上分享七塔寺的摄影作品时,使用了这个名字。

可祥法师手书“觉路七塔”
李白《春日归山寄孟浩然》中有诗句云:“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佛法能开启众生觉悟的道路,超度众生脱离迷惑,到达理想的彼岸世界。我对“觉路七塔”的理解:“觉路”即觉悟之路,要依照佛陀教导的“四圣谛”“六度”“八正道”等正法来修持,才能像佛一样开大智慧,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塔”是佛的象征,所谓能如实觉知者为佛,“七塔”喻示过去七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为禅宗法脉源头表征,七塔禅寺之“七塔”即为此意。“觉路七塔”的寓意是大家要依照佛法来修行,将摄影艺术、读书作文等日常生活上升至修行的高度,最终目的都是要达到禅宗所言“明本心、见本性”,抵达觉悟之彼岸。
《报恩》:您使用账号“觉路七塔”发布摄影作品之前,是否通过网络分享过其他的作品?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开始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在七塔寺拍摄的图片?
王坚:我以前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钱湖早安”,主要发布的是我在东钱湖拍摄的一些风光摄影作品。“觉路七塔”的头条号现在有六千多的粉丝,这上面发布的基本上都是七塔寺的垂直内容,关注者主要是宁波本地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
选择在网络上发布七塔寺的作品,目的有三:一是把佛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来观察研究,希望通过发布一些在七塔寺拍摄的照片,来增进大众对于正统佛教文化的了解;二就是为了和更多人分享,有很多人一年到头难得亲自到寺院一趟,发布这些照片也能够与他们共享寺院一年四季的风景;三是为了让作品“试水”。对于那些我自己觉得有把握的照片,其实不发也可以,但那些介于“好”和“坏”之间的照片,自己把握不好,就会拿出来让大家评论。有时候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反响不大,自己觉得平平的,反而有很好的反响,个人和大众的取向还是存在一点区别的,摄影者本人需要倾听更多的声音。
《报恩》:您为七塔寺拍摄了丰富的摄影作品,包含大量的寺院建筑、人物肖像、佛事活动现场图等。作为老宁波人,您与七塔寺的渊源从何而起?
王坚:拍摄七塔寺之前,我一直拍摄的都是自然风光题材,到了2016年,《钱湖早安》影集出版后,我想更换拍摄对象和题材,也是为了挑战一下自己。因缘际会之间,就有了开始的契机。
有朋友曾问我在七塔寺拍了这么长时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每次进到寺院里来,就感觉到家了,内心有一种平静油然而生。
很难说清楚这种感觉,我一迈入寺院的大门,心里就会感觉很舒服。以前连什么是早课、晚课、过堂都不知道,随着来的次数多起来,慢慢也就了解了。和师父们也变得熟悉起来。他们都对我很好,早上来的时候,会问我吃饭了没?也聊聊今天的天气如何等等,有时还会把他们早上分到的小点心、水果往我的包里塞。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来,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这段时间干什么去啦?怎么没来?”现在感觉他们像家人一样,这个熟悉的过程就像手串慢慢包浆一样,很有意思。
《报恩》:七塔寺影集的筹备目前进行得如何?您在筹备过程中有什么感受?选入影集的作品有什么标准?
王坚:最近一直在做七塔寺影集的筹备工作,主要是挑选、汇编和整理照片。从2016年到现在,我来七塔寺拍照的次数有六七百次,有时候早上来,有时候下午来,有时候早上、下午都会来,一年下来会有十万张左右的照片。截止到现在,我拍摄了大概有五、六十万张与七塔寺相关的照片,这个体量实在太大。
我会按时间顺序将作品进行备份,现在就是从最早一直往后翻阅、整理和挑选。整理照片这件事做起来是“痛并快乐着”。“痛”是因为挑选照片很难,有时候选一天,一张好的照片都选不出来。现在进行第一道初筛,之后还要请人帮我再次梳理。如果不是自己的照片,可能就会更加理性地去做一些取舍,而自己拍摄的作品,却有点难以下手,这感觉就跟外科医生不敢给亲人做手术一样。
第一道筛选工作完成后,应该要选出四五千张,眼下大概进展到一半。目前我对于影集的想法是:大概挑选出五百张以内的照片,具体怎么选要看整体的作品质量,要兼顾不同照片之间的协调性等,后续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商讨。至于挑选作品的标准,首先是要自己觉得顺眼;第二是要看符不符合寺院的风格;第三是看单个作品能不能融入影集的整体风格中,内部要有一个整体的平衡,主要就是这三点。
《报恩》:您以前拍摄自然风光较多,现在则以寺院题材为主,在创作不同题材的作品时,您会有意地使用不同的摄影技法吗?您如何在作品中传达佛教气质和禅意?
王坚:不管是风光摄影还是寺院题材,技术原理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好的作品都要有好的光影效果,要抓住变化的瞬间。拍摄寺院题材影像,从原理上讲,可以把房子看成山,把人看成树木,技术上其实是差不多的。但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来凸显寺院的气质,佛教所特有的东西要借助人、佛像、建筑之间的结合来表现。
至于禅意,有的人说静是禅,有的人说动是禅,这看个人的心境。
《报恩》:在您拍摄的大量作品中,是否有一二幅倾心之作?展开谈谈这些作品背后的意境?
王坚:让我从作品里挑出最满意的,很难。因为每张照片都是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不过我也挑了几张自己比较满意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张是一位老香客在上香时的场景。在寺院拍照,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信仰其实是很隐私的东西。创作者在拍摄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出香客的虔诚,同时又要保护个人的隐私,这对摄影师来说是责任,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拍摄的难度。像这张照片,很静,人物的状态也很虔诚,光线又好,肢体语言、心境还有环境结合在一起,很和谐。从审美的视角来看,光线包括烟雾的动态,都富有美感。

这张照片表现了佛像的庄严。佛像看上去很高大,镜头经过一点变形之后,好像对佛像更有了一种仰视的感觉,同时也表现出殿堂的庄严。这一张从佛教的视角来看,图像有些变形,不是很正,但从艺术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个角度冲击力会更大一点。
三圣殿的佛像其实是最难拍的,因为佛像跟建筑的比例比较特殊,佛像小、房子大。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拍到自己很满意的片子。人的眼睛跟镜头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眼睛可以做到“视而不见”,但镜头不行,它会把视角范围内的东西全部拍进去。所以长期从事摄影的人的观察,跟平常人的观察会有一点区别。摄影的难度也在这里,要知道不同镜头的特性,知道想表现什么东西的时候要换什么镜头,以及这个镜头拍摄出来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我平时常用的镜头有一个12毫米的广角、一个10-18毫米的超广角和一个70-240毫米的长焦。一般情况下,我一天之内只用同一个镜头,因为不同镜头的拍摄思路是不一样的,这样拍摄的思路就不会受到干扰。

这一张我印象也很深刻。这位老居士站起来有些吃力,或者说她已经不能正常地跪拜,于是她就坐在凳子上叩拜,非常虔诚。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仍旧坚持到寺院来礼佛。

这样的照片是等出来的。心里预先想好在什么位置、要拍什么,就提前找好位置,然后等在那边。这张照片是受佛经里的内容所启发而尝试的,佛教讲求“不着相”,如《金刚经》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金刚经》又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强调有为法之无常变幻,这样极具画面感的经句是可以通过摄影作品表现的。

这张片子首先是通过一个固定点,多个焦点连续拍摄(大概二十几张),后期采用“景深合成”的方式制作而成,最终把佛像的庄严宝相表现出来。平时礼佛的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看佛像,但我们搞摄影的,要用一种“非常”的视角来表现佛像,把它表现得越殊胜,就越引人赞叹。
《报恩》:影像作品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这些年来您为七塔寺留存了大量的图像素材,在翻阅整理过去的作品时,看着影像中所呈现出的七塔寺的发展变化,您有什么感受?
王坚:这几年变化确实很大,这个城市越来越美、越来越整洁,身在其中的七塔寺在周边的映衬下也越来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七塔禅寺主办的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今年已经举行到第六届,浙东佛教高等研修班也开始第二期,栖心讲坛则进行到第五十七期,同时还举办了“之江问道·法雨长施”七塔禅寺栖心佛学系列讲座、都市生活禅等活动。栖心图书馆的读者也越来越多,有时侯会一座难求。随着“文化兴寺”理念的提出,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七塔寺会跟这个城市一样,越来越好、越来越美。
《报恩》:您曾经提出“创作者要把创作意图准确地传递给观众,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在拍摄寺院题材的作品时,您通常会有什么想表达的意图呢?
王坚:这其实是两个问题。首先,在我看来寺院题材跟其他题材的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于拍摄者要坚持真实创作,真实是最主要的。“以真、善、实”为美。摆拍对我来讲,是不允许的。
李元先生将自己的风光摄影喻为“自然摄影”,就是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添加或者改变作品的原貌。我所理解的“自然摄影”理念是“摄影原教旨主义”,即讲究存在的自然。佛教是讲随缘的,既然是佛教题材,那么摆拍就不是随缘,也是对佛教的不尊重,这是我为自己划的一道红线。我的照片里边有人物出现的,都不是摆拍。其实这样拍摄的难度很大,很多时候都需要等待,等待人物出现。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位置、这个光线可以,我就会在那里等,相当于是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
至于想传达的创作意图,就是要把佛教的建筑之美、造像之美、器物之美、仪轨之美、传统之美等内容通过画面传达给观众,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佛教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希望通过这些“正”的佛教题材作品尽量传达真实的、正统的理念给观众。
二、摄影创作者要守住真实的底线
《报恩》:关于摄影创作,您持有“创作者需要具备观众对其作品进行‘拷问’的觉悟”的观点,这句话如何理解?
王坚:“拷问”就是观众的质疑、批评,或者说让创作者难堪。这种情况对创作者来说,是需要保持平常心来面对的。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观众不会过多考虑客观环境因素,比如拍摄时的位置、光线等等,他们只看最后的成品,这是他们的权利。
另外还有一点,观众人数众多,聪明人大有人在,因此创作者不能觉得人家不专业。以前白居易写诗不是还要念给老太太听,写到她们能听懂吗?美没有外行,是有共同标准的。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创作者要正确地对待观众的眼光和评论,任何时候观众都是对的。好的作品自然会引起观众的共鸣。当创作者个人的标准跟观众标准不一样的时候,就需要处理一个命题:是要随大流还是坚持自己的个性?这看个人的选择。但只要选择把作品拿出来,就必须要接受观众的考核。拿出来接受拷问和自我欣赏是两回事。
《报恩》:您这些年来在工作之余一直深耕摄影领域,是什么驱动着您始终坚持摄影工作?摄影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给您带来了什么?
王坚:摄影于我,虽然时间是业余的,但态度是专业的,这是我对自己的评价。我是有专业精神的,《钱湖早安》系列拍摄了九年才集结出版,从2016年开始,我在七塔寺拍摄也到第七个年头了。
摄影的驱动力其实很简单,就是好玩,拍照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开始拍摄前要做许多选择,比如这段时间叶子开始黄了,就要选择树叶、颜色的题材,接下来要选择到什么地方去拍、具体什么时间点去拍,以及拍摄时天气怎么样、要带什么东西、坐什么交通工具、跟谁一起去……拍摄回来后还要考虑选片要怎么选。摄影就是这样一层一层进行的,每一层都非常有乐趣,每个选择的改变都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东西。选择拍摄的时间,其实也意味着等待。夏天的时候我会想,等过几个月我就可以拍红叶了,会有一种期盼的心情。
对我来说,有摄影这样一个相伴多年的爱好,是很幸运的事情。有时候我都会自我感动,感觉自己对摄影是终生不渝的。
摄影给我带来了许多东西。第一个就是让我的时间过得充实,摄影是很费时间的;第二个是摄影要求人不断精进,要学好多东西。不管是风光摄影还是佛教题材摄影,到最后比拼的是每个人的审美,而不是快门、光圈这些入门时需要掌握的技术。一个人的美学境界决定了其摄影的境界,摄影也提高了我个人的美学修养。平时一群人出去玩,玩摄影的人和不玩摄影的人观察的东西都不一样。经常有人问,我们明明跟你一起去的,你从哪里拍来的这些照片?这一点也很有意思。
《报恩》:时下短视频发展蓬勃,在您看来,视频与图片两种作品的形式有什么区别?
王坚:我一般不拍视频。视频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肯定有它的先进性,比如更全面,可以把一件事情讲清楚。视频跟摄影其实是两个独立的门类,如果要说难度的话,我肯定是觉得摄影略高一些,因为摄影只能用一个画面尽可能地将事情表达清楚,而视频是通过连续的画面。但是当下视频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它的传播范围应该要比摄影作品更加广泛。
《报恩》:您表达过“色彩对于摄影师而言是危险的,掌声越多、陷得越深、色彩越艳,容易迷失自我,忘却初心”的看法,能否再具体阐释一下您对摄影色彩乃至背后摄影技法的看法?您觉得维系摄影艺术的特性,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坚:这里所说的“色彩”,一个是前期造假,一个是后期越做越漂亮。慢慢地,摄影师自己都迷失了。比如现在流行的一些寺院题材摄影照片,都是大家一哄而上、提着灯笼寻佛什么的,都不真实。首先,拍摄一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本身就有违佛教理念;其次,摆拍或者后期进行过大的改动,呈现出来的东西已经是美术作品,而不是摄影作品。
画画可以进行想象、创造,但是摄影不行。有时候听到别人说我的照片跟画出来的一样,虽然对方是出于真心的夸奖,但我的内心还是会为摄影感到很悲哀。摄影不是画画,它是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
摄影首先要做到真和实,然后才会出满意的作品。我修图一般是以原来的照片为准,基本原则是不改动画面里的东西,且拍摄的必须是要真实发生中的事情。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微加工一下,即便在传统的暗房里边也是允许的,暗房也需要通过调试水温,根据放大灯照射的时间来控制影调的深浅或者色彩,也有后期的剪裁,即二次构图等等类似操作。
维系摄影艺术的特性,我认为就是要坚持真实的原则。摄影师必须要有摄影专业精神,不能找时代进步、技术发展等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违背摄影的本质。摄影作品必须基于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其区别于其他艺术种类的最大特性。
文/陈雅芳 张陈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