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所以说是“进入”,因为严格说来,咸宁城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
1926年8月26日夜12时,汀泗桥战役正式打响,由广东人组成的第4军首当其冲,麾下6个团中,叶挺独立团只是和第12师师部一同行进的预备队,倒是两个兄弟团,35团和36团冲锋在前,相互配合拿下了汀泗桥。
按计划,拿下汀泗桥后战斗任务就算结束,但憋了一口气的叶挺下决心要打这一仗。
汀泗铁桥被拿下后,叶挺率领2个营离开师主力,越过第12师右翼陈铭枢第10师的右翼进行大范围包抄,打算合围从汀泗桥败逃的北洋军败兵,却没有料到败兵逃跑的速度很快,当叶挺率领2个营到达距离汀泗桥6里的古塘角时,败兵已经越过了古塘角,继续往咸宁方向逃跑。
叶挺心有不甘,不顾师长张发奎追击不得超过15里的命令,一气追出25里进入了咸宁城,最终俘虏了几百敌兵。
于是,叶挺独立团成了北伐军中跑在最前的部队,而小小的咸宁城也突然见证了瞬间的改天换地。
咸宁城居民的眼中,从4天前的23日起,大批头戴五色星帽徽,衣领上佩戴红五角领章,配直肩章的北军源源不断从北门进入,到了27日下午,这些北军就争先恐后向北逃,后面跟着大批头戴大檐平顶帽,帽墙正中镶青天白日徽,身穿草青色中山军装的南军。
在军纪严明的南军和军纪败坏的北军之间,老百姓很快作出选择,他们不仅积极帮南军带路,还自发捉拿落单的北军。

第二天的28日上午,天上飘着阴雨,炎热的咸宁城有了几分凉爽,不堪屋内闷热的市民们敞开大门,惊奇地看着街上到处张贴传单的南军宣传队,尤其让他们眼中一亮的是宣传队中梳着短发,英姿飒爽的女兵。
女兵们脸上绽放着阳光和自信的笑容,那份气质和咸宁城学堂里的女学生一样,只是多了十分的英气和活泼,她们自由地和男兵张贴传单,胸部不甘心地将军装撑得鼓鼓的,细细的蛮腰却乖乖地被宽阔的武装带紧束着,贴标语的手像葱白一样白嫩,让市民们想入非非,识字的市民在宣传队女兵刚刚贴上的标语前仔细看念着,又吸引了一大批市民围观。
很少有市民们注意到,一支小队伍簇拥着10来名骑马的军官从南门而来,普通市民们对这些军官并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南军官兵的标识并不明显,唯一的区别就是士兵们扛长枪穿草鞋,军官们穿军靴,左臂上配着不同的牌牌。眼前这批军官看起来都是30,40岁的样子,除了比常见的军官年龄显得大些,并没有特殊,至于马匹,营长就可以配备,有的连长都骑马,市民们的眼光牢牢吸引在宣传队靓丽的风景上,对眼前走过的马队都不以为然。
这支队伍沿着南北大街来到了原来的北军司令部——咸宁城老县衙,军官们先后下马,马匹被马夫牵走,他们在几名年轻军官的引导下进入县衙大堂,副官和卫士则被请到大堂两侧的厢房中。
一、几位大佬如何定了贺胜桥战役的规划?

老县衙的大堂并不大,辛亥以后,这个县衙的所有匾额都被去除,屏风上依稀还能看到当年的“海天日”画,屏风下还保存着一张法桌,桌上放着一部电话机,一名40岁左右,左臂上配党徽和三颗金色三角星的瘦高军官显然是这群军官的中心人物,他站在大堂中央,上下左右扫视了一下大堂环境,然后走进法桌上的电话机端详着,一口宁波官话问:“叶挺就是通过这部电话机,知道吴佩孚到了贺胜桥的?”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一名左臂上佩戴两颗金星,身材瘦小的军官。这名军官30岁年纪,一张男人味十足,留着漂亮八字胡的国字脸,精心打理的军装下腰杆挺得笔直,用一口粤式普通话回答到:“报告总司令,昨天叶挺进来时,正听到这部电话响,他拿起听筒一听,是吴佩孚的一个参谋从贺胜桥打过来的,叶挺将计就计,从参谋口中套出了吴佩孚已经到达贺胜桥的消息。”
被称作总司令的,就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他笑着对这名军官说:“向华,你的部队在汀泗桥打得很好啊,我没有想到进展这么快,连敌人都没有想到,叶挺团昨天算得上孤军深入,看来他们的士气很高,他现在在哪里?”
这名被蒋介石称作向华的,就是第4军第12师中将师长张发奎,他说:“叶挺打仗很主动,他一听吴佩孚到了贺胜桥,就带独立团占领了城北的东山站,现在他们已经推进到驾城铺,距离这里有15里。”
当张发奎回答时,年轻的参谋们急忙将法桌上的电话拿走,将一副地图铺在桌上,但细窄的法桌撑不起宽大的地图,使得地图两边垂了下来,4名参谋两两站在法桌两边,每人抓起地图一角,将地图摊开。
蒋介石走过去一边看着地图一边点头:“驾城铺对面的横沟桥镇就是吴佩孚的军队嘛,叶挺打得很主动,我们革命军人,如果个个有叶挺的精神,北伐就一定能成功。”然后,他转过身面朝大家说,“诸位,我们奉先总理遗训,北伐以来深得民心,一路势如破竹,沿途百姓无不箪食壶浆欢迎我们,短短3个月,我们就从广东打到了湖北,胜利指日可待,前面就是武昌城了,不过我们要先拿下贺胜桥,希望诸位一鼓作气,既要发扬革命的战斗精神,又要灵活运用战术,以最小的代价拿下贺胜桥。”

蒋介石身边的一位瘦高个子,左臂配上将军衔的军官说:“根据获得的情报,贺胜桥的敌人有两股,一股是从汀泗桥败退到贺胜桥的军队,这些军队有1万人,但是被我们打残了,不足为惧,另一股是吴佩孚亲率的南下新锐,有刘玉春的第8师,张占鳌的第13混成旅,还有吴佩孚本人的卫队旅,也有1万人,两股敌军共约2万余人,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有60多门山野炮,100多挺机枪。”
蒋介石插话说:“人数上我们是占优势的。”
上将接着说:“初步的侦察结论,敌人在贺胜桥有3道防线,第一道在贺胜桥以南约10里的桃林铺,第二道在贺胜桥南4里的印斗山,第三道就是贺胜桥,3道防线的纵深共有10里。”上将思路清晰,胸有成竹,他并不看桌上地图,眼光却一直停留在军官们的脸上。
见大家士气颇高,上将很欣慰说:“我们革命军人以一当十,作战英勇,这是反革命的北洋军阀比不了的,有些将领向我反应,我们经过了前几次的大战,弹药比较缺乏,希望我补给,但是我没有补给,革命军的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了敌人就是我们的补给,我们唯有刺刀,我们要赶快冲锋,我们拿下了武昌,汉阳兵工厂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蒋介石说:“参谋长说得很好,革命军人就是要有为革命牺牲的勇气,我们当兵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在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
被蒋介石喊作参谋长的这位上将就是白崇禧,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参谋次长,一直向蒋介石请求到前线带兵,但是蒋介石却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担任参谋长,一番拉扯后两人达成协议,白崇禧先留司令部几个月,待攻下武昌后再到前线带兵。
蒋介石又朝着一名35岁左右,左臂上配上将军衔的壮实军官问:“德邻,你的第7军部队到了哪里?”

被称作德邻的是第7军军长李宗仁,他回答:“总司令,我第7军在第4军右翼,目前分两路,第1路由夏威旅长率领已经到达了袁家铺,第2路由胡宗铎旅长率领,已经到达了王家铺的钟家村一线。”
此时夏威和胡宗铎两位旅长都在李宗仁身边,蒋介石向二将点点头,又转向一位45岁的上将问:“景瑗,你的第4军到哪里了?”
在场所有的军官中,这位上将年龄最大,资历也最老,他曾是孙中山总统府的警卫团团长,在粤军中桃李满天下,算得上粤军元老,名叫陈可钰,此时以副军长代行军长职,只是他此时身体不好,皮肤苍白,人也显得非常瘦弱。
陈可钰回答到:“总司令,我军第12师前锋就是叶挺独立团,目前到了驾城铺,第10师跟在第12师后10里。”
蒋介石转眼看着第12师师长张发奎和第10师师长陈铭枢说:“好,你们在汀泗桥打得很好,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再打好贺胜桥这一仗。”
对陈可钰的安排,第12师师长张发奎并不认可,他认为第12师在汀泗桥一仗担任主力,付出了重大牺牲,便宜却被第10师捡了,使得第12师缴获不如第10师多,因此这次理当由第10师担任主力,让他的第12师得到喘息,陈可钰却再次让他打主力,这大出他意料之外,但陈可钰是第12师的老师长,他的安排让张发奎无话可说。
蒋介石又转向一位30左右,戴眼镜的上将:“唐军长,你的第8军到了哪里?”
第8军上将是唐生智,他急忙一个立正:“总司令,我军第1师在宝塔州附近渡江,第2师正在嘉鱼渡江,准备绕道汉口和汉阳,攻击吴军后背,第3师在向金口前进中,第4师也在蒲圻附近准备渡江。”

蒋介石很高兴:“唐军长,你的部队进展很快,兵贵神速嘛,要乘吴佩孚立足未稳一鼓作气打败他。”他看着大家说,“第1军已经到了蒲圻和岳州,第6军也已经到了崇阳,形势对我们很好。”
白崇禧说:“这次打贺胜桥,我看第4军和第7军的军部都可以设在这里,一方面这里距离前线有20里,在吴佩孚大炮射程外,另一方面,这次是第4军和第7军共同作战,便于配合指挥。”
蒋介石说:“健生说得对,我们要攻取武昌,贺胜桥是绕不过去的,前方将士们在流血牺牲,我也要和大家在一起,我决定把总指挥部也设在这里,和你们4军,7军在一起。”他右手臂伸得笔直,食指朝下点着地面,然后收回右手变成双手叉腰,“第4军和第7军联合作战,需要统一指挥,我看从贺胜桥一直到武昌的战役都由德邻全权负责,德邻,这个总指挥就由你来当,你看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一个立正:“职服从命令。”
“好,从现在起,前线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
李宗仁答应道:“是。”
蒋介石朝着白崇禧说,“健生,去看看我们的住处,不要妨碍德邻指挥。”说着向大堂外走去,白崇禧对众人拱手道:“拜托诸位了。”随在蒋介石身后走了出去。
看蒋介石和白崇禧都已离开,李宗仁对陈可钰及在场的军官说:“既然总司令有此命令,职唯有遵命,军情紧急,现在乘着大家都在,我想就在这里再明确一下任务。”
李宗仁:“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拿下武昌,贺胜桥只是我们的当前的战术任务,因此我们的战略部署要朝着有利与攻占武昌来进行,现在唐军长的第8军正渡长江袭取汉阳,从西面孤立武昌,陈军长的第4军在铁路一线,叶挺团已经在驾城铺和吴军对峙,就烦劳陈军长率4军继续沿铁路线正面进攻贺胜桥,我率第7军从右翼东北方向楔入鄂城,为将来4,7,8三军从中,东和西三面夹击武昌奠定目标。”
张发奎不顾自己只是中将,脱口而出:“总指挥,你的战略非常好,只是眼下我们4军1万多人,当面吴军有2万多,他们不仅有工事之利,还有精良的装备,正面进攻有困难,希望总指挥能给我们4军一些支援。”
张发奎的插话让李宗仁有些意外,但李宗仁是忠厚之人,并不责怪,而是解释说:“张师长不要担心,我的左翼胡宗铎旅长带第2,7两个旅和你们并肩前进,共同作战。”

胡宗铎比张发奎大4岁,毕业于保定4期,是张发奎的学长,概因军旅生涯走了一段弯路,现在还挂少将衔。
听李宗仁如此说,张发奎半开玩笑地对胡宗铎拱手:“小弟就要承蒙胡兄多关照了。”
胡宗铎不苟言笑,他并不如张发奎放得开,拘谨地说:“发奎老弟不要这样说,我们都是革命军人,理当互相策应。”
李宗仁笑着说:“好,明天下达进攻命令,现在就散会,请诸位各就各位。”
由于4军和7军的军部都设在县衙,因此李宗仁和陈可钰等军部的将领都在县衙安顿,其余师级以下将领都各回本阵,陈可钰陪着张发奎和陈铭枢步出县衙,来到大门口,陈可钰对二人说:“我们内部么事都好说,前线的事,你们之间直接协调解决,不用汇报我,如果需要联络7军我再出面。”
张发奎和陈铭枢点头称是,马夫将他们的马匹牵过来,两人各回本部。
二、谁是贺胜桥的主攻?

马夫牵来的是一匹枣红色蒙古马。按照制度,师长拥有两匹马,因此张发奎还有一匹黑色川马,通常在平路上,张发奎会骑着蒙古马奔驰,在山间小路才骑那匹黑色川马,此时他翻身上了蒙古马,让在厢房内等候他的一名副官和一名卫士步行回师部,自己骑马飞奔。
张发奎本性粗狂,爱好烟酒,尤喜策马飞奔,但和部队一起行军时通常不骑马,此时没有大部队,他正好有独自策马的机会,他加鞭飞跑起来,感受着呼呼扑面的凉爽和两旁一闪而过的景色,感觉到了身心的释放,遗憾的是指挥所就在咸宁城北2里的东山,几分钟就跑到了,实在没有过瘾。
东山是一个只停货车的铁路小站,它的东北是山岭,山岭之西是斧头湖,狭窄的地形使得东山成为阻止北方军队南下的咽喉,也因为如此,叶挺得到吴佩孚到贺胜桥的消息后就立刻占领了这里,随着第12师主力全面北上,这个小站的站长室就成了张发奎的师指挥部。
张发奎下马进了站长室,副师长朱辉日带着几个作战参谋在忙着。
朱辉日35岁,保定六期生,挂少将衔,此时正忙着和前线的3个团联系并听取汇报,见张发奎进来,就一眼不眨地看着他,希望从他这里得到最新的消息。
夏天的湖北非常闷热,张发奎骑马奔驰时还感到凉爽和痛快,下马后顿时觉得闷热难受,浑身冒汗,他进门后一边脱下军帽一边松开风纪扣,一名有眼力的参谋急忙递过来一杯水,他端起来喝尽了,然后从下衣口袋中掏出一支烟,参谋给他点上,他坐在凳子上猛吸一口烟,然后长长吐出,转眼见朱辉日看着自己,笑着说:“这一仗,我们还是在第10师前面。”
朱辉日跟张发奎的时间日久,因此说话并不顾忌,说:“汀泗桥一仗我们吃亏,第10师可是占了大便宜,拇知老师长怎么想的?”
张发奎说:“我也不知,我猜老师长是认为当面的敌人不经打,他想让我们多立功吧。”
朱辉日说:“会不会是陈铭枢不愿意打头阵,他一直抱怨他的武器不如我们。”
张发奎说:“他的武器比我们差远了,他的军官好多都还没有配手枪,我们的军官可都配齐了手枪,连总司令的卫队都装备了我送的10多支毛瑟手枪,不过,我们的武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拼命从海南的邓本殷手上缴获的,他陈铭枢有本事也去吴佩孚那里缴获啊。”
朱辉日摇摇头:“真的好搞笑。”
张发奎说:“不说了,总司令的意思,我们4军和7军主攻,由7军军长统一指挥,进攻命令明天下达。”

朱辉日说:“站长向我们报告,在我们到来之前,他接到汉口站来的电话,吴佩孚从河南带了2个师南下,目前已经抵达汉口,乘着他们立足未稳,我们要抢先进入阵地,保证命令下达后部队能最快地进攻。”
张发奎说:“你的想法很好,就这样办,不过,你想顶样(怎样)配置3个团?”
朱辉日说:“36团在汀泗桥打了主力,损失较大,现在独立团已经冲在了最前面,我建议这次由独立团主攻,35团配合,36团为预备队。”
张发奎站起身说:“好。”手指夹着烟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观看着,地图上贺胜桥方向的敌军阵地已经用好几个蓝色三角贴上了。
从咸宁到贺胜桥一段密布湖泊和树林,但地形远不如汀泗桥险峻,那里既没有汀泗桥附近的500多米陡峭山岭,也没有汀泗河那样1人多深,200米宽的河流,部队可以充分展开和发扬火力,并且快速发起进攻,只是吴佩孚亲自带来的嫡系,其战斗力比汀泗桥敌军要强得多。

张发奎看着地图,心中喜忧参半,这时,朱辉日靠近张发奎,用手指指着地图上粤汉铁路上咸宁到贺胜桥之间的一个地点:“独立团已经进驻驾城铺,向横沟桥和贺胜桥方向警戒。”
地图上的横沟桥是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在驾城铺东面,隔着粤汉铁路和驾城铺遥遥相对,东北走向的粤汉铁路在这里来了个急转弯,直直地向北朝向贺胜桥。
朱辉日的手指向西面滑过去,停留距离驾城铺约12里的地方:“目前35团在独立团西面的官埠桥镇,向黄石桥方向警戒。”之后,又在前两个地点后面划着大圈,“36团在两团后面5里,随时支援。”
张发奎看着点头说:“我看就这样,马上上报老师长,把师部直属队也算作预备队,随时准备好支援,保证3个团之间联络畅通。”他又对在场的几名作战参谋说,“你的(你们)都要紧张起来,做好随时下连队的准备。”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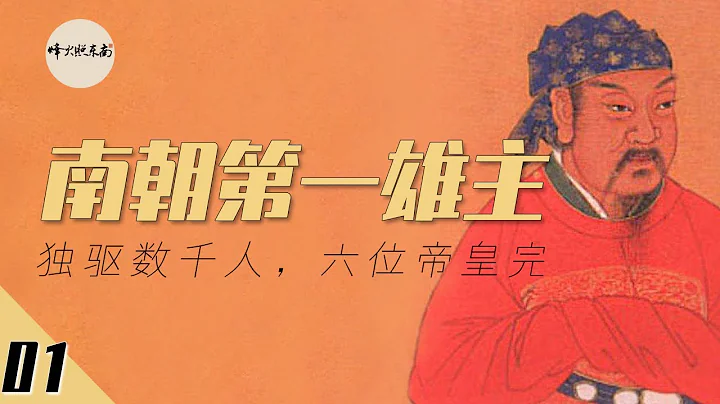









![[Multi Sub]【全集完结】《我的女将军大人》女将军穿越意外嫁总裁,被心机女暗算,下一秒把人拎起来了?总裁老公看呆了!#姜十七#甜宠#霸道总裁 - 天天要闻](https://i.ytimg.com/vi/WjOB6VJIAGY/hqdefault.jpg?sqp=-oaymwEcCOADEI4CSFXyq4qpAw4IARUAAIhCGAFwAcABBg==&rs=AOn4CLBwlD8_ThEJmQNWBHgzxiZDH2EZHg)





